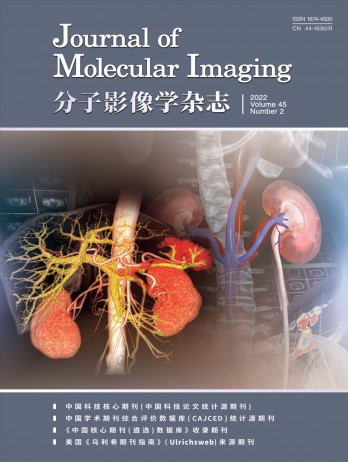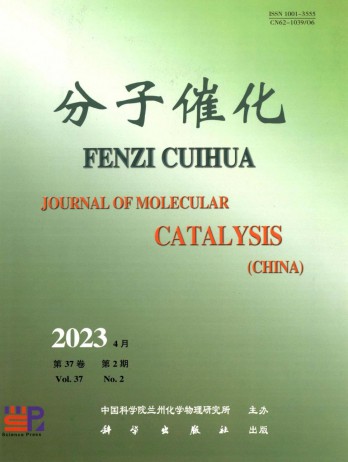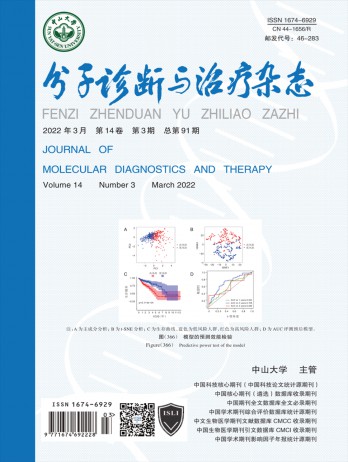分子遺傳學綜述精品(七篇)
時間:2023-10-12 16:08:3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分子遺傳學綜述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林麝;分子遺傳學;分子標記;人工繁育;泌香
林麝Moschusberezovskii又名麝鹿、香獐,屬偶蹄目Artiodactyla、麝科Moschidae、麝屬Moschus,是目前養殖規模較大、數量最多的麝科動物之一。雄麝香腺分泌的外激素――麝香在傳統中藥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2]。由于國際香料市場和醫療行業對麝香需求量的大增,人類“殺麝取香”和對其棲息地的嚴重破壞,已使該物種野生種群數量急劇減少,現存麝類已面臨瀕危。目前,林麝已被列人CITES附錄Ⅰ中,《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將麝列為瀕危或易危動物[3]。我國1988年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將林麝列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2002年又將其提升為一級保護動物。麝的珍貴引起了許多生物學工作者的濃厚興趣,在林麝的生態學[4]、行為學[5]、分類學[6]、生理學[7]以及麝香的藥理學與臨床應用[8]等方面開展了積極的探索。
近年來,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不斷發展,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等新興生物技術開始被不斷地運用到林麝遺傳育種工作中,為林麝的育種保護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其中,以新興發展起來的分子遺傳標記技術最引人注目,分子遺傳標記的出現使基于此類標記的選擇育種技術有了實現的可行性,顯現出了巨大的應用潛力。當前,分子遺傳標記在林麝遺傳育種中的應用主要體現在遺傳分類、人工繁育、泌香、疾病等方面。本文就分子遺傳學在林麝研究中的應用現狀做一綜述,并對后期研究進行了展望,以期為提高林麝的生產性能提供參考。
1林麝分子遺傳標記
分子遺傳標記是基于DNA差異進行個體或群體遺傳多樣性分析的有力工具。常用于林麝遺傳多樣性分析的分子標記方法有AFLP,mtDNA,微衛星DNA等。
AFLP技術在種群結構和差異的調查中起著非常重要作用[9]。陳軒[10]根據AFLP分子標記的特點,以四川養麝研究所白沙養麝場21只林麝樣品和金鳳山養麝場14只林麝樣品為材料,對2個種群的遺傳多樣性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四川養麝研究所白沙養麝場圈養的2個林麝種群均具有較高水平的遺傳多樣性,但金鳳山種群具有相對較高的遺傳多樣性。趙莎莎[11]利用相同的原材料進一步檢測了22對選擇性引物組合,共獲得了908個AFLP多態片段,結果證明了麝香高產組在多態位點比率(PPL)上極顯著高于參照組和低產組,在遺傳多樣性水平上也有更高的整體競爭優勢。
mtDNA是核外遺傳物質,由于mtDNA的控制區富含A,T堿基,屬于遺傳高變區,進化速度比其他區域快,多態性豐富,常被應用到野生動物群體遺傳多樣性檢測中。彭紅元等[12]通過分析四川省3個本地種群中林麝mtDNA控制區域582bp片段,發現94個變異位點,在109個個體中檢測出27個單倍型,表明3個群體間很少進行遺傳交流,建議建立系譜以增加群體間基因的交流。2014年,馮慧等[13]調查了陜西省林麝1個圈養種群3個野生種群mtDNAD-Loop632bp片段的遺傳多樣性和種群結構,結果表明,陜西省林麝群體mtDNAD-loop區序列存在著較豐富的變異和遺傳多樣性,鳳縣野生群體和鳳縣養殖場群體的核苷酸多樣性和單倍型多樣較高,養殖場種群沒有出現近親繁殖及遺傳多樣性下降的情況。鳳縣野生群體和鳳縣養殖場群體兩者遺傳分化較小,存在著較高的基因流水平。
微衛星DNA廣泛分布與真核生物基因組中,具有多態性高、共顯性遺傳、選擇中性、易于操作等特點,是一種極具應用價值的分子遺傳標記,由于微衛星重復序列在群體間和不同的個體間通常表現出很高的序列變異性,并且這種變異呈共顯遺傳,因而在微衛星重復序列廣泛應用于物種遺傳多樣分析。2004年,鄒方東[14]運用微衛星標記法構建了3個林麝基因組微衛星富集文庫,每個文庫含有上萬個轉化子。2005年,Zou等[15]又運用了改進的富集文庫方式來分離微衛星位點,獲得了野生林麝的多態位點,結果發現70%的基因組文庫為(AC)_n文庫,8個微衛星位點呈現高度多態性,可作為研究林麝的分子遺傳標記。2006年,夏珊[16]對構建林麝的微衛星文庫篩選了6個多態性好的座位,并對林麝的遺傳多樣性進行初步的分析,6個微衛星座位的多態信息含量(PIC)最低為0.6214,最高為0.7984,說明這6個林麝微衛星座位具有高度多態性,進一步證明了微衛星DNA是很好的分子遺傳標記。
2林麝遺傳分類研究
目前,對林麝的遺傳分類有3種研究手段,分別為形態解剖學、細胞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一種是根據外形、頭骨和距骨的形態特點以及生態習性、分布等認為麝確是一個獨立物種[17]。陳服官等[18]根據林麝生物標本,再一次肯定了這種分類方法。林麝作為麝科動物一個亞種除了在形態解剖學上得到了明確的肯定外,從細胞遺傳學特征來看,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細胞的染色體組型和染色體帶型都代表著種的特性,它為不同物種在分類研究和確定其在進化過程中的位置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依據。2004年,鄒方東等[19]以林麝外周血淋巴細胞為實驗材料,首先建立了適合林麝淋巴細胞增殖的培養體系,并用培養出的細胞制備染色體,確定林麝核型是2N=58,且全都是端著絲粒染色體,還首次應用染色體G-帶技術,對林麝染色體的G-帶帶型進行了研究,確定了林麝染色體是2N=58,且全都是端著絲粒染色體,這與其他鹿科動物存在較大差異。結果表明,從細胞遺傳學角度將麝分為單獨一科也是比較合理的。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麝作為獨立的科在分子水平上相繼得到了印證。Kuznetsova等[20]對鹿科家族成員和其他偶蹄動物的線粒體基因12S和16SrRNA(2445bp)的序列和核β-spectrin基因(828bp)的區域進行分析,發現鹿科和麝存在幾個分子共源性特征。劉學東等[21]則利用測得梅花鹿、坡鹿、原麝和林麝的線粒體12SrRNA基因全序列,與GenBank中檢索到的鼷鹿、長頸鹿和牛12SrRNA基因全序列進行對比,分別應用ME,ML,MP方法重建系統樹,發現3種樹拓撲結構一致,結果顯示麝、鹿、牛、長頸鹿均各自為單系群,且麝作為一個單系進化。此外,采用PCR技術和序列測定方法從線粒體DNA上得到367bp的細胞色素b基因片段序列,分析其序列可得出在麝、獐、麂和鹿的系統進化中,麝約在600萬年前與鹿科分歧,而鹿科的3個亞科是在350~500萬年前開始分歧,表明麝可單獨作為麝科[22]。張亮則采用克隆SRY基因的CDS區的方法,得到林麝和馬麝的SRY基因,對其進行分析顯示,支持麝作為獨立一科的觀點[23]。2009年,彭紅元等[12]測定了林麝全線粒體序列,分別運用MP,Baryes方法與其他22種反芻亞目的動物相關基因序列進行系統進化分析,表明林麝與鹿科動物的親緣關系最為接近,并單獨形成一支,在牛科和鹿科之前分化出來,為鹿科、牛科互為姐妹群。2012年,馮慧等[13]從秦嶺林麝的毛發樣品中提取得到線粒體DNACytb基因的部分序列,并對其進行序列分析,發現林麝、原麝、馬麝、喜馬拉雅麝、黑麝是5種獨立的種,林麝與原麝的親緣關系最近,進一步彌補了現有形態分類研究的不足,得到更有說服力的分析結果。截至目前,運用各種克隆方法得到的林麝DNA序列,對其分析后發現其遺傳學分類與形態解剖學、細胞遺傳學得到的結果是相同,對麝作為單獨一個物種的結果進行了充分的肯定。
3林麝分子遺傳學在人工繁育上的應用
經過50多年的發展,我國在林麝的人工繁育方面取得了不少優秀成果。但是,由于基礎研究及資金等方面的問題,我國的圈養林麝規模一直徘徊在6000只左右[24],并且在林麝養殖過程中出現的種群退化、后代抗病力下降等問題也不斷凸顯,因此,加大對林麝的人工繁育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工作力度顯得尤為重要。2004年,鄒方東等[25]首次成功克隆了與林麝生殖相關的核β-A亞基成熟肽序列,為林麝的人工繁育和麝資源的保護利用提供了相關基礎資料。也有人對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遠東地區和薩哈林島的麝進行遺傳多樣性分析,發現隨著棲息地的分裂,麝的近親繁殖遺傳多樣性在不斷上升,進而出現種群隔離現象[26]。此外,岳碧松研究團隊對四川省米亞羅、金鳳、馬爾康3個養殖場的林麝進行微衛星分析,表明都是有效的群體規模,其遺傳結構具有重要的保護意義,并建議在林麝人工育種時應當充分考慮這種遺傳結構[27],這為林麝的選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認識。2013年,岳碧松研究團隊再次對四川米亞羅地區人工繁育林麝的多態性進行微衛星分析,發現由于引入新的血緣,林麝的雜合程度和遺傳多樣性在不斷增加[28],為林麝的人工繁殖管理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
4分子遺傳學與林麝泌香的關系
獲取麝香是保護林麝遺傳資源的本質因素,提高麝香的產量,對林麝泌香相關的研究已經從組織解剖水平深入到泌香分子機制的研究。陳軒[10]分析了林麝AFLP的多態性與產香量的關系,篩選出34個在高產組和低產組間等位基因頻率分布有顯著(P參照組>低產組(P
白康[29]采用PCR-SSCP、測序分析等生物技術手段對雄性激素受體(AR)基因外顯子1,4,8進行研究,結果顯示,AR基因外顯子1,4,8在所做樣本中不存在多態性,說明雄性林麝AR基因外顯子(1,4,8)在林麝中具有高度保守性。王勤等[30]克隆了調控林麝的繁殖和泌香的重要垂體激素FSH-β和LH-β基因,這為開展林麝泌香過程中基因表達的關聯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5分子遺傳學與林麝疾病相關分析
麝類疾病是長期阻礙林麝人工養殖發展的關鍵因素。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分子遺傳標記技術已經運用到林麝的疾病診治過程中,這為尋找麝類疾病起因,制定相應抗體提供了一種新的借鑒方法。羅燕等[31]對林麝肺源致病性Escherichiacoli毒力基因進行了檢測及鑒定,為進一步研究林麝肺源致病性E.coli的致病機制奠定了基礎,同時為防治林麝E.coli性肺炎提供了依據。2013年,鄒丹丹等[32]克隆和表達了林麝IL-1β基因,為其用于林麝疾病的防治奠定基礎。李靈等[33]以四川養麝研究所的115只林麝個體為對象,通過對MHCⅡ類經典的DR和DQ座位的分離、遺傳變異分析和化膿性疾病相關性的分析,揭示了林麝MHCⅡ基因多態性的維持機制及其與化膿性疾病的密切關系。周鑫等[34]為調查林麝肺源致病性大腸桿菌O因子血清型以及相關耐藥基因的流行狀況,采用玻板凝集反應法進行O因子血清型鑒定,同時用PCR方法檢測耐藥基因,發現29株菌皆攜帶多種耐藥基因,這對林麝臨床科學合理用藥有重要指導意義。
6問題及展望
6.1存在的問題
6.1.1林麝馴化程度低,對分子遺傳工作的開展帶來極大不便從1958年以來,全國陸陸續續開展了林麝的馴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陜西鎮坪、四川馬爾康、重慶南川等養殖基地[35-37]。但由于科研經費有限及林麝養殖效益等問題,馴化研究并沒有持續,這造成了林麝的馴化程度很低。這給林麝分子遺傳研究過程中的樣品采集、生產性能測定等工作帶來極大不便,也給林麝帶來強烈的應激反應。強烈的應激反應不僅給實驗數據的可靠性與穩定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還對林麝自身的健康造成不利影響。
6.1.2林麝為一級保護動物且價格昂貴,限制了某些分子遺傳相關工作的開展林麝為國家一級珍稀瀕危藥用動物,不允許因為科學研究而對林麝有任何傷害,因此無法及時地采集林麝內臟進行深入的分子生物學相關研究,只能采集林麝毛發、血液或因疾病死亡林麝的內臟,這給林麝分子遺傳學相關研究帶來了不便。同時,由于林麝資源量有限,存在非常嚴重的炒種情況,目前每對林麝的價格被炒到7萬元,昂貴的種源成本大大降低了林麝產香的盈利能力,也大大提高了林麝研究的成本,這種現象不僅嚴重阻礙了林麝分子遺傳相關研究,而且不利于整個林麝養殖產業的健康發展。
6.1.3相關科研人員稀缺,發展緩慢目前,相對與其他常見動物,從事林麝相關工作的人員極少,主要分布在四川養麝研究所、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四川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浙江大學、陜西動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幾乎沒有進行過林麝養殖行業的專題研討及技術交流會。因此先進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在林麝上應用的時間相對靠后,這也大大地降低了林麝遺傳學相關研究的進展。
6.2展望
6.2.1麝香資源奇缺是林麝分子遺傳學研究開展的內在動力麝香具有極高的藥用價值,但由于麝香的產量極低,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這使得麝香的價格長期維持在黃金的3倍左右,因此,提高麝香產量就成為了林麝養殖行業的最重要目標。但由于林麝資源量極少且馴化程度低,傳統遺傳育種方法很難在林麝上得到順利開展,因此通過分子遺傳學方法篩選麝香高產分子標記越來越成為關注的焦點。
6.2.2新技術新方法的應用將大大加快林麝分子遺傳學研究進展林麝分子遺傳學研究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的不斷進步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DNA條形碼鑒定物種技術[38]、DNA分子性別鑒定技術[39]已成功運用在林麝遺傳資源保護與與繁育工作中。然而,相對于林麝如此豐富的遺傳背景,僅靠分子生物學技術遠遠不夠,而且相關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充分應用,因此有必要進一步了解林麝的遺傳結構,將傳統研究方法和分子生物技術相結合,了解其遺傳結構差異和特征,進行針對性保護和利用。另外,為了促進人工養麝事業的發展,提高林麝種群增長率和麝香產量,須繼續加強對林麝的泌香性狀、疾病抗性等表型的標記研究,為實現標記輔助選擇(MAS),加速良種培育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1]中國藥典.一部[S].2010:361.
[2]安談紅.麝香藥用價值研究[J].吉林農業,2010(8):211.
[3]李天培.古老珍貴的物種――麝[J].中學生物學,2004(3):9.
[4]姜海瑞,薛文杰,徐宏發.林麝的生物學特性、資源現狀及保護對策[J].生物學教學,2012(5):7.
[5]衛寧.圈養雄性林麝期與非期主要行為的研究[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14.
[6]GrovesPC,馮祚建.安徽省麝的分類地位[J].獸類學報,1986,6(2):105.
[7]韓增勝,楊長鎖,李青旺,等.林麝生殖生理和繁殖性能觀察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31(6):103.
[8]陳怡君,鐘玉緒,董武,等.麝香酮對斑馬魚胚胎的發育毒性[J].中國藥理學與毒理學雜志,2014,28(2):267.
[9]朱偉銓,王義權.AFLP分子標記技術及其在動物學研究中的應用[J].動物學雜志,2003,38(2):101.
[10]陳軒.林麝AFLP的多態性研究及產麝性能的標記分析[D].杭州:浙江大學,2007.
[11]趙莎莎.圈養林麝遺傳多樣性及泌香性能關聯標記的分析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9.
[12]彭紅元,張修月,岳碧松.林麝線粒體基因組擴增及其序列結構的初步分析[J].玉林師范學院學報,2011,32(2):63.
[13]馮慧,馮成利,劉曉農,等.林麝毛發DNA的提取及系統發育分析[J].西北農業學報,2012,23(8):14.
[14]鄒方東,岳碧松,張義正.林麝(Moschusberezovskii)微衛星的分離與多態性研究[C].南充:四川動物學會第八次會員暨第九次學術年會,2004.
[15]ZouFD,YueBS,XuL,etal.Isolationandcharacterizationofmicrosatellitelocifromforestmuskdeer(Moschusberezovskii)[J].ZoolSci,2005,22(5):593.
[16]夏珊.林麝(Moschusberezovskii)微衛星分子標記篩選及其應用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6.
[17]高耀亭.中國麝的分類[J].動物學報,1963(3):479.
[18]陳服官,閔芝蘭,黃洪富,等.陜西省秦嶺大巴山地區獸類分類和區系研究[J].西北大學學報,1980(1):137.
[19]鄒方東,岳碧松,張義正,等.林麝染色體制備方法及核型與G-帶帶型研究[J].獸類學報,2004,24(2):115.
[20]KuznetsovaMV,KholodovaMV,DanilkinAA.Molecularphylogenyofdeer(Cervidae:Artiodactyla)[J].Genetika,2005,41(7):910.
[21]劉學東,鄭冬,馬建章.從12SrRNA基因序列探討麝類動物(Moschus)在新反芻下目中的系統學地位[J].東北林業大學學報,2005(3):59.
[22]李明,盛和林,玉手英利,等.麝、獐、麂和鹿間線粒體DNA的差異及其系統進化研究[J].獸類學報,1998,18(3):184.
[23]張亮,鄒方東,陳三,等.林麝及馬麝SRY基因片段克隆及其在系統進化分析中的應用[J].動物學研究,2004,25(4):334.
[24]李林海,黃祥云,劉剛,等.我國麝養殖種群現狀及養殖業發展的分析[J].四川動物,2012,31(3):492.
[25]鄒方東,張義正,楊楠,等.林麝、馬麝及梅花鹿活化素基因β_A亞基成熟肽序列的克隆和分析[J].動物學雜志,2004,25(3):22.
[26]KholodovaMV,Prikhod′koVI.MoleculargeneticdiversityofmuskdeerMoschusmoschiferusL.,1758(Ruminantia,Artiodactyla)fromthenorthernsubspeciesgroup[J].Genetika,2006,42(7):955.
[27]GuanTL,ZengB,PengQK,etal.Microsatelliteanalysisofthegeneticstructureofcaptiveforestmuskdeerpopulationsanditsimplicationforconservation[J].BiochemSystEcol,2009,37(3):166.
[28]HuangJ,LiYZ,LiP,etal.GeneticqualityoftheMiyaluocaptiveforestmuskdeer(Moschusberezovskii)populationasassessedbymicrosatelliteloci[J].BiochemSystEcol,2013,47:25.
[29]白康.林麝雄激素受體多態性和性激素水平與其泌香量關系的研究[D].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2.
[30]王勤,張修月,王中凱,等.林麝促卵泡激素和促黃體激素基因的克隆及其序列分析[J].四川動物,2012,31(1):77.
[31]羅燕,王朋,趙洪明,等.林麝肺源致病性大腸桿菌分離鑒定及毒力基因PCR檢測[J].中國預防獸醫學報,2012(8):615.
[32]鄒丹丹,楊東,姜立春,等.林麝IL-1β基因的克隆、表達及生物學活性檢測[J].畜牧獸醫學報,2013,44(11):1734.
[33]李靈.林麝Ⅱ類MHC基因分離與化膿性疾病的相關性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13.
[34]周鑫,羅燕,程建國,等.林麝肺源致病性大腸桿菌O因子血清型鑒定及部分耐藥基因的PCR檢測[J].四川動物,2014(5):715.
[35]張義正,鄧正已,李正昌.林麝的馴化及異地移養[J].中藥材,1985(2):14.
[36]鄧鳳鳴.林麝的馴化與控制放牧[J].野生動物,1986(4):35.
[37]胡,封孝蘭.林麝幼仔集群習性培育試驗初報[J].特產研究,2009(3):5.
篇(2)
關鍵詞:抑郁;遺傳;環境;性別差異
分類號:B845
1 引言
抑郁通常用來指一系列范圍較廣的情緒問題,包括輕微的消極情緒到嚴重的情緒障礙。主要表現為悲傷、苦惱等消極情緒,伴隨著退縮、注意力渙散等行為特征,重性抑郁患者還表現出失眠、厭食等軀體癥狀(cassano&Fava,2002;Compas,Ey,&Grant,1993)。抑郁是個體主要的情緒障礙和心理健康問題之一。在世界范圍內,抑郁也是造成傷殘和疾病負擔的5種主要原因之一(Caspi et al.,2003)。
20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著行為遺傳學的興起,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遺傳因素在抑郁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早期雙生子研究顯示,兒童青少年抑郁的遺傳力約為0.24-0.55(Happonen etal。,2002;Rice,Harold,&Thapar,2002a)。近年來,繼Caspi等人(2003)里程碑式的研究之后,采用分子遺傳學范式探究抑郁的遺傳基礎及其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機制成為抑郁研究領域的前沿課題之一。隨著研究的深入,對于抑郁遺傳基礎的研究不斷獲得新的發現和突破,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就是遺傳因素(Aslund et al.,2009;Eley et al.,2004;Jacobson&Rowe,1999;Jansson et alJ,2004)及其與環境的交互作用(Hammen,Brennan,Keenan-Miller,Hazel,&Najman,2010;sj8berg etal.,2006;Vaske,Beaver,Wright,Boisvert,&Makarios,2009)對抑郁的影響存在顯著性別差異。
考察抑郁遺傳基礎性別差異的表現及其原因,有助于推進抑郁產生機制的研究,對于解釋抑郁的發生特點亦具有重要啟示。鑒于此,本文對既有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進而從性激素、環境敏感性及中間表型3個方面分析性別差異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展望了未來研究的方向。
2 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
通過對該領域相關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定量行為遺傳學研究主要比較抑郁遺傳率的性別差異,較早期的分子行為遺傳學研究考察基因與抑郁簡單關聯的性別差異,隨著研究深入,研究者開始探討抑郁基因一環境交互作用(GxE)的性別差異。鑒于此,本文按照其發展沿革將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基因對抑郁的直接效應,二是基因與環境的交互效應(詳見表1)。
2.1 遺傳直接效應的性別差異
早期研究大多采用數量遺傳學中的雙生子范式考察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雙生子研究通過比較同卵雙生子和異卵雙生子在心理發展特征上的相似程度來了解遺傳和環境對表型變異的相對貢獻,以遺傳率作為衡量遺傳效應大小的指標,即在某一群體的表型變異中,遺傳效應所占的比例(曹叢,王美萍,張文新,陳光輝,2012;Plomin,DeFries,McCleam,&McGuffin,2001)。采用這種范式,Jacobson和Rowe(1999)以自我報告的方式對美國青少年健康追蹤研究中的2302名青少年(平均年齡16歲)雙生子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女性抑郁情緒的遺傳率大于男性。之后,Jansson等人(2004)以1918名瑞典老年雙生子為被試的研究也發現女性抑郁的遺傳率高于男性,而且這種性別差異不受抑郁測評方式(二分法或連續記分法)的影響。此外,Scourfield等人(2003)以兒童青少年(5-17歲)為被試,以母親報告的被試抑郁癥狀為指標,考察了抑郁遺傳率的性別差異問題,其研究結果亦表明女孩的抑郁遺傳率高于男孩。
近年來,隨著分子遺傳學的興起與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分子遺傳學的方法對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進行了考察。目前,大多數抑郁研究考察了5一羥色胺系統基因、多巴胺系統基因與抑郁的關聯,例如5-HTTLPR(serotonin.transporter-linked promoter region,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MAOA(monoamine oxidase A,單胺氧化酶A)基因、COMT(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兒茶酚胺氧位甲基轉移酶)基因和DRD2 (D2dopamine receptor,多巴胺D2型受體)基因等。相關候選基因可以通過降解(如MAOA、COMT)和轉運(如5-HTTLPR)功能調節突觸間隙中5一羥色胺或多巴胺的水平,也可以改變腦內受體數量(如DRD2基因)調節信號傳導,進而影響個體抑郁水平。
該領域的研究為抑郁遺傳基因,特別是5-HTTLPR基因對抑郁影響的性別差異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并且諸多研究一致表明5-HTTLPR基因與女性抑郁存在密切關聯。譬如,Eley(2004)等人以377名10-20歲青少年為被試的研究發現,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SS和SL基因型,研究者按照5-HTTLPR區域上重復序列的數量將基因型劃分為由14個重復序列組成的短等位基因S和由16個重復序列組成的長等位基因L1的女性抑郁水平較低,但是5-HTTLPR基因與男性抑郁無關。Aslund(2009)等人以1482名17-18歲瑞典青少年為被試進行研究,結果亦發現5-HTTLPR基因多態性僅對女性的抑郁存在直接效應,攜帶ss基因型的女性其患抑郁的風險較低,但該基因多態性與男性抑郁無關。Uddin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5-HTTLPR基因僅對女性抑郁存在直接效應,具體表現為攜帶SL基因型的女性抑郁水平較低(Uddin et al.,2010;Uddin。De losSantos,Bakshis,Cheng,&Aiello,2011)。由此可見。5-HTTLPR基因與抑郁的關聯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這些研究結果在具體基因型上仍然存在分歧,這或許與對5-HTTLPR基因rs25531多態性位點功能的劃分有關,需要未來研究進一步進行探討。
需要指出的是,有小部分研究發現某些遺傳基因的直接效應只存在于男性群體中。如Nyman等人(2011)采用北芬蘭出生序列(Northem FinlandBirth Cohort)追蹤研究中的5225名成人為被試。探索多種候選基因與環境風險因素在抑郁發展中的作用,研究結果發現,DRD2基因僅與男性抑郁癥狀顯著相關(Nyman et al.,201 1)。此外,Baekken等人以北特倫德拉格健康研究fNord-TrondelagHealth Study)中的5531名成人為被試,研究COMT基因與焦慮抑郁的關系,結果表明在男性群體中,攜帶Met/Met基因型的個體患抑郁的可能性顯著低于Val/Val基因型攜帶者,但在女性中沒有發現該趨勢(Baekken,Skorpen,Stordal。Zwart,&Hagen,2008)。
綜上所述,雙生子和分子遺傳學研究均表明遺傳因素對抑郁的直接效應存在性別差異.而且分子遺傳學研究資料進一步顯示,不同遺傳基因對男女個體抑郁的影響是不同的,5-HTTLPR可能是女性抑郁的風險基因,而對男性抑郁來說,COMT和DRD2基因的影響可能更大。
2.2 遺傳與環境交互作用的性別差異
采用基因一環境設計考察抑郁的遺傳基礎是當前行為遺傳學研究領域的前沿課題之一,諸多研究表明抑郁的GxE效應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如Barr等人(2004)選擇與人類直系同源的恒河猴為研究對象(恒河猴與人類在5-HTTLPR上具有相同的基因多態性),考察了5-HTTLPR基因與早期不利事件(early adversity)對壓力刺激時的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和皮質醇分泌的影響,結果發現由同伴養育(即早期不利處境)的雌性恒河猴中,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個體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分泌增加,總體皮質醇水平下降(通常這一激素的反應模式被認為與壓力導致的神經障礙有關),但在雄性中沒有出現該反應模式。
除動物研究外,以人類為被試的研究也發現了同樣的性別差異模式。例如,Eley等(2004)和Aslund等人(2009)的研究一致表明5-HTTLPR基因與負性生活事件(失業、重病、喪親等)或虐待對抑郁的交互作用存在性別差異,攜帶S等位基因的女性在遭遇負性生活事件或虐待時,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Hammen等人(2010)以346名青年為被試的研究發現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個體,在15歲時經歷的慢性家庭壓力(父母關系質量、親子關系質量等)越多,其成年后的抑郁水平越高,但這一交互效應只存在于女性群體中。Vaske等人以2023名青少年為被試,考察了DRD2基因TaqlA多態性與壓力性生活事件對抑郁的交互效應,結果僅在非裔美國女性中發現了GxE效應(Vaske et al.,2009)。
然而,也有小部分研究獲得了不同的研究結果。sjoberg等人(2006)以200名青少年(16.19歲)為被試,考察了5-HTTLPR與心理社會壓力f創傷性家庭沖突、父母離異、居住地環境)對抑郁的影響,發現在男性和女性群體中GxE交互作用模式截然相反,在女性中,攜帶s等位基因的個體在經歷了創傷性家庭沖突后其抑郁水平顯著高于未經歷家庭沖突的女性,然而在男性中,當攜帶L等位基因的個體處于風險環境(父母離異或居住條件不良等)中時,其患抑郁的風險較高。與此類似,Brummett等(2008)分別以288名和142名成人為被試進行了兩項研究,結果均發現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在面臨壓力性生活事件(親屬重病、社經地位)時,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而攜帶5-HTTLPR L等位基因的男性在面臨壓力性生活事件時抑郁水平較高。最近,Priess-Grobe和Hyde(2013)以309名青少年為被試,考察了5-HTTLPR基因與負性生活事件(親屬死亡、父母離異等)對抑郁的影響以及MAOA基因與性別的調節作用(5-HTTLPR×負性生活事件×MAOA×性別),也發現在攜帶低活性MAOA基因型的個體中,5-HTTLPR基因與負性生活事件對抑郁的交互作用存在性別差異,攜帶S等位基因的女性經歷的負性生活事件越多其抑郁水平越高,而在經歷了負性生活事件的男性中,只有攜帶L等位基因的個體才表現出抑郁癥狀。以上3項研究似乎表明,面臨壓力時攜帶s等位基因的女孩容易患抑郁,而同樣情況下攜帶L基因的男性患抑郁的風險較高。此外,Nyman等人(2011)的研究結果表明COMT基因rs4680多態性與環境的交互效應僅在男性中顯著,攜帶G等位基因的男性在經歷了環境壓力后抑郁水平較高(Nyman et al.,2011)。
通過分析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抑郁的GxE效應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并且在女性群體中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如在壓力環境下,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的抑郁水平較高。但是,在男性群體中所獲得的結論仍存在分歧。
導致男性群體中既有研究結論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1)多數研究采用的是單基因一環境交互作用的研究范式,而沒有考察多基因的交互效應。人類行為具有復雜的遺傳基礎,多數人類行為并不像單基因遺傳疾病(如亨廷頓舞蹈病)那樣具有清晰簡潔的模式,而是會依賴于環境因素和多種基因的交互作用(McGuffin,Riley,&Plomin,2001)。事實上,已有研究證實了多種基因間存在交互效應,并且提供了與單基因研究不同的結果,如上述Priess-Groben和Hyde(20131的研究結果顯示,同時攜帶低活性MAOA和5-HTTLPR L等位基因的男性在經歷了負性生活事件后抑郁水平較高,這與Aslund等人(2009)的單基因研究結果不一致。(2)研究者所選擇的環境指標不同。多數研究只考察了壓力性生活事件等直接對個體產生影響的近端風險因素(proximalrisk factors,指直接對個體產生影響的社會和身體經驗,如負性生活事件、虐待等),如Eley等(2004)、Aslund等(2009)和Vaske(2009)等人以不利生活事件、虐待等為環境指標,均發現僅在女性群體中存在GxE效應,而少數不一致的研究則選擇了遠端風險因素(distal risk factors,指間接對個體產生影響的歷史、文化、人口及地理特征等因素,如地區貧困水平等),如Uddin等(2010)選擇了地區貧困水平等遠端環境指標,發現僅在男性群體中存在G×E效應,而Moffitt等人指出遠端環境的效應受到近端環境的調節(Moffitt,Caspi,&Rutter,2006),因而近端和遠端風險因素的選擇可能對研究結果具有重要影響。(3)研究對象的年齡不同。Moffitt等人(2006)指出在研究基因與不利環境對抑郁的作用時,年齡可能是導致大部分研究結果不一致的重要因素。如Eley等(2004)、Aslund(2009)等人選擇青少年為被試的研究發現僅在女性群體中存在GxE效應,但是Brummett等(2008)以中老年人為被試的研究卻發現5-HTTLPR基因與壓力的交互作用在男性和女性群體中呈相反的作用模式。
3 抑郁遺傳基礎性別差異的原因
雖然尚未有研究對抑郁遺傳基礎性別差異的原因進行系統的分析總結,但綜述既有文獻資料可以發現,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可能與性激素、個體對不同類型環境的敏感性以及中間表型有關。
3.1 性激素
性激素可能通過以下幾個途徑影響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首先,性激素直接調節基因與抑郁相關生理反應間的關系。Josephs等(2012、以成人為被試通過3種壓力反應實驗(研究1:通過社會排斥誘發地位威脅,研究2:認知失敗,研究3:身體勝任力)考察了5-HTTLPR基因與素對皮質醇水平的交互作用,研究結果均發現在素水平較高時,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個體的皮質醇水平較高,而攜帶LL基因型的個體皮質醇水平較低,但當素水平較低時,兩種基因型的個體皮質醇水平相差不大甚至攜帶LL基因型的個體皮質醇水平更高,這一結果表明5-HTTLPR基因與皮質醇反應的關系受到素的調節,而已有研究顯示重性抑郁患者的皮質醇水平較高(Maes,Jacobs,Suy,Minner,&Raus,1989),這提示我們性激素可能通過調節遺傳基因與抑郁間的關聯,進而影響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性激素對基因~抑郁關聯的影響。
其次,性激素影響抑郁相關基因的表達。研究發現雌激素可以改變對5-羥色胺(serotonin,5-HT)神經遞質有重要作用的基因的表達,這種改變會增加5-HT的合成,減少5-HT的自我阻斷(Pecins-Thompson&Bethea,1998;Pecins-Thompson,Brown,&Bethea,1998)。Gundlah等人通過對切除卵巢的恒河猴進行雌性激素治療(注射雌激素)發現。雌激素的增加會降低中縫核及下丘腦中MAOA基因的表達(Gundlah,Lu,&Bethea,2002),而有研究指出5-HT水平較低的人群更容易產生抑郁(Priess-Groben&Hyde,2013),因而,受雌激素調節的MAOA基因轉錄減少,會增加突觸間隙中5-HT水平,進而影響個體抑郁的發生與發展。
第三,雌激素直接影響5.羥色胺系統的功能。研究者從不同的方面考察了雌激素對5-羥色胺系統功能的影響。首先,雌激素可以影響中腦和下丘腦5-羥色胺受體水平(Beyer et al.,2003;Zhou,Cunningham,&Thomas,2002)。與此一致,Chakravorty和Halbreich(1997)的研究也發現雌激素可以調節5-HT1受體和5-HT2受體,減少單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MAO)活性。其次,雌激素可以增加5-HT的合成(Dickinson&Curzon,1986)。簡言之,雌激素和其他性激素一樣作用于細胞內的雌激素受體(Rubinow&Schmidt,2003),當荷爾蒙與受體相結合時,調節編碼基因的轉錄,制造大量蛋白,而這些蛋白對合成五羥色胺來說恰恰是必不可少的。最后,雌激素還能增強5-HT的活性。如Halbreich等人(1995)發現處于絕經期的女性5-HT的活性顯著降低,而且更易產生情緒障礙,研究同時指出使用雌激素替代療法(注射雌激素)可以顯著減少抑郁的易感性并且增加了5-HT抗抑郁藥物的功效。換言之,雌激素在5-HT功能上的累積效應就如同這一系統的激動劑(agonist)(Halbreich,1997)。
值得指出的是,抑郁的性別差異通常出現在青春期,表現為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水平高于男孩(Uddin et al.,2011;Piccinelli&Wilknson,2000),但是這一時期女孩的雌激素是升高的,這與上述研究中提到的“低雌激素水平與抑郁有關”相矛盾。對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由于女性在青春期時雌激素迅速升高,導致雌激素內穩態(estrogenhomeostasis)紊亂,而這一紊亂會擾亂五羥色胺的合成過程并引緒障礙(Halbreich&Kahn,2001)。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性激素與抑郁的關系可能是非線性的。如一項男性研究指出素水平與抑郁癥的關系呈u型曲線,即素水平過高或者過低,個體的抑郁水平較高(Booth,Johnson,&Granger,1999)。
3.2 環境敏感性的性別差異
眾所周知,環境因素(如壓力性事件)是抑郁的重要預測源。如前所述,遺傳和環境對抑郁的交互作用存在性別差異,這既與特定遺傳基因對兩性存在不同影響有關,也可能與男女對環境的敏感性不同有關。一項對346名青年人的研究發現,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其經歷的慢性家庭壓力(如父母爭吵等)越多,患抑郁的可能性越大,但這一GXE效應在男性中并不存在。換言之,相比男性,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對家庭人際關系(如父母婚姻質量和親子關系質量)更為敏感(Hammen et al.,2010)。然而,Uddin等人(2010)以1084名青少年為被試的研究則發現,當地區貧困水平(該地區接受公共救助家庭的比例)較高時,攜帶5-HTTLPR SL基因型的男性患抑郁的風險較低,而這一GXE交互作用在女性群體中并不顯著,這與Hammen等人(2010)的研究結論截然相反。通過分析上述研究方法可以發現,兩項研究選擇的環境指標存在差異,前者選擇的是家庭環境變量,而后者選擇的為社會環境變量。這些研究結果提示,男女對不同類型的環境敏感性可能存在差異。Sjoberg等人(2006)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該假設的合理性。他們采用不同類型的環境指標(創傷性家庭沖突、父母離異、居住地環境)發現,攜帶5-HTTLPR L等位基因的男性更容易受到公共居住環境和父母離異的消極影響,而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則更容易受到傷害性家庭沖突(與父母或兄弟姐妹的關系等)的影響。
結合上述研究可推知,在宏觀社會環境水平(如社區環境)上,男性的敏感性要大于女性,但在人際關系及家庭水平的環境變量上,女性的敏感性要高于男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離婚這一環境指標上,男性的敏感性更高。雖然既有研究表明男女對不同類型的環境敏感程度存在差異,但大多相關研究測量的是女性較為敏感的環境變量。此外,多數研究只考察了消極環境變量的作用,忽略了積極環境對個體抑郁性別差異的貢獻:而已有研究發現在社會支持水平較高的環境下.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個體患抑郁的風險較低(Kaufman et al.,2004)。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探究不同類型和不同性質的環境指標對抑郁遺傳基礎性別差異的作用。
3.3 中間表型(intermediate phenotype)
中間表型(intermediate phenotype)是內在的、可遺傳的、穩定的個人特質,如神經生理結構、生物化學成分、認知等,與心理障礙、精神疾病等密切相關(Meyer-Lindenberg&Weinberger,2006)。正如心理學家Uher和McGuffin(2008)所言,中間表型比外在的心理癥狀更具有遺傳性,對中間表型的研究將會擴展和深化已知的基因一環境交互作用。近期,已有研究表明基因對抑郁的效應可能受到注意偏好、消極推理風格等中間表型的調節。如Gibb Uhrlass,Grassia,McGeary和Benas(2009)的一項研究發現,5-HTTLPR基因、兒童推理風格和母親情緒性批評三者存在交互作用,具體表現為在具有消極推理風格的兒童中,攜帶5-HTTLPR SS基因型的個體經歷的母親情緒性批評越多,其抑郁水平越高。Gibb,Benas和Grassia(2009)的另一項研究還檢驗了5-HTTLPR基因、母親抑郁病史與兒童注意偏好之間的聯系,結果也發現母親抑郁水平越高,攜帶5-HTTLPR S等位基因且同時表現出對悲傷面孔注意回避的兒童患抑郁的可能性更大。伴隨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神經成像技術的廣泛應用,研究者開始考察腦功能、腦結構等中間表型與抑郁遺傳基礎的關聯。由于杏仁核活性與個體抑郁有關(Lonsdorf et al.,2009),因此通過考察5-HTTLPR基因與杏仁核活性關聯的研究可以推知中間表型對遺傳效應的調節作用。Lemogne等人(2011)的研究發現在不同的認知評估任務中,5-HTTLPR基因與生活壓力對杏仁核活性的作用模式相反,具體表現為,在自我指向的認知評估任務中,隨著生活壓力的增加,S等位基因攜帶者的杏仁核活性降低,而LL基因型攜帶者的杏仁核活性增強;但在情緒標簽的認知評估任務中,隨著生活壓力的增加,s等位基因攜帶者的杏仁核活性增強,LL基因型攜帶者的杏仁核活性則降低。此外,情緒系統中其他腦結構與基因的關聯也備受關注(Cole et al.,2011;Andms et al.,2012;Drabant et al.,2012),如Drabant等人(2012)考察了大腦邊緣系統與5。HTTLPR基因的關聯,結果發現,與攜帶5-HTTLPR L等位基因的女性相比,攜帶sS基因型的女性在面臨壓力情境時表現出杏仁核、海馬、前腦島、丘腦、丘腦后結節、尾狀核、楔前葉、前扣帶回和內側前額葉等腦區活性的顯著增強,而這些腦區活性的增強與焦慮抑郁密切相關。
上述研究表明遺傳效應可能受到中間表型的調節,并且既有研究發現中間表型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如在青少年階段具有消極歸因風格的女性要顯著多于男性(Hankin&Abramson,2002;Nolen-Hoeksema&Girgus,1994),并且在女性群體中消極歸因風格與抑郁的聯系比在男性中更為密切(Gladstone,Kaslow,Seeley,&Lewinsohn,1997)。除了消極歸因風格外,反思(rumination)傾向也是抑郁的特征之一(Nolen-Hoeksema,2000),一項關于成人的追蹤研究發現反思傾向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的反思傾向顯著高于男性(Nolen-Hoeksema,Larson,&Grayson,1999),這些研究結果提示,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可能部分歸因于中間表型的性別差異。
4 小結與展望
抑郁具有復雜的遺傳基礎,不論是遺傳直接效應還是遺傳一環境的交互作用均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盡管一些具體結論還存在分歧。本文通過綜述已有文獻,從性激素、環境敏感性及個體中間表型三方面討論了抑郁遺傳基礎性別差異的可能原因。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未來研究應該更加關注如下問題:
(1)采用多基因一環境設計考察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
由前可知,多數研究采用的是單基因一環境交互作用的研究范式,即使有的研究(Eley et al.,2004;Nyman et al.,201 1)同時考察了多種基因,也僅僅是分析單個基因與環境對抑郁的影響,并沒有考察多種基因的交互效應。然而,神經遞質之間的功能關系十分復雜,一種遞質功能紊亂可能引起另外一種或幾種遞質的功能失衡,從而導致一定的病理生理現象(王美萍,張文新,2010)。不同基因間存在交互效應,如Kaufman等人(2006)的一項研究就發現BDNF(brain derived neurophicfactor,腦源性神機更營養因子)和5-HTTLPR基因對個體抑郁存在交互效應。如前所述多基因研究與單基因研究的結果也往往不同,因此未來研究應盡可能采用多基因一環境設計更深入地考察抑郁的遺傳基礎及其性別差異。
(2)考察不同類型和性質的環境與遺傳基因交互影響抑郁的性別差異。
如前所述,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可能是個體對不同類型的環境的敏感性存在差異造成的,多數研究并沒有給男性敏感的環境變量以足夠的重視,因此未來研究應同時采用男性和女性的敏感環境因素,考察其在抑郁遺傳基礎中的效應。此外,現有抑郁的分子遺傳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多是“素質一壓力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由于該模型認為,當個體處于應激或高壓狀態時,具有某種不良遺傳素質的個體更容易發生心理與行為問題,因而以該模型為理論基礎的研究多以壓力性生活事件等消極環境為指標來考察抑郁的GxE效應(Aslund et al.,2009;Caspi et al.,2003;Beach et al.,2010)。然而,新近興起的理論模型——“不同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model)明確提出并證明,某些基因型的個體也更容易受到積極成長環境的影響而表現良好或優秀(Belsky&Pluess,2009;Ellis,Boyce,Belsky,Bakermans-Kranenburg,&van Ijzendoom,2011)。因此,現有以“素質一壓力模型”為理論基礎的研究未能揭示GxE交互作用的多種可能方式,攜帶不同基因型個體對積極環境的敏感性是否存在性別差異也是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重點考察的內容。
(3)抑郁遺傳基礎的性別差異的發展變化。
篇(3)
[關鍵詞] 馬方綜合征;分子遺傳學;基因檢測;研究進展
[中圖分類號] R59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04(c)-0015-04
Recent molecular genetics research progress in Marfan syndrome
LI Bao-zhu SHU Xiao-rong CHEN Ren-hua WANG Jing-feng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120,China
[Abstract] Marfan syndrome(MFS)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ly inherited connective tissue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ocular,skeletal manifestations and cardiovascular.The severe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re the main lethal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MFS.The study found that original fibrin(FBN)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receptor(TGFBR) gene families are the main mutations in MFS.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mutant genes,detection methods of mutation,correlation of genotype and phenotype,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MF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rfan syndrome;Molecular genetics;Gene detection;Research progress
馬方綜合征(Marfan syndrome,MFS)亦稱為先天性中胚層發育不良、蜘蛛指征、肢體細長癥、Marchesani綜合征,是一種以結締組織為基本缺陷的遺傳性疾病,具有基因多態性和多種臨床表征,發病率為0.2‰~0.3‰。MFS主要表現為周圍結締組織營養不良、內眼疾病、骨骼異常和心血管異常[1],病變有時也累及皮膚、肺部及硬腦脊膜等器官[2-5],癥狀主要有骨骼過長,晶狀體異位,主動脈瓣反流和較嚴重的新生兒馬方綜合征等。現就MFS的突變基因家族、突變基因的檢測方法、基因型與表型的相關性及后續展望作如下綜述。
1 突變基因家族
現如今已發現8種涉及MFS的基因,共3843種基因突變體(表1)。目前,研究最多的和引起MFS發病的主要突變基因家族是原纖維蛋白(the original fibrin,FBN)基因家族和轉化生長因子β受體(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receptor,TGFBR)基因家族。
1.1 FBN基因家族與MFS
1986年,Sakai等[6-7]發現一種作為微纖維蛋白重要組成部分的細胞外基質糖蛋白,將其命名為FBN。其在細胞外基質以聚合體形式形成微纖維蛋白,存在于骨骼、眼睛、血管壁等人體彈性和非彈性組織中。1990年,Hollister等[8]通過FBN單克隆抗體,發現了MFS患者微纖維蛋白系統的異常。1991年,Magenis等[9]應用原位雜交技術,成功定位并克隆了FBN基因,并首次檢測到2例MFS患者的原纖維蛋白基因1(the original fibrin 1,FBN1)基因突變。
MFS患者常伴有彈性組織中無定形基質聚集和彈性纖維斷裂現象,研究發現,基質原纖維蛋白-1(fibrillin-1,FBN-1)是參與這一發病機制的重要因素[6],FBN1是最早發現、最常見且突變體最多的MFS致病基因。FBN1位于15號染色體長臂(15q15-q21.1),含有65個外顯子,長230 kb,轉錄大小為10 kb的mRNA,翻譯為2871個氨基酸的蛋白質(表2)[9]。
表2 FBN1基因的突變類型及數量
目前為止,已發現FBN1基因突變3077種,記錄于FBN1 mutations databate(http://umd.be/FBN1/)。FBN1突變可發生于基因的任何區域,無明顯突變熱點,只有約12%的突變基因有可重現性,由此給基因篩查突變增加了難度[10]。基因分為編碼區和非編碼區,FBN1基因編碼區突變約占總突變的80%,非編碼區突變約占總突變的20%。常見編碼區突變有移碼突變、錯義突變和無義突變,移碼突變和錯義突變約占編碼突變的80%,無義突變約占編碼突變的20%。無義突變導致的終止密碼子的提前出現,使得突變轉錄子被一種RNA監視機制所降解,進而導致翻譯的蛋白量僅為正常的50%,且翻譯所得異常蛋白單體干擾正常蛋白單體的聚合[11-12]。這些無義突變可以導致MASS癥狀,包括近視、二尖瓣脫垂、主動脈根部膨大、骨骼皮膚異常等[13]。非編碼區突變主要發生在剪接位點,保守區剪接位點突變約占20%。剪接位點突變易引起內含子內假外顯子的出現、內含子保留、隱蔽剪接位點激活和外顯子跳躍等剪接錯誤,蛋白結構域的錯誤和缺失會導致嚴重的臨床病癥出現[14]。
FBN1突變雖然沒有區域特異性,但外顯子57和65發生突變較少,外顯子13、26和27發生突變較多[15]。FBN1基因突變最常見的類型是點突變,約占所有突變的73%,其中,錯義突變約占59%,無義突變約占14%。FBN1的突變可引起多組織器官的病變,如心血管、顱面部、中樞神經系統、肺部、眼部、骨骼和皮膚等。
1.2 TGFBR基因家族與MFS
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家族介導的信息傳遞控制著細胞繁殖、分化和凋亡等多種程序。2004年,一個具有與MFS部分相似臨床癥狀的患者,在排除FBN1和FBN2基因變異后,發現其家系中編碼轉化生長因子β受體2(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 receptor 2,TGFBR2)的基因染色體發生斷裂[16]。具有與MFS相似的骨骼和心血管表現,且TGFBR基因家族發生突變的綜合征被稱為MFS 2型[17]。此類MFS具有與細胞外基質TGF-β信息傳遞相關的結締組織疾病,從而導致致命的主動脈并發癥。通過新型藥物對MFS患者TGF-β信息傳遞功能進行適當調整,也許可以維持患者的健康心血管狀態或者延遲致命病變[18-19]。
2 突變基因的檢測方法
MFS患者癥狀表現呈多樣性,主要表現為晶狀體異位、骨骼過長、主動脈瓣反流等。目前,MFS的臨床診斷依然主要依據1996年制定的Ghent診斷標準,該診斷包括對骨骼、眼部和心血管三個主要系統的診斷以及皮膚、肺和硬腦脊膜等次要系統的診斷。由于MFS發病癥狀與年齡密切相關,有些患者嬰兒和(或)兒童時期并未表現出癥狀,且很多患者并不符合診斷標準,因此,MFS基因診斷在輔助臨床診斷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MFS檢出率主要受其臨床診斷正確性、基因突變類型、臨床基因檢測方法和水平的影響。臨床基因檢測MFS時,通常檢測FBN1基因序列的突變情況,MFS患者FBN1基因突變檢出率占73%~90%。
目前,突變基因的常用檢測方法有變性高效液相色譜分析(denatur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DHPLC)、變性梯度凝膠電泳(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DGGE)、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分析(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構象敏感凝膠電泳(conformation sensitive gel electrophoresis,CSGE)、單鏈構象多態性分析(single-strand conformation polymorphism,SSCP)、高分辨率溶解曲線(high resolution melting cure,HRM)、多重連接探針擴增技術(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和直接測序等。
DHPLC檢測具有自動化、高通量、高靈敏度、高特異性、檢測速度快和價格低廉等特點,適用于基因突變的大規模篩查,檢測未知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可達到95%以上。DGGE法檢測對各種突變特別是點突變較敏感,檢測時無需標記,并且幾乎可以檢測出所有突變,但無法確定突變位置,DN段大小限制在100~500 bp,需要專門設備檢測且需要計算機對序列進行分析。RFLP法可用于證實患者的突變位點,為產前診斷提供確切診斷依據。DGGE、RFLP、CSGE和SSCP等方法的基因突變檢出率為60%~90%,且檢測過程相對繁瑣。HRM檢測無需基因序列特異性探針,不受堿基位點的局限,可以同時檢出已知或未知突變與SNP,靈敏度和精確度高達100%。但是HRM需專業儀器,技術要求高,反應條件摸索費時費力。MLPA法可以用于拷貝數異常的檢測。直接測序法價格相對較貴,不適合大樣本基因突變篩查,但可以確定突變基因位點和類型,是突變檢測的金標準。
基因cDNA序列篩查突變基因,不僅可以檢測整個編碼區基因突變,還可以檢測基因剪接位點的突變。cDNA篩查方法檢測FBN1基因突變的檢出率達90%。應用CSGE、DHPLC和直接測序等方法不僅可以檢測基因組DNA(genomic DNA,gDNA)中的突變基因,還可以檢測導致RNA快速降解的基因。gDNA篩查方法檢測FBN1基因突變的檢出率達70%~93%[15]。MFS基因突變體具有多樣性,作為常規檢測MFS的FBN1基因外顯子多、基因大、沒有突變熱點,給突變篩查帶來難度,且突變篩查可能存在假陽性[20-21]。
3 基因型與表型的相關性
由FBN1基因突變與心血管表型特征相關性可知,FBN1基因突變主要引起主動脈和二尖瓣病變,如主動脈擴張、主動脈夾層、主動脈閉鎖不全、二尖瓣反流和二尖瓣脫垂等。而FBN1等位基因的完全缺失并不預示著溫和表型的出現,且單倍基因劑量不足也可導致典型MFS表型[22]。研究表明,MFS患者的預后取決于疾病的臨床表現和治療,而不是簡單地取決于TGFBR2突變的存在與否[23]。TGFBR2基因發生突變的MFS患者臨床癥狀表現傾向于肢體細長和具有心血管疾病,但沒有眼部病癥[17]。MFS表現型復雜多變,即使同一家系同一等位基因的突變,也會出現嚴重程度不同的表型,因此,到目前為止,通過某一特定突變基因推測其表型還不可能。由此可見,除了突變基因,MFS患者的表型還可能受環境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4 MFS的主要致死病變及新生兒MFS
患者的致死病變主要在心血管系統,且死亡年齡與心血管病變程度有關。MFS的心血管疾病病癥主要表現為二尖瓣脫垂、二尖瓣反流、主動脈根部擴張和主動脈瓣反流等,主要危及生命的心血管并發癥是主動脈和主動脈夾層動脈瘤,約1/3的MFS患者有二尖瓣脫垂和(或)主動脈根部擴張的并發癥[24-26]。若不提前干預治療,病程發展快且易危及生命。
新生兒MFS病癥往往表現最嚴重,主要包括指細長、手指屈曲性痙攣、胸部畸形、早衰面容、心臟瓣膜反流和鄰近主動脈擴張等,易導致新生兒因心力衰竭致死[27-28]。FBN1基因24~32外顯子突變被認為是導致新生兒MFS的主要突變基因[29]。MFS患者有正常的生育能力,因此,對家族遺傳性MFS患者及家系成員進行基因檢測,確定突變基因位點,對于指導患者及其家屬婚育和對其后代進行產前診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5 展望
MFS的發病機制尚未清晰,其基因型和表型之間的差異表明環境等因素可能影響其表型。基因組學、后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和環境基因組學的研究表明,大多數疾病由基因突變和環境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通過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和生物信息學等技術的應用,從基因、蛋白、細胞、組織、器官、家系和環境等方面進行研究,利于進一步確定MFS的發病機制和遺傳特征。對MFS先證者家屬進行突變基因單倍型分析和基因檢測,提前對MFS患者進行干預治療,不僅可以進行提前診斷、減緩病程發展,還可以為后續基因治療、藥物靶點治療和組織工程修復等奠定研究基礎,為臨床新藥應用、生物療法和基因療法等提供科學依據。
[參考文獻]
[1] Pyeritz RE,McKusick VA.The Marfan syndrome:diagnosis and management[J].N Engl J Med,1979,300(14):772-777.
[2] Weir B.Leptomeningeal cysts in congenital ectopia lentis:case report[J].J Neurosurg,1973,38(5):650-654.
[3] Newman PK,Tilley PJ.Myelopathy in Marfan′s syndrome[J].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1979,42(2):176-178.
[4] Cilluffo JM,Gomez MR,Reese DF,et al.Idiopathic("congenital")spinal arachnoid diverticula.Clinical diagnosis and surgical results[J].Mayo Clin Proc,1981,56(2):93-101.
[5] Yellin A,Shiner RJ,Lieberman Y.Familial multiple bilateral pneumothorax associated with Marfan syndrome[J].Chest,1991,100(2):577-578.
[6] Sakai LY,Keene DR,Engvall E.Fibrillin,a new 350-kD glycoprotein is a component of extraeellular mierofibrils[J].J Cell Biol,1986,103(6):2499-2509.
[7] Zhang H,Apfelroth S,Hu W,et al.Structure and expression of fibrillin-2 novel microfibrillar component preferentially located in elastic matrices[J].J Cell Biol,1994,124(5):855-863.
[8] Hollister DW,Godfrey M,Sakai LY,et al.Immunohistologic abnormalities of the microfibrillar-fiber system in the Marfan syndrome[J].N Engl J Med,1990,323(3):152-159.
[9] Magenis RE,Maslen CL,Smith L,et al.Localization of the fibrillin(FBN) gene to chromosome 15,band q21.1[J].Genomics,1991,11(2):346-351.
[10] Collod-Béroud G,Le Bourdelles S,Ades L,et al.Update of the UMD-FBN1 mutation database and creation of an FBN1 polymorphism database[J].Hum Mutat,2003,22(3):199-208.
[11] Thermann R,Neu-Yilik G,Deters A,et al.Binary specification of nonsense codons by splicing and cytoplasmic translation[J].Embo J,1998,17(12):3484-3494.
[12] Collod-Béroud G,Boileau C.Marfan syndrome in the third millennium[J].Eur J Hum Genet,2002, 10(11):673-681.
[13] Dietz HC,McIntosh I,Sakai LY,et al.Four novel FBN1 mutations:significance for mutant transcript level and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 of FBN1 mutations 159 EGF-like domain calcium binding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arfan syndrome[J].Genomics,1993,17(2):468-475.
[14] Smallridge RS,whiteman P,Werner JM,et al.Solution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a calcium binding epidermal growth factor-like domain pair from the neonatal region of human fibrillin-1[J].J Biol Chem,2003,278(14),12199-12206.
[15] 崔婉婷,金春蓮.馬方綜合征的基因突變篩查及其應用研究[A]//第八次全國醫學遺傳學學術會議(中華醫學會2009年醫學遺傳學年會)論文摘要匯編[C].北京:中國遺傳學會,2009.
[16] Mizuguchi T,Collod-Béroud G,Akiyama T,et al.Heterozygous TGFBR2 mutations in Marfan syndrome[J].Nat Genet,2004,36(8):855-860.
[17] Boileau C,Jondeau G,Babron MC,et al.Autosomal dominant Marfan-like connective-tissue disorder with aortic dilat ion and skeletal anomalies not linked to the fibrillin genes[J].Am J Hum Genet,1993,53(1):46-54.
[18] 方凱,陳玉成,曾智.馬方綜合征分子基因研究進展[J].華西醫學,2007,22(1):191-192.
[19] 王雪濤.漢族馬方綜合征患者基因突變及臨床特征的研究[D].福州:福建醫科大學,2012.
[20] Mátyás G,De Paepe A,Halliday D,et al.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naturing HPLC for mutation detection in Marfan syndrome:Identification of 20 novel mutations and two novel polymorphisms in the FBN1 gene[J].Hum Mutat,2002,19(4):443-456.
[21] K■rkk■ J,Kaitila I,L■nnqvist L,et al.Sensitivity of conformation sensitive gel electrophoresis in detecting mutations in Marfan syndrome and related conditions[J].J Med Genet,2002,39(1):34-41.
[22] Hilhorst-Hofstee Y,Hamel BC,Verheij JB,et al.The clinical spectrum of complete FBN1 allele deletions[J].Eur J Hum Genet,2011,19(3):247-252.
[23] Attias D,Stheneur C,Roy C,et parison of 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outcom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TGFBR2 and FBN1 mutations in Marfan syndrome and related disorders[J].Circulation,2009,120(25):2541-2549.
[24] Brown OR,DeMots H,Kloster FE,et al.Aortic root dilatation and mitral valve prolapse in Marfan′s syndrome:an ECHOCARDIOgraphic study[J].Circulation,1975,52(4):651-657.
[25] Pyeritz RE,McKusick VA.The Marfan syndrome:diagnosis and management[J].N Engl J Med,1979,300(14):772-777.
[26] 高凌根.馬方綜合征與Liddle綜合征分子遺傳學與臨床研究[D].北京:北京協和醫學院,2011.
[27] Buntinx IM,Willems PJ,Spitaels SE,et al.Neonatal Marfan syndrome with congenital arachnodactyly,flexion contractures,and severe cardiac valve insufficiency[J].J Med Genet,1991,28(4):267-273.
[28] 牛子儒.馬方綜合征植入前遺傳學診斷技術初步研究[D].北京:中國人民醫學院,2013.
篇(4)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強迫癥狀;病因學;臨床表現
近10年來,國內外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強迫癥狀的研究較多,為了解其系統研究的現狀,作者對其發生率、病因學、臨床表現及治療進行了簡要綜述。
1 OCSS的概念
Obsessive是指反復出現的觀點、思想、沖動、意象;Compulsive是指反復出現的、有目的的、有意識的動作行為。在美國的精神病診斷系統中將Obsessive和Compulsive統稱為強迫癥狀(OCS)。OCS在強迫癥(OCD)及精神分裂癥、抑郁癥、焦慮癥等疾病中的發生率較高。本文主要介紹精神分裂癥的強迫癥狀(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OCSS)。
2 OCSS的發生率
國內OCSS的發生率為1.7%~13.2%。唐瑞春[1]報道3595例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中61例(1.7%)有強迫癥狀;劉建勛等[2]報道3.9%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有強迫癥狀;李曉菊[3]報道5.3%的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有強迫癥狀;劉紅等[4]發現13.2%的兒童精神分裂癥患者有明顯的強迫癥狀;國外報道[5] OCSS的發生率為13%~40%。說明強迫癥狀是精神分裂癥的常見癥狀之一。
3 OCSS的可能病因學
3.1 強迫癥狀與腦結構異常改變 早在1992年YaLe大學的Woods[6]對以強迫癥狀為主要表現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的大腦血流影響學研究發現,患者的大腦基底節前扣帶回、前額葉皮質的結構和功能異常。1999年美國加洲San Tose腦研究中心的Joseph[7]把有強迫癥狀的精神分裂癥和無強迫癥狀的精神分裂癥分成兩組,對照性的研究其腦結構和腦功能,發現有強迫癥狀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腦結構的改變明顯,其基底節、紋狀體、前額葉的功能明顯障礙。
3.2 強迫癥狀與高香草酸 1994年Oades[8]研究發現,以強迫癥狀為主要表現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尿中高香草酸(HAV)的濃度增高。HAV為腦中多巴胺(DA)的代謝產物,HAV的濃度增高說明腦中的DA濃度及活性增高。Oades同時還發現患者血清5羥色胺(5HT)的濃度明顯增高,說明患者腦內DA與5HT功能亢進。1995年Toren P等[9] 提出OCSS的產生可能與5HT功能低下或失調有關。2000年徐貴云等[10]提出OCSS的產生可能與5HT和DA功能失調有關。但是,OCSS與5HT和DA的確切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
3.3 強迫癥狀與分子遺傳學 1999年Bengel[11]從分子遺傳學方面研究了強迫癥患者和正常對照組5HT轉運子(5HTT)5′端調節區域多態性,結果發現強迫癥患者5HTT的等位基因I與對照組存在明顯差異(46.7%/32.3%,χ2=5.19,P
4 OCSS的臨床表現
OCSS的強迫思維內容荒謬,這與精神分裂癥的病態思維相關。患者無焦慮、痛苦及求治愿望,自知力不全。而強迫癥的強迫癥狀內容接近現實,不荒謬,患者十分痛苦,自知力完整,治療要求迫切。下面,我們通過表1,表2來說明OCSS表現。
表1 61例OCSS表現[1](略)
5 OCSS的治療
近幾年的研究傾向于應用抗精神病藥物合并抗強迫癥藥物治療OCSS。其理由為抗強迫癥藥物可直接減輕強迫癥狀,同時可增強抗精神病藥物的血藥濃度[12]。Reznik I等[13]將30例存在OCSS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隨機分為兩組,一組給予安定藥物加氟伏沙明,另一組給予安定類藥物。治療8 w后氟伏沙明組PANSS總分減少34.3%,YBOCS評分減少29.4%,兩組療效比較差異有顯著性。徐貴云等[14]將75例合并OCSS的患者分為利培酮合并安慰劑組(對照組)與利培酮合并氯丙咪嗪組(實驗組)進行治療,發現對照組總有效率為82.9%,顯效率為68.6%;實驗組總有效率為93.7%,顯效率為89.2%。兩組比較差異有顯著(P
對于藥物治療無效的強迫癥患者實施神經外科治療可能更為有效。而內囊毀損術治療難治性強迫癥已有30年的歷史,有報道顯示[16],其總有效率可達55%~78%。內囊毀損術主要是通過干擾額葉丘腦通路或破壞眶額皮質,恢復眶額丘腦間連接系統、額葉尾狀核蒼白球丘腦系統之間的平衡而達到治療目的。那么是否可以應用內囊毀損術治療經藥物治療無效的OCSS哪?
6 結語
OCSS在精神分裂癥中較常見,此類患者的大腦基底節、紋狀體及前額葉的結構與功能均有明顯障礙,其病理過程的產生可能與5HT及DA功能失調有關,但目前還不十分明確。那么是否可通過嘗試研究5HTT基因的異常來探索OCSS的發病機制哪?應用抗精神病藥物合并氯丙咪嗪或SSRI類抗抑郁劑治療效果較好,但對經藥物治療無效的患者,是否可以嘗試神經外科手段治療,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 唐瑞春,楊家良.具有強迫癥狀的精神分裂癥61例對照研究[J].四川精神衛生,1994,7(2):81
[2] 劉建勛,李蓮芳.精神分裂癥的強迫癥狀臨床分析[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1996,22(1):25
[3] 李曉菊.精神分裂癥的強迫癥狀[J].臨床精神醫學雜志,2003,13(1):37
[4] 劉紅,羅隕軍,林節.兒童精神分裂癥的強迫癥狀臨床分析[J].四川精神衛生,1995,8(4):232
[5] Berman L, Merson A,Viegner B,et al.Obsession and compulsions as a distinct cluster of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a neuropsychological study[J].J Nery Ment Dis,1998,186:150
[6] Woods SW. Obsessive and Compulsive in schizophrenia A Study on Cerebrum blood stream phantom[J].J Clin Psychiatry,1992,53:20
[7] Oades RD. The brain changes comparison research in schizophrenia[J].J Neural Tramsm Gen Sect,1994,96:2143
[8] Joseph. Case study:biochemistry abnor chang on Obsessive and Compulsive in schizophrenia[J].Psychiatry,1999,62:138
[9] Toren P,Sarruel E,Weizman R,et al.Case study:emergence of transient compulsive symptoms during treatment with clothiapine[J].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1995,34(11):1469
[10] 徐貴云,馬崔.精神分裂癥的強迫癥狀[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01,27(1):76
[11] Bengel D. Obsession in molecular genetics comparison research[J].Mol Psychiatry,1999,4:463
[12] Zohar J, Kaplan Z, Benjamin J. Clomipramine treatment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symptomatology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J].J Clin Psychiaty,1993,54(10):385
[13] Reznik I, Sirota P.Obsessive And Compulsive in Schizophrenia a randomized with fluvoxamine and neuroleptics[J].J Clin Psychopharmacol,2000,20(4):410
[14] 徐貴云,馬崔.利培酮治療精神分裂癥強迫癥狀的對照研究[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01,27(2):129
篇(5)
關鍵詞:人類基因組 基因克隆 基因組學 結構基因組 功能基因組
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HGP)是由美國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Renato dulbecco于1986年在雜志《Science》上發表的文章中率先提出的,旨在闡明人類基因組脫氧核糖核酸(DNA)3×109核苷酸的序列,闡明所有人類基因并確定其在染色體的位置,從而破譯人類全部遺傳信息。美國于1990年正式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估計到2003年完成人類基因組全部序列測定。歐共體、日本、加拿大、巴西、印度、中國也相繼提出了各自的基因組研究計劃[1]。由于各國政府和科學家的共同努力,HGP目前已在為全球范圍的合作項目;隨著數理化、信息、材料等學科的滲透和工業化管理模式的引進,HGP已真正成為生命科學領域的科學工程,基因組(genomics)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也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科學界也在思索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后的下一步工作,因此就有了“后基因組計劃”(post-genome project)的提法。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原定于2003年所完成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只是一個以測序為主的結構基因組學(structural genomics)研究,而所謂的“后基因組計劃”應該是對基因功能的研究,即所謂的功能基因組學(functional genomics)。此外,一些新的概念如:“蛋白質組(proteome)”、“環境基因組學(environmental genomics)”和“腫瘤基因組解剖學計劃(cancer genome anatomy project,CGAP)”等等也在不斷向外延伸。
一、結構基因組學
(一)人類基因組作圖
人類基因組作圖根據使用的標記和手段不同,初期的作圖有二種:一是通過計算連鎖的遺傳標記之間重組頻率而確定它們相對距離的遺傳連鎖圖,一般用厘摩(cM)來表示;二是確定各遺傳標記之間物理距離的物理圖,一般用堿基(bp)或千堿基(kb)或兆堿基(Mb)來表示。1cM的遺傳距離大致上相當于1Mb的物理距離。隨著研究工作的進展,遺傳圖和物理圖逐漸發生整合,在此基礎上大量引入基因標記,從而形成了新一代的轉錄圖[1]。
1.遺傳連鎖圖 遺傳連鎖圖(genetic map)繪制需要遺傳標記,早期的遺傳標記主要為生化標記,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RFLP)、串聯重復序列拷貝多態性和小衛星重復順序等遺傳標記為主,這類標記的數量較少,信息也較低;20世紀80年代后期發展的短串聯重復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TR)也稱微衛星(microsatellite,MS)標記,主要為二核苷酸重復序列,如:(CA)n,它們在染色體上分布較均勻,信息含量明顯高于RFLP,因而成為遺傳連鎖分析極為有用的標記;近年來,單個堿基的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標記又被大量使用,其意義已超出了遺傳作圖的范圍,而成為研究基因組多樣性和識別、定位疾病相關基因的一種新標記。
2.物理圖 物理圖(physical map)包含了兩層意義,一是獲得分布于整個基因組的30000個序列標簽位點(sequence tagged site,STS),這可使基因組每隔100kb距離就有一個標記;二是在此基礎上構建覆蓋每條染色體的大片段DNA克隆,如:酵母人工染色體(yeast ar tificial chromosome,YAC)或細菌人工染色體(bacterial artificial chromosome,BAC)、人工附加染色體(human artificial episomal chromosome,HAEC)和人工噬菌體染色體(P1 bacteriophage artificial chromosome,PAC)等連續克隆。這些圖譜的制作進一步定位其它基因座提供了詳細的框架[2]。
3.轉錄圖 構建轉錄圖的前提條件是獲得大量基因轉錄本即信使核糖核酸(mRNA)的序列,人類基因組中的基因數目約在10萬左右,構建轉錄圖首先需要獲得人類基因的表達序列標簽(expressed sequence tag,EST),以此建立一張人類的轉錄圖,并與遺傳圖的交叉參照。
4.DNA序列的生物信息學 HGP一開始就與信息高速公路和數據庫技術形成了同步發展。迄今,國際上四個大的生物信息中心即美國的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CBI)、基因組序列數據庫(GSDB)、歐洲分子生物實驗室(EMBL)和日本DNA數據庫(DDBJ)已經建立和維持了源自數百種生物的互補DNA(cDNA)和基因組DNA序列的大型數據庫。這些中心和全球的基因組研究實驗室通過網點、電子郵件或者直接與服務器和數據庫聯系而獲得的搜尋系統,使得研究者可以在多種不同的分析系統中對序列數據庫提出質詢,這些分析包括基因的發現、蛋白質模體的鑒別、調控元件的分析、重復序列的鑒別、相似性的分析、核苷酸組成的分析以及物種間的比較等。
(二)基因組的基本結構和進化
人類基因組研究的目的,不僅為了單純地積累數據,而且要提示數據中所蘊藏的內在規律[3],從而更好地認識生命體。近年來,隨著模式生物體測序的相繼完成和人類基因組測序速度的加快(到1999年12月已宣布完成人類第22號染色體的完全測序),特別是生物信息所提供的強有力的分析和綜合手段,使人人能夠逐漸透過浩瀚的基因組序列信息,去探索一些更為本質的問題,如:基因組的復雜度與生物進化、基因組編碼序列的結構、基因和蛋白家族、基因家族的大小及其進化。
(三)疾病的基因組學
HGP的直接始動因素是要解決包括腫瘤在內的人類疾病的分子遺傳學問題[4],因此與人類健康密切相關。另一方面,8000多種單基因遺傳病和多種大面積危害人群健康的多基因疾病(如:腫瘤、心血管病、代謝性疾病、神經疾病、精神疾病、免疫性疾病)的致病基因和疾病相關基因占人類基因組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因此,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和鑒定是HGP的核心部分。
20世紀90年代之前,絕大多數人類遺傳性疾病的原發生化基礎尚不清楚,無法用表型-蛋白質-基因的傳統途徑進行研究。在HGP的遺傳和物理作圖帶動下,出現了最初被稱為“反求遺傳”、90年代初又改稱為“定位克隆法”的全新思路。該思路的關鍵內容是:應用細胞遺傳學定位和家第連鎖分析方法,首先將疾病基因定位于染色體的特定位置,然后通過進一步的遺傳和物理作圖,使相關區域壓縮至1Mb之內,此時即可構建YAC、BAC、PAC、HAEC或粘粒(comid)等克隆重疊樣,從中分離基因,并在正常人和患者的DNA中進行結構比較,最終識別出疾病基因。包括囊性纖維化、Huntington舞蹈病、遺傳性結腸癌、乳腺癌等一大批重要疾病的基因是通過“定位克隆”發現的,從而為這些疾病的基因診斷和未來的基因治療奠定了基礎。隨著人類基因圖的日臻完善,一旦某個疾病位點被定位,即可從局部的基因圖中遴選出結構、功能相關的基因進行分析,將大大提高疾病基因發現的效率。
目前,人類疾病的基因組學研究,已深入到多基因疾病這一難點。多基因疾病難以用一般的家系遺傳連鎖分析取得突破,需要在人群和遺傳標記的選擇、數學模型的建立、統計方法的改進等方面進行不斷的探索。
二、功能基因組學
HGP當前的整體發展使功能基因組學提到了議事日程[5],出現了結構和功能基因組學向功能基因組學過渡、轉化的過程。一般認為,在功能基因的組研究中可能的核心科學問題有基因組的多樣性和進化規律;基因組的 表達及其調控;模式生物體基因組研究等。
(一)基因組多樣性
人類是一個具有多樣性的群體,不不同群體和個體在生物學性狀以及在對疾病的易感性/抗性上的差別,反映了進化過程中基因組與內、外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開展人類基因組多樣性的系統研究,無論是對于了解人類的起源和進化,還是對于醫學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各種常見多因素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和精神分裂癥等)相關基因的研究將成為功能基因組時代的研究熱點。除了利用多態性遺傳標記進行精細定位這一傳統途徑,也將采用基因組水平再測序的方法直接識別變異序列,即選取一定數量的受累和未受累個體,對所有疾病相關或候選基因的全序列(或其編碼區)進行再測序,準確定位其變異相關標記位點。同樣,腫瘤研究也需要對腫瘤相關基因進行大規模的再測序。
(二)識別人類基因的共同變異
已知大多數人類基因的等位基因數量是有限的,常僅有2~3種。形成這種遺傳多樣性局限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現代人類來源于一個相當小的群體,這有助于揭開許多疾病敏感性的奧秘。如:載脂蛋白E基因有三種主要變型(E2、E2和E4),可以解釋老年癡呆癥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性;血管緊張素原轉換酶(ACE)與心血管疾病一定相關性;化學趨化因子受體CKR-5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敏感性等。非編碼區對評價疾病風險也是重要的,精確定位非編碼區變異的方法可以是對調控區域變異的系統性篩查,也可利用精密遺傳圖在人類群體中識別祖先染色體節段。
三、藥物基因組學
基因組多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體對藥物的反應,通過對影響藥物代謝或效應通路有關基因的編碼序列的再測序,有可能提示個體對藥物反應差異的遺傳學基礎,這就是“藥物基因組學”(pharmacogenomics)的主要內容[6];以此作為延伸,提示個體對環境反應差異的遺傳學基礎的環境基因組學也已露端倪。
四、蛋白質組學
蛋白質組學是要從整體上研究蛋白質及其修飾狀態。目前正在發展標準化和自動化的二維蛋白質凝膠電泳的工作體系,包括用一個自動系統來提取人類細胞的蛋白質,繼而用色譜儀進行部分分離,再用質譜儀檢測二維修飾,如:磷酸化和糖基化。此外,也有人在設計和制作各種蛋白質生物芯片;蛋白質的另一個重要工作內容是建立蛋白質相互作用的系統目錄。生物大小即蛋白-蛋白和蛋白-核酸之間的互作構成了生命活動的基礎,這些互作有可能以通用的或特殊的“陷井”(如:酵母雙雜交系統)加以識別[7]。
總之,基因組學正方興未艾,其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已得到全體人類的共識,預期在不遠的將來,人類基因組學將對人類的健康、計劃生育、優生優育產生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1 Rowen L. Mahairas G, hood.L.Science,1997;278:605-607
2 Goffeau A,Barrell h,Bussey H et al. Sceince,1996;274:546-567
3 Kleyn PW,Vesell eS.Develop Sci,1998;18:1820
4 Housman D,Ledley fD.Nature Biotech,1998;16:492
5 Hitert P,Boguski m.Science,1997;278:568
篇(6)
關鍵詞基因治療;治療方式;發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r45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5739(2010)01-0025-01
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展基因治療的國家,也是目前開展基因治療最多的國家。我國在1991年7月開始基因治療的臨床研究,最早的工作是對b型血友病的基因治療及利用抑癌基因對癌癥的基因治療[1]。基因治療目前主要用于治療對人類健康威脅嚴重的疾病,包括遺傳病、惡性腫瘤、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等[2]。
1基因治療的方式
1.1體內基因治療
體內基因治療是指將具有治療功能的基因直接轉入病人的某一特定組織中。利用反轉錄病毒載體已成功地將真核基因轉入動物細胞,但通過質粒dna的直接操作,將更加省時而且產量較高;采用溫和病毒載體的體內基因治療主要是通過腺病毒和單純皰疹病毒來完成的,即將載有矯正基因的載體直接注射入需要這些基因的組織。以腺病毒為載體的體內療法在遺傳性疾病方面,目前主要見于囊性纖維變性的基因治療研究。多數研究表明,基因治療糾正了呼吸道上皮的氯離子轉運缺陷,使跨上皮基礎電位下降,肺功能有所改善[3]。
1.2反義療法
反義療法主要是通過阻遏或降低目的基因的表達而達到治療的目的。反義療法是通過引入目的基因的rna的反義序列而達到上述目的。當引入的反義rna與mrna相配比后,用于翻譯的mrna的量就大大減少,因而合成的蛋白的量也相應大大減少。引入的反義序列也可能與基因組dna互補配對,從而阻遏mrna的轉錄。這2種情況都會使細胞中靶基因編碼的蛋白合成大大減少,以達到基因治療的目的。
1.3通過核酶的基因治療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科學家cech和altman發現了核酶,核酶是指由rna組成的酶,能夠序列特異性地抑制靶mrna。近年來,核酶在抑制癌基因的表達[4]、增強腫瘤對藥物的敏感性及抑制腫瘤血管的生成等方面的應用得到了廣泛的研究。
1.4自殺基因療法
自殺基因療法是惡性腫瘤基因治療領域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已廣泛用于各種惡性腫瘤的基礎研究和臨床試驗性治療。它是用藥物敏感基因轉染腫瘤細胞,其基因表達的產物可以將無毒性的藥物前體轉化為有毒性的藥物,影響細胞的dna合成,從而引起該腫瘤細胞的死亡。
2基因治療存在的問題
2.1基因治療的社會和倫理問題
基因治療不僅僅是一種醫療方法,它還涉及很多其他問題。因為當人們試圖“糾正”人類自身“不正常”的基因時,這種糾正的后果是無法預料的。由于人類的遺傳信息非常復雜,轉基因也可能帶來不可預料的后果,沒有人能保證這種基因結構的改變絕對不會造成人類某一未知功能的缺失。另外,當人們試圖把基因治療引入生殖細胞時,又涉及后代基因結構的改變問題,且改變將直接影響這個“未來人”,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倫理問題。
2.2基因治療的技術問題
目前,基因治療的對象是單基因的缺陷,但許多疾病涉及多個基因之間復雜的調控和表達關系。對這類疾病的基因治療難度很大,因為向細胞中導入多個基因后,使幾個基因之間能保持正常的調控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單基因缺陷癥,使導入細胞的基因能正常表達也是一個較復雜的問題。將基因導入細胞后,其表達量的多少是直接影響能否達到治療的目的和有無副作用的關鍵。但這個問題將會在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的基礎上,對人類后基因組計劃的開展,弄清了人類基因之間復雜的調控聯系后而最終得到解決。只有這樣,才能在基因治療中盡量做到使導入的基因處于正確的調控下,取得治療效果,消除副作用。
3展望
以基因轉移為基礎的基因治療要在臨床上很好地應用,還有待理論和各種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過去20~30年基因治療的發展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已被看成是對先天和后天基因疾病的潛在有效的治療方法,不過其依然存在缺少高效的傳遞系統、缺少持續穩定的表達和宿主產生免疫反應等問題。今后基因治療研究將向2個方向發展:一是基礎研究更加深入,以解決在臨床應用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及基因治療本身需要解決的一些難點;二是臨床試用項目增多,實施方案更加優化,判斷標準更加客觀,評價效果更加精確。總之,隨著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以及臨床醫學的發展,基因治療也會不斷發展,日趨成熟,很多難題會得到解決,并在臨床上得到廣泛應用。 編輯整理
4參考文獻
[1] 李立家,肖庚富.基因工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2] anderson w.human genetherapy[j].nature,1998(392):25.
篇(7)
關鍵詞:多囊卵巢綜合征;臨床研究;進展
臨床婦科內分泌疾病中,多囊卵巢綜合征(PCOS)較為常見,以持續無排卵和雄激素過多為主要特征,是一種以多種代謝異常、內分泌紊亂為主的異質性臨床綜合征,對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1]。PCOS治療主要依據病變程度、患者年齡及就診目的對治療措施進行選擇,提倡系統性、個體化、綜合性的治療,并與預防相結合,以最大限度的改善預后。本文對相關研究及其臨床特點進行分析,旨在為臨床治療方案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現將相關內容綜述如下[2]。
1 PCOS與遺傳的相關性
PCOS存在一定的家族聚集現象,故遺傳因素對之有一定的影響存在,在目前對PCOS研究的熱點內容中,分子遺傳學為較重要的部分[3]。研究顯示,PCOS為共顯性遺傳常染色體,其遺學學基礎為家族聚集性[4]。PCOS可能由環境因素與致病基因相互作用導致,為多基因病,與多個基因突變密切相關。與PCOS發病存在關聯的候選基因中,有學者共提出37個,如相關甾體激素合成基因,包括性激素結合球蛋白基因、膽固醇側鏈解酶基因等。相關胰島素活性及其分泌的基因如胰島素受體基因、胰島素基因等[5]。
CYP11α基因于15號染色體上定位,以膽固醇側鏈裂解酶為編碼。對膽固醇有催化作用,使其旁鏈分裂轉化為孕烯醇酮,為與雄激素合成代謝有重要關系的酶。故在PCOS基因研究中,CYP11α在候選基因中占重要地位。CYP11α微衛生多態性是重要的造成PCOS高雄激素血癥的相關遺傳因素,屬較為重要的遺傳易感位點,具有深入科研價值[6]。
PCOS的相關特征中,還包括高雄激素血征,SHBG調節雄二醇、睪酮對靶器官的作用。SHBG水平可受營養、代謝、激素等多因素影響,為人類性甾體激素血漿運輸蛋白,由肝臟產生。與正常人SHBG比較,PCOS患者呈較低水平。SHBG是PCOS候選基因之一,其在PCOS患者中水平出現下降具有一定的遺傳學背景[7]。胰島素基因在染色體11p15.5上分布,其存在的可變數目串聯是造成PCOS特別是無排卵的患者主要的可疑性位點,在2型糖尿病及高胰島素血癥患者的發生機制中均有一定的作用產生。
在細胞水平上胰島素首先與受體結合發揮作用,胰島素受于細胞膜上,是一種膜蛋白,為四聯體,分別有2個α亞基及β亞基構成。α亞級與胰島素結合,有配體結合的區域,于細胞外分布。β亞基含13個酪氨酸殘基,為跨膜結構,具有酪氨酸激酶的活性。編碼胰島素受體基因對受體酪氨酸激酶的活性有著重要的決定作用。研究發現,位于17外顯子1058位點有體重指數(BMI)和TC等位基因多態性出現,故PCOS非肥胖者可依據此特點進行診斷。
2 PCOS與IR相關性
臨床對IR在PCOS患者中存在已有共性研究,PCOS患者糖代謝異常中高胰島素血癥及IR為基本特征,有約63.4%的發生率[8]。肝臟清除胰島素的效果下降及周圍IR為IR發生的主要原因,周圍IR可能為變異的胰島素受體基因造成胰島素受體數目不同程度的減少,而高胰島素血癥為一種IR的代償性反應[9]。在胰島素受體有缺陷情況存在的情況下,胰島素生長因子受體與升高胰島素結合,對卵泡膜細胞進行刺激,使雄激素分泌增多,對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結合蛋白及肝臟SHBG合成起到抑制作用,使游離IGF-1和有生物活性的雄激素增加。相關研究顯示,POCS異常與心血管疾病,肥胖均有一定相關性。
3 PCOS與脂肪細胞因子相關性
肥胖患者占PCOS總患者人數的50%,脂肪細胞因子在相關疾病的發生及肥胖中有著重要作用。脂肪細胞為較活躍的內分泌代謝器官,是能量儲存場所,通過對各種脂肪細胞因子分泌,如脂聯素、瘦素等參與體內能量平衡調節和復雜的代謝活動,并在相關疾病和肥胖中存在。
3.1 瘦素相關特點分析 瘦素為脂肪細胞分泌的一種蛋白,在機體肥胖基因編碼中,其為氨基酸殘基,第146個,通過下丘腦受體對大腦機體脂肪狀態進行通知,進而達到對體重控制的效果。對外周和中樞均有調節作用[10]。外周組織和下丘腦均存在活性瘦素受體。除通過對下丘腦-卵巢軸、垂體功能對性激素的內分泌和合成造成影響,還存在間接或直接的外周作用。卵泡液內高濃度瘦素在外周對卵母細胞和卵泡的成熟進行干擾,對排卵產生抑制。血中高濃度瘦素對顆粒細胞作用,對芳香化酶活性進行抑制,對雄激素轉化為雌激素進行阻止,增高血雄激素水平,最終發展至PCOS。PCOS患者體內,瘦素的作用呈多樣且復雜性,即可在能量代謝途徑上作用,造成IR形成而誘導PCOS發生,也可對生殖系統直接作用對激素的代謝和合成進行干擾,引起疾病發生。研究發現,血清瘦素水平在PCOS患者中通常為異常表現,故PCOS發病中瘦素通過對胰島素進行調節而產生一定作用。故血清瘦素水平與PCOS的發生存在較大相關性,需對PCOS代謝異常中瘦素的特點進一步研究,以為PCOS的臨床診治提供依據。
3.2 脂聯素(APN)分析 脂聯素為相對分子量為30000的蛋白,由脂肪組織特異性分泌,是最近發現的脂肪細胞因子。APN具有抗動脈硬化、抗炎、調節糖代謝、改善IR增增加胰島素在外周組織的敏感性,其水平的減低與動脈粥樣硬化、糖尿病、IR存在密切相關性[11-14]。通過對脂肪代謝產能進行促進,降低脂脈在體內的含量,進而減輕肝臟及血液中脂肪酸含量,降低血糖濃度,使胰島素的敏感性提高[15]。有學者研究顯示,PCOS患者中APN可能為發生2型糖尿病等并發癥遠期特點的預測指標,需加強PCOS低水平APN患者的隨訪,以對糖代謝異常進行防治[16-18]。
4 PCOS與心理、精神的因素
PCOS的研究已向營養、生化等多個領域涉及,但對心理學的相關研究較少,研究表明,PCOS患者對生活的滿意度較低,精神、心理因素對患者造成嚴重不利影響,是導致遠期并發癥發生的重要因素[19-20]。心理、社會、精神對人體尤其是內分泌系統有較大的影響,長期恐懼憂慮、精神緊張、精神壓抑、環境改變等會導致排卵異常和神經內分泌障礙,而目前,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使女性心理壓力更大,需加強心理因素引起PCOS的研究。
5 小結
綜上,PCOS為代謝性疾病,具有多基因遺傳傾向,其發病機制及病因尚不十分明確,對PCOS的研究目前已涉及多個領導領域,在基因、脂肪細胞因子方面較集中,隨著醫療科技和醫學的進一步發生,對PCOS的認識也會加深,為治療中依據病因對方案進行制定提供了依據,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Hickey M,Sloboda DM,Atikinson HC,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and umbilical cord androgen levels and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in adolescence: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J Clin Endocrinol Metab,2009,94(10):3714-3720.
[2] 李國屏,李小紅,陳湘梅,等.多囊卵巢綜合征與精神因素、家族史、飲食、運動的相關關系分析[J].中國婦幼保健,2006,21(6):740-743.
[3] 劉金勇,劉嘉茵,韓素萍,等.丙戊酸鈉對卵泡內膜細胞雄激素分泌及相關甾體合成酶改變的影響[J].生殖與避孕,2005,25(11):655-9.
[4] 閆妙娥,宋娟娟,吳效科.PCOS是卵巢對胰島素超敏綜合征[J].生殖與避孕,2006,26(4):233-6.
[5] 陳子江,李媛,趙力新,等.超聲下未成熟卵泡抽吸入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征不孕的臨床研究[J].中華婦產科雜志,2005,40(5):295-298.
[6] 王佳,詹平.雙酚A對機體影響及其機制研究進展[J].預防醫學情報雜志,2005,5(7):581-582.
[7] 郁琦,金利娜.第2屆全國多囊卵巢綜合征及其相關疾病治療新進展專題研討會紀要[J].中華婦產科雜志,2007,42(5):291-293.
[8] 石玉華,陳子江. 多囊卵巢綜合征易感基因的研究進展[J].中華婦產科雜志,2007,42(5):345-347.
[9] Munir I,Yen HW,Baruth T,et al.Resistin stimulation of 17alpha-hydroxylase activity in ovarian theca cells in vitro:relevance to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 Chin Endocrinol Metab,2005,90(8):852-7.
[10 ]Fluck CE,Mille WL,GATA-4 and GATA-6 modulate tissue specific transcription of the human gene for P450c17 by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Sp 1 .Mol Endocrinol,2004,18(5):1147-57.
[11] 陳子江,石玉華,趙越然,等.胰島素受體基因多態性在多囊卵巢綜合征發病的關系[J].中華婦產科雜志,2004,39(6):345-347.
[12] 熊文琴,張文權. 多囊卵巢綜合征患者胰島素抵抗與內分泌異常、心血管疾病風險的關系[J].實用預防醫學,2007,14(2):363-365.
[13] 劉澤安,陳利馨. 多囊卵巢綜合征胰島素抵抗性不孕癥藥物治療臨床研究[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03,12:741-743.
[14] 邵瑞云,郎豐君,蔡金鳳,等.補腎活血中藥加克羅米芬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征所致不孕的臨床觀察[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4,24(1):41-43.
[15] 王興娟,王靜,賈麗娜,等.81例多囊卵巢綜合征患者血清瘦素觀察[J].復旦學報(醫學版),2007,34(4):537-540.
[16] 陳友國,沈宗姬,胡建銘,等.脂聯素對多囊卵巢綜合征內分泌代謝異常的影響[J].江蘇醫藥,2006,32(2):1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