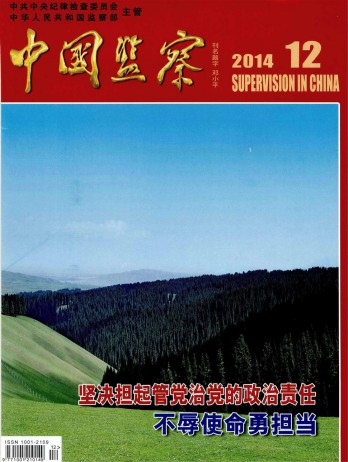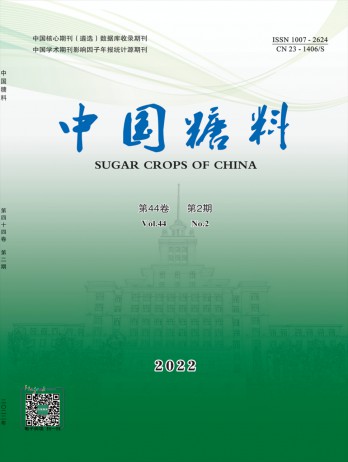中國建筑史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3-21 17:11:54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建筑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清代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卷六】【生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從生。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下象土。上象出。此與出以類相從。十一部。凡生之屬皆從生。作為動詞的“生”的含義如表1所示作為名詞的“生”的含義如表2所示。
2.建筑的生命精神內涵
古人善于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的時間現象,從而產生了具有不同情感的生命感悟。例如:《周易》“生生之謂易”。這是從時間循環變異現象而產生的恢宏闊大的生命情懷。又如:《周易•系辭下》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具有生生之德,正是四時運行而化生百物,并具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生命順序,“突現了生之理”(朱良志,1995)。尤其是自然景物隨四季的盛衰榮枯更容易化時間現象為悠悠心境。這是從四時運行的時間現象而產生的對生命過程的感悟。中國傳統哲學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是古人的時空觀念或者說是宇宙觀。宇是空間觀念,宙是時間觀念,宇宙連用是時空觀念的綜合體現。《莊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二字連用,始見于《莊子•齊物論》曰:“旁日月,挾宇宙,為其吻合。可見,對中國古人而言,時間的體驗雖然是具體的、經驗的,但更是一種無法定質定量的心理時空。他們善于將物理時間轉換成富有感性色彩的生命感悟,其關鍵就在于客觀場景的具體時間現象能否在人的心理上引感。2.1建筑時間觀建筑的時間觀,體現在居住其中的人的心理感知從而對時間現象進行抽象的抒懷。而這種時間觀往往是同“宇宙”的觀念相連,指向“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古人崇天“巍巍乎,為天為大”,古代的建筑甚至城市規劃,也往往“象天法地”。《三輔黃圖》上記載的營建咸陽時的“……信宮作極廟,像天極”,漢代宮室,如班固所謂“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1]P24-25,都是古人建筑時間觀的體現。另一方面古人對時間秩序的感知上升為規范人們行為的“禮”的秩序,因四時四季不同,而舉行的祭祀活動所建設的建筑,形成的不同的空間與氛圍。今日北京仍然保留有祭祀自然的壇廟如天壇、地壇、日壇、月壇。2.2建筑空間觀當人們在院落中,觸摸斑駁的墻體,看著白墻上枝椏稀疏的影像歲日光西暮,而逐漸挪移,時光在建筑上完成了傳遞,而人們也從光影的變換中體會歲月時間的流逝。完成了從時間到成空間的轉變。傳統建筑院落所構成的空間,在園林住宅中的表現尤為突出。把構成院落的元素僅僅當成建筑元素的話,那一道門、一扇窗便只是具體的物質存在;那一面墻、一座游廊,只是空間的分割,但就是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建筑元素,在時間的作用下,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建筑空間觀。即時空的交錯與融合。作為建筑的使用者,居于其中的人,在游廊中穿梭,透過一扇漏窗,望見如意門洞所框出的半枝芭蕉,于是多個空間在以人為主體的活動中,完成了空間的轉化。“步移景異”就是這個意思。多進院落形成的縱向縱深的空間序列與橫向跨院形成的水平序列,往往通過不同的墻體或門的變化完成空間的轉變或推進。建筑元素就變成了空間轉換的節點而存在。
3.中國建筑藝術的生命論
3.1生——生命結構論張皓[2]認為立足在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廣闊背景上,中國哲學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一種生命哲學。他認為這一哲學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結構,以“生命即本體即真實”為其基本綱領,并通過時空兩位的縱向橫向展開,形成一個無所不在的有機生命之網。因此有了“生之為性”的哲學命題。善即生即仁,人間之美乃生之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這“生”是真善美的統一。3.2時——生命時間論中國文化形成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時間觀,這種時間觀十分重視生命,以生命的目光看待時間。“莫若以時”,以時就是應時,適時。具有兩個側面即莫錯用時和莫錯過時。而由此“奉天時”通過審時,窺時的到達“契時”最終達到“契生”和“與時俱化”。3.3氣——生命基礎論中國哲學以氣為本原范疇,中國美學也以氣為藝術生命之本,氣是美的發生與作品的活力所在。中國文化思想以“氣”為萬物之本,生命之元,陰陽之化,精神之流;中國文化以“氣”將精神與物質、運動與時空統一的思想具有相當的優越性,對于美學,以“氣”闡發之,更有無可比擬的精辟、深刻、超然于貫通等長處。所謂“三來”蓋之文藝創作由審美感應而的三種動因:神來,情來,氣來。自魏文帝曹丕主倡以氣論文之后,人們更多的從藝術創作本身來尋求氣的奧秘,氣范疇也更多的納入審美主體的內涵。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文以氣為主”是一個劃時代的命題,標志著文學由經學的附庸走向自覺、自立。中國美學素以生命之氣來看藝術和審美活動。在中國美學中,神氣既指創作個性才氣的油然體現,又指藝術作品奇妙傳神的審美特征。
4.結語
建筑的生命精神內涵,特別是傳統建筑自營造之時,就同“生”息息相關。傳統建筑觀念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便生利人”。人們從自然界中的萬物認識到了生命的意義,也認識到了陽光、水分、植物等條件對生命的重要性,“生”,是華夏先民對自然事物的一種極遠古的認識。生命是有限的。一座建筑的生命可以很久遠,遠到建它的人隨風逝去,而它依然挺立;一座建筑的生命也可以很短暫,短到它還未建成,可能就一夜間轟然倒塌。建筑是有生命的。建筑亦是有感情的。建筑中承載著使用者的喜怒哀樂,保留著居于其中的人的痕跡。于是人們可以在古建筑中發憂思之情,才可以在建筑中緬懷曾經的人和事。
參考文獻:
[1]王其亨,當代建筑史家十書•王其亨中國建筑史論選集,遼寧美術出版社,2014年9月
[2]張皓中國美學范疇與傳統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3]蕭默,建筑的意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1月第一版[4]侯幼彬,中國建筑美學,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5]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筑史,北京:建筑工業出版社,
[6]方擁,中國傳統建筑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7]馮柯,說宅,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
篇(2)
一、徽州文化的界定
要研究徽州文化,首先就要有對徽州文化較為清晰的界定。對此,可以說,學術界至今沒有統一的、明確論及的界說。據筆者的理解,所謂徽州文化即是指發生與存在于歷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發生輻射、影響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如此定義,至少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限定:
其一,我們說的徽州文化是指歷史上徽州區劃范圍內的文化。其地理區域范圍包括當年徽州府轄的6個縣,即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和婺源。
其二,徽州的歷史至少有五、六千年,其文化當然可歸為廣義的大徽州文化的范圍。但嚴格和典型意義上所說的徽州文化概念,主要還是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設了徽州府后才全面崛起,在明清時達到鼎盛的文化,但這一文化與其早期發展及后期演變都有內在關聯。
其三,徽州文化不能僅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還包括由徽州而發生,由本籍包括寄籍、僑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創造從而輻射于外、影響于外的文化,這其中的關鍵是要有對徽州的強烈認同。如朱熹,盡管他在福建,主要活動也在福建,但他祖籍在徽州,朱熹本人對徽州強烈認同,從來號稱“新安朱熹”等;同時,徽州人也更是強烈地認同朱子,視朱熹為徽州人的驕傲,在思想意識、觀念、道德、倫理、社會行為及活動的諸多方面都自覺不自覺地深受朱子思想的影響,故朱子的思想、學術活動等亦可作為徽州文化的內容。
其四,這里所說的“文化”應是取其廣義的概念,不僅指學術理論、文化藝術,還包括商業經營、宗法倫理、精神信仰、風俗民情、文獻著作、社會經濟、土地制度、歷史人物等等。
如此界定的徽州文化概念,實際是將徽州歷史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多元的、系列的整體,既有顯明的地理空間和時間流程上的限定性,又有內容實質上的限定性,以及由此限定而內在包括的對自身限定的一體化超越,決定了徽學研究的對象。由此,筆者不會同意有人將徽學(或稱之為“徽州學”)的研究對象僅僅限定為“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在徽州這個封閉、落后、貧困的山區出現的一種具有豐富性、輝煌性、獨特性、典型性、全國性五大特點的徽州文化產生、繁榮、衰落的規律的學問。”(注:趙華富:《論徽州學的研究對象和意義》,載張脈賢、劉伯山等編:《徽學研究論文集(一)》,1994年10月。)將宋之前及以后的徽州文化斷然地割除在徽學研究之外,這里且不論其界定的內容是否準確,僅其忘記了徽州文化當有其來源即產生的歷史條件基礎及以后的演變來說,就應是不夠完整的。歷史當是不能簡單、武斷地人為分割而將分割后的片斷獨立純化成塊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應是徽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或重點內容而不應是唯一內容。
實際上,徽州文化只是徽州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個階段。徽州早期的土著人是越人,最早的文化形態是筆者稱之為的早期江南越文化,其時限當是從遠古至春秋戰國,其時,徽州歷史文化尚未從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母體中分離出來以走獨具品格發展的道路。其后是山越文化,其時限為從戰國中后期至三國,這時的徽州社會與文化已開始從中華民族母體的社會文化發展中分離出來,但卻是走著一條停滯發展甚或出現倒退的道路,越人“入山為民”,以成山越,“依山阻險,不納王租”,生產方式上“刀耕火種”,生活習俗上,“志勇好斗”,烙有很深的半原始叢林社會與文化的痕跡,以至于有人稱這一時期是徽州歷史上的“黑暗”時期。(注: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頁。)東漢末年至南宋的長達一千多年的時期是筆者稱之為新安文化階段(晉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徽州設新安郡,故稱),徽州的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由于北方諸多土家大族的移民而帶來在人口、經濟、文化上的沖擊、碰撞及最后的整合,得到長足進步和快速遞進,封建化進程得到實現,至南宋時,越人已與遷居而來的北方漢人融合,徽州人已經是十分成熟的“封建人”;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突出,由徽州本土向外的徽州歷史上第二次移民——負移民的過程已經開始,它主要是通過科舉和經商兩條道路實現;徽州重儒、重文、重教的風氣已經形成,“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興則名臣輩出。”(注:淳熙羅愿:《新安志》卷一。)“新安自南遷后,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于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故四方謂‘東南鄒魯’。”(注:趙@①:《商山書院田記》。)并且也正是此時期,徽州已是作為了“程朱闕里”,是程朱理學的發祥地,(注:見拙作:《程朱理學淵源考》,《探索與爭鳴》,2000年第3期。)而程朱理學特別是朱子之學恰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內核。所以說,我們不能割斷地研究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只是徽州歷史文化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它直接孕育和發展于新安文化,后者是前者的基本來源。(注:關于徽州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歷史分期,可參見拙作:《崛起的徽州文化學——關于文化學研究的一點意見》,《徽州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二、徽州文化的基本內容
徽州文化在南宋崛起后,經元時的發展,至明清,其發展已達到充分化。體系完整,內容深刻,特點鮮明,其輝煌性、豐富性,至少是表現在:
其一,南宋以后,徽州人幾乎是在文化的所有領域都有突出的貢獻,在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創造與發展,以至形成了各自有著自己風格與特點的流派。如商業經營上有著名的徽商(后文再述)。哲學上有新安理學,亦即朱子之學,其開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還有婺源的程洵、休寧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淵遠流長,特別是“在明清,朱子之學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推新安之士為然。”(注:道光《休寧縣志》。)考據學上有徽派樸學亦即江戴樸學(江即江永,婺源人;戴即戴震,屯溪人),它作為乾嘉學派中的皖派,影響極大,清江藩評價說:“三惠之學興于吳,江永、戴震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注:清江藩:《漢學師承記》。)繪畫上有新安畫派,歙縣江韜(即漸江)被認為是其祖師,近代有歙人黃賓虹等。據有人統計,從明朝萬歷年間到清乾隆間的不到200年時間里,徽州共出屬新安畫派的大畫家60多人,其中的名家、大家的水平,按黃賓虹的評定,當“均在江浙之上”,可想影響之大。(注:李明回:《談新安畫派》,《安徽文博》,第4期。)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興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有何震、黃士陵等。據馮承輝編纂的《印識》記,僅明代一代,全國有篆刻家190余人,其中僅徽州的歙縣、休寧兩地就占35人,清代更多。(注:鄭清土:《何震和徽派篆刻》,《徽州學叢刊》創刊號。)刻書上有徽派刻書,它始于南宋,興于明清,在我國雕版印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明清“時人有刻,必求歙工”,(注:嘉靖《徽州府志》。)徽刻儼然
與常(州)刻、蘇(州)刻齊名為當時全國三大刻。版畫上有徽派版畫,它在中國美術史上獨樹一幟。明代萬歷年間有“無劇不圖”,“刻圖必然求歙工,歙工首推黃氏”之說。據統計,從明代萬歷到清初的100多年時間里,僅歙縣虬村一村黃姓以版畫為業者就達100多人。(注:周蕪:《徽派版畫史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戲曲上有徽劇,它是京劇的前身,清乾隆年間,曾出現“四大徽班進京”,名噪一時。到了道光年間,北京則是“戲莊演劇必徽班”。(注:道光《夢華瑣簿》。)建筑上有徽派建筑,為中國建筑史上一絕。醫學上,有極負盛名的新安醫學,為我國醫學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從東晉到清末,徽州僅有史料可查的名醫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寫了461部醫著,其中明清兩代有名醫605人,有245人撰寫445部醫著,在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注:李濟仁、胡劍北:《新安名醫志》,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棋藝上,新安圍棋自古至今就高手輩出,明清時圍棋界的新安派被譽為是與“永嘉派”和“京師派”齊名的三大派之一,其中歙縣人程汝亮是被王世貞在《弈旨》一書中列四個“明代第一品”的第一人;而歙縣人程蘭如則被稱為是與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齊名的盛清四大國手;(注:吳小汀:《明清時期圍棋“新安派”初探》,《徽學通訊》總第17、18期。)近代以后則有著名國手歙縣人過惕生、過旭初兄弟倆。徽州的傳統工藝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個領域。文房四寶藝術,徽州占有兩寶,即徽墨、歙硯,元之前還包括澄心堂紙、汪伯立筆;飲食烹調上,有著名的徽菜,它精選料,重色、重油、重火功,為全國菜系之一;雕刻工藝上,除上述版畫等外,還有著名的徽派磚雕,木雕、石雕,并稱“徽州三雕”。此外,還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種竹、木編織工藝等等。這些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在這些領域里的精萃,曾各領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
其二,在文化發展的有些領域,徽州或許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派別,卻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和杰出人物。如自然科學界,徽州是群星燦爛。數學上有數學大師屯溪人程大位(1533-1606年),他著有《算法統宗》十四卷,最大貢獻是將數學從籌碼記數發展為珠算計數,確定了珠盤式運算并完善了珠盤口訣,在國內外影響極大;物理學上,有物理學家歙縣人鄭復光(1780—約1862年),他精通數學、物理和機械制造,特別是在光學上貢獻最大,著有《鏡鏡冷癡》五卷,專論光學原理和光學儀器制造,是我國當時最主要的一部光學著作等等,以至有人說,一部徽州自然科學史也就是一部安徽自然科學史。(注:張秉倫:《明清時期安徽的科學發展及其動因初析》,《徽州學叢刊》,創刊號,1985年。)徽州的詩詞文學,雖然難以斷定它存在一個流派,但至少是存在一個龐大的群體。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詩人、大文學家,其古詩在南宋堪稱第一,(注: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傳世的就至少有1200余首;祁門人方回(1227—1307年)的詞風、思想與辛棄疾相近;明歙縣人汪道昆(1525—1593年)不僅官居顯位,且其文學造詣頗深,其文學被譽為是明中期文學復古派“后五子”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別是在布衣詩上,王士禎曾記:“論明布衣詩,極推吳非熊、程孟陽,海內莫不聞兩先生皆新安產也。”(注:《新安二布衣詩》,清稿本,藏祁門縣博物館。)有清一代270余年間,徽州至少可稱得上詞人的就有200多,詞萬首。在其他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是歙縣人王茂蔭(1798—1865年),他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理財和經濟思想史專家;休寧人朱升(1299—1370年)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經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戰略思想家,1337年他曾進言朱元璋“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對朱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黟縣人俞正燮(1775—1840年)是清朝著名的經學家和史學家;戲曲家有目連戲集大成者祁門人鄭之珍(1518—1595年),有明代著名戲曲家休寧人汪廷訥(1573—1619年),特別是汪廷訥,其不僅作品博采眾家之長,獨樹一幟,同時,他還是一位圍棋理論家,著有《坐隱老人弈藪》一卷和《坐穩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5卷;語言學界,除朱熹、江永、戴震等碩儒大家多有研究外,不經名人士的研究也相當深入,如在徽州方言研究上,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書屋”(注:筆者2000年以前在黃山市工作期間,曾在徽州搶救和收集一了一萬一千余份(部)徽州文書原件,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獻給安徽大學,為此,安徽大學特設“伯山書屋”以藏之。)內就收藏有由婺源人胡昭潛抄,婺源人江湘嵐編著的《婺北十二都東山鄉音字類》手抄本上下兩冊和胡昭潛自著《休邑土音》稿本上下兩冊(注:這四冊手抄本書筆者訪得婺源同一戶人家,另有胡昭潛手抄《照錄家乘》、《八音之譜》、收租帳本等。),分類詳細、音準,可見徽州民間語言學研究之底蘊;教育學界徽州更是淵源流長,朱熹、鄭玉(1298—1358年)、趙@①(1319—1369年)、汪克寬(1304—1372年)等都是徽州有名的教育家,當代更有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歙縣人陶行知(1891—1946年);績溪人(1891—1962年)是當代文化巨子等。他們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過突出貢獻,其學術思想,都不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內容。
其三,除上述二方面外,徽州文化的內容還包括受上述因素及地理因素影響,由徽州社會自然衍生和客觀形成的一些獨特文化現象。如徽州號稱是一個契約社會,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的民間契約文書至少就有數十萬份,(注:見拙作:《徽州文書的留存及搶救》,《光明日報》2001年11月11日理論版。)早的是宋代的,明清最著,遲的據筆者所見直至1955年、1965年和1985年,(注:見拙作:《“伯山書屋”一期所藏徽州文書的分類與初步研究(上)》,《徽學》,2000年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內容涉及土地山場房屋池塘等買賣、租佃雇傭關系、過繼入贅關系、商業資本籌集、訴訟案卷、宗族公約、民間借貸、鬮書、票據、會書等,不僅數量多,年代持續時間長,而且還很系統。如此契約社會現象在徽州是最為典型的,它透露著很深層次的徽州社會及人際關系的理性成份。再如徽州的宗法制度與宗族文化,其典型性和獨特性亦極顯著。徽州人由移民而來,聚族而居,休寧人趙吉士曾言:“新安有數十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póu@②;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雖數十世未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注: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一二。)敬宗重族,強化修譜,謂之:“夫人之一生莫乎綱常之事,綱常之在莫過于譜諜。”“三代不修譜,則為不孝”(注:祁門《武溪陳氏宗譜》,藏安徽大學“伯山書屋”。)等。還有徽州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土地佃仆關系、徽州人的意識與價值觀念、徽州人的風俗與信仰、徽州方言現象、徽州棚民現象等,這些都是徽州特有或表現極為典型、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也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
三、徽州文化興盛的原因
徽州文化當年能如此繁榮,并保持幾百年不衰是有內在的原因和基礎的。
首先是經濟基礎,這就是徽商。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幫,它當年是逼出來的。
徽州介于萬山叢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地瘠,“即富者無可耕之田”,“田瘠確,所產至薄,……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又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之一。”(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糧食從來不能自給,所需糧食皆“仰四方之來”。特別是到了唐宋以后,“黃巢之亂”和“靖康之亂”連續兩度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當時的徽州耕地狀況和生產力水平,幾乎達到飽和,于是民眾生存空間更小,徽民們“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矣”。(注:許承堯:《歙事閑譚》卷二十八。)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注:康熙《徽州府志》卷八。)正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徽商遂在南宋時開始形成。當然,徽商的形成還內在地與徽州本土山經濟結構和以新安江為主干流的縱橫便利水系有關,山經濟結構本身的盈缺待補的不平衡性,內在需求以流通與交換來獲得平衡,滿足徽民的基本需求;發達的水系又帶來運輸的便利,使地處僻野山區的徽州的商品流通得以最為經濟的實現。(注:參見拙作:《徽商概論》,黃山市政協文史委編:《古代商人》,黃山書社,1999年。)但早期的徽商還是一種簡單的以徽州山林盛產的茶、木、瓷土及二次生產的漆、墨、紙、硯等換取徽州所需的糧、布、鹽等的缺盈互補貿易。到明以后徽商才得到大發展,不再局限于以徽州為中心的販買販賣,而是面向全國,經營規模也越來越大,經濟之道走向成熟,成為中國商界一支勁旅。清時,則又躍為中國十大商幫中居首之幫,這其中尤以鹽商、木商、茶商、典當四項為最盛。足跡遍及全國,遠涉海外;正所謂“鉆天洞庭遍地徽”,影響極大,以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從徽商的賈道特點來看,徽商作為當時中國一代儒商,其“賈而好儒”,注重賈儒結合,賈仕結合,強化宗誼,重視教育,恪守賈道,營利甚巨。“百萬上賈者眾,二、三十萬中賈者不計其數。”所賺的錢,一是擴大再生產;二是弄文附雅,宿養文士,建會館、辦文會、興詩社、蓄戲班、印圖書、藏書史、筑園林等;三是發展教育,以“富而教不可緩,徒積貲財何益乎”(注: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二。)的思想意識,延師課子,加強對子弟培養,輸金資助,置學田和義田,辦族學,建書院,資府縣學等;四是輸入故里,修橋補路、興建土木、撰文修譜等。這就在客觀上為徽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后盾。
其二,是徽州文風與教育的基礎。徽州歷史上文風昌盛,教育發達,府縣學、書院、社學、私塾、文會極為昌盛。如書院,據有人統計,自宋至清,徽州六縣共建書院、精舍、書屋、書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注:劉秉錚:《徽州書院沿革述略》,《徽學研究論文集(一)》。)社學,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詔書天下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是年徽州六邑有社學462所,(注:《徽州教育記》,載《徽學通訊》第13—14期增刊。)康熙時,則達562所。(注:康熙《徽州府志》卷七。)私塾更是林立。“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十戶之村,無廢誦讀”,就是當時徽州文風昌盛的寫照。由于教育發達,人才也就輩出。據葉顯恩先生統計,中進士者,僅徽州本籍,宋代624名,明代392名(占明代全國進士總數的1.55%),清代226名(占全國進士總數的0.86%);(注: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第192頁。)再加寄籍外地的一起,則就多得驚人。狀元也很多,如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計17人,占全國總數的14.9%,(注:參見吳建華:《清代徽州狀元》,《徽州通訊》,第13-14期增刊。)僅次于蘇州府,全國名列第二。人才的輩出,以致徽州歷史上有“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一科同郡兩元者”等之說。發達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榮的溫床。
其三,是程朱理學的影響。徽州號稱“東南鄒魯”,是“程朱闕里”,程朱理學的發祥地。《程朱闕里志》記:“程朱之學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學宮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舉而合祀之,則獨吾歙。……朱學原本二程,二程與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黃墩徙,故稱程朱闕里。”“程朱三夫子,一自婺人閩,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黃墩。”(注:雍正重刻《程朱闕里志·序》,藏黃山市博物館。)特別是朱熹的思想,對徽州的影響至深。朱熹曾兩次回徽省墓,角次皆講學授徒,論定高足者至少有12人。在徽州,朱熹為其朱氏及他姓,撰源考、作譜序、題牌匾、留詩句等等,文跡甚眾,留墨甚多,如筆者就收藏有一塊朱子當年題寫有“鳶飛魚躍”的碑刻,彌足珍貴。徽州更是“一以郡先師朱子為歸”,“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傳子若孫也。”(注:清休寧《茗洲吳氏家典·序》。)徽商建立在全國各地的會館皆崇祀朱子等。朱子之學不僅深深影響徽州入仕、入學、入賈之人,也深入民眾意識,使徽州構成儒家思想進而兼容著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區,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為甚重。這些都內在深沉地左右和指導著徽州文化的發展,使朱子之學成為徽州文化發展的強大思想意識上的支柱,構成徽州文化之理性內核。
其四、除上述三點外,徽州文化所能突出個性和特色的地方,還是第一,內在接受著徽州獨特的地理環境、山水資源情況的規限與影響;第二,內在深刻地接受著徽州移民社會和文化性質的決定和影響;第三,同步發生干涉地、雙向作用地接受徽州文化本身存在與發展過程之決定和影響,其中存在地緣與地理文化決定性、文化發生的邊界條件決定性和文化整體系統內部的協同影響性等諸方面決定因素。
四、徽州文化的歷史地位
徽州文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后期,封建政權、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權和加強一體化時期形成并獲得極大繁榮的區域文化,因此,它是作為一種典型的中國封建文化,封建性應是它的本質屬性。作為徽州文化基礎之一的徽商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封建商幫,賈儒結合、賈仕結合、重親誼、重鄉誼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體表現;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種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選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目的等無不內在體現中國封建社會的內容和要求;更主要的是,作為徽州文化指導思想的程朱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其一切都是在維護和辯護于中國封建社會。也由于徽州文化的封建性本質,因此,當歷史的腳步發展到近代,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徽州文化隨之一體化般地衰退、消亡也就必然。徽州文化在清末以后衰退了,輝煌屬于過去。
然而,曾保持興盛幾百年的徽州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是有其獨特、重要的歷史地位的。五千年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中國封建文化,而中國封建社會在進入了南宋以后,開始處在后期,徽州文化正是在這一時期全面崛起并繁榮,它的全面性、豐富性、輝煌性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投影;同時又由于徽州文化的獨特性、典型性、全國影響性,又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縮影,從而確定了它典型代表和標本的地位。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文化發展的基本線索及其在晚期以后與徽州哲學意識發展基本線索的內在對應情況能很好地證明這點。
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文化一直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而儒家文化的發展又是經過幾個階段的。最初是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為
代表的經典階段,其次是董仲舒建立的“天命論”儒學階段。到了兩宋,由于社會的進步,特別是“佛教興,而中國哲學一時退處于無權;然其中固不乏獨至之處。宋學興,乃即以是為憑借,以與佛學相抗焉”。(注:呂思勉:《理學綱要》篇二,《理學三原》。)天命論形式的儒學日益顯示其不足,于是理學興起,將儒學理論化、哲學化,從而建立更系統、嚴謹的體系,程顥、程頤是理學體系的形成者,朱熹是集大成者,構成儒家文化發展的第三階段。理學之后則是儒家文化的衰退,至明清,啟蒙思潮、反理學思潮出現,形成了儒家文化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一階段長達幾百年,其中又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其特點是披著封建文化的外衣反儒學、反封建;第二個時期是“五四”時期,其特點是明確提出“打倒孔家店”,接受科學與民主,提倡新文化。
上述基本線索,從理學階段開始就與徽州結下不解之緣。首先是理學,且不說徽州是二程和朱子的祖籍地,徽州人研究理學,又形成新安理學學派,以維護、繼承、光大朱子之學為宗旨,“嚴尊師道,精悟師訓”,著述甚豐,影響甚大,代表了朱子理學的正宗,獨領,既是作為程朱理學的典型投影更是作為了典型縮影。其次是在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徽州人披著封建文化的外衣反理學、反封建又在全國最為出色。這其中戴震是世人公認的早期啟蒙運動的一面大旗。段玉裁評論說:戴氏的學說“專與程朱為水火”,“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注: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七。)梁啟超評價說:戴氏“欲以‘情感哲學’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認為這是“為八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是“發二千年所未發”。(注:梁啟超:《戴東原圖書館緣起》。)孫叔平先生則更是明確地指出:“戴震是‘五四’運動以前對封建禮教發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注: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其三,作為“五四”時期,徽州人是一大旗手。作為擁有30多個博士頭銜,從小就接受徽州文化熏陶的,在這一運動中,提出文學改良,反八股文言;提倡中西文化結合,主張要接受西方文明;引入實用主義,倡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等,這些思想及其實踐在當時以及之后都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是世人公認的“五四”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可見,宋以后徽州哲學學術思想的發展是完整地、典型地體現、反映了晚期中國封建社會哲學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容。
不僅如此,徽州文化的其他內容及徽州社會生活結構與方式也都是這樣那樣地在各自的領域成為中國后期封建文化形態在這些領域的典型投影和標本體現。例如徽商,它就是作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商業發展及商幫形式的一個典型,其“賈而好儒”,賈仕結合,強化宗誼,重視教育的特點;采取走販、囤積、放債、壟斷的經營方式;善于察低昂、權取予等等,無不從中透露了當時中國十大商幫的一般。再如,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人倫、社會生活結構關系等都是恪守程朱理學的教化,人們重忠、重孝、重義、重節等等,而這又恰是以徽州最為典型、顯著。僅以徽州婦女為例,受程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說教影響,徽州婦女殉理學之道者全國最著,休寧人趙吉士曾指出:“新安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注: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民國修訂的《歙縣志》有16本,其中《烈女傳》就有4大本;在徽州為節烈婦女樹立的牌坊也是最多的,從一坊一表到一坊幾表甚或一坊上萬表皆具,如清光緒三十一年,徽州府建了一座“孝節烈坊”,竟集中表彰全府孝貞節烈女性達6萬5千余人,堪稱一奇。可以說,徽州是受中國封建倫理教化最甚,所受影響及毒害最深,體現封建儒教倫理最為典型的地區。
正因為徽州社會與文化是晚期中國封建社會與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標本,因此,這也就決定了它在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發展史上有著獨特與重要地位,對其的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注:見拙作:《徽州文化研究的學術意義》,《新華文摘》,1998年第4期。)
注釋:
③《資治通鑒》卷五十六。
字庫未存字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