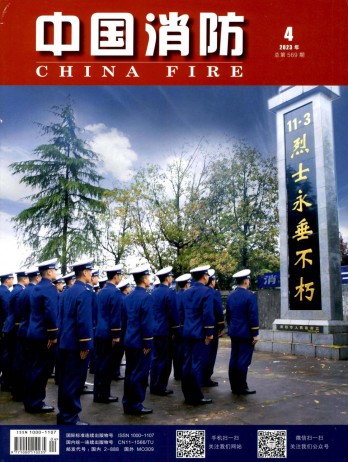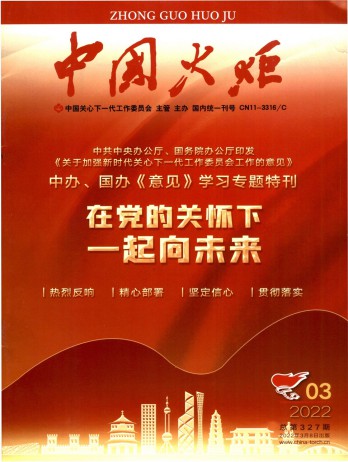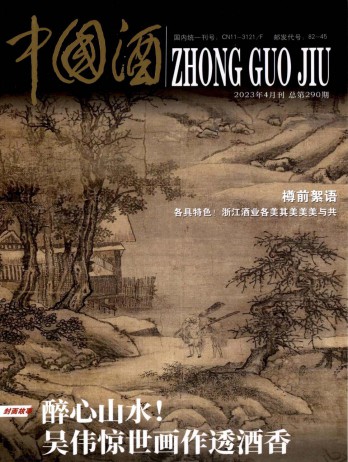中國藝術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4-01 10:12:3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藝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莊子是具有藝術天才的哲學家,對于藝術境界的闡發最為精妙。在他是“道”,這形而上原理,和“藝”,能夠體合無間。“道”的生命進乎技,“技”的表現啟示著“道”。在《養生主》里他有一段精彩的描寫: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若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堯樂章)之會(節也)。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棨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交錯聚結處)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道”的生命和‘藝”的生命,游刃于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音樂的節奏是它們的本體。所以儒家哲學也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易》云:“天地絪蘊,萬物化醇。”這生生的節奏是中國藝術境界的最后源泉。石濤題畫云:“天地氤氳秀結,四時朝暮垂垂,透過鴻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藝術家要在作品里把握到天地境界!德國詩人諾瓦理斯(noValis)說:“混沌的眼,透過秩序的網幕,閃閃地發光。”石濤也說:“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藝術要刊落一切表皮,呈顯物的晶瑩真境。
藝術家經過“寫實”、“傳神”到“妙悟”境內,由于妙悟,他們“透過鴻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這個使命是夠偉大的!
那么藝術意境之表現于作品,就是要透過秩序的網幕,使鴻濛之理閃閃發光。這秩序的網幕是由各個藝術家的意匠組織線、點、光、色、形體、聲音或文字成為有機諧和的藝術形式,以表出意境。
因為這意境是藝術家的獨創,是從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觸時突然的領悟和震動中誕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觀的描繪,象一照像機的攝影。所以藝術家要能拿特創的“秩序的網幕”來把住那真理的閃光。音樂和建筑的秩序結構,尤能直接地啟示宇宙真體的內部和諧與節奏,所以一切藝術趨向音樂的狀態、建筑的意匠。
然而,尤其是“舞’,這最高度的韻律、節奏、秩序、理性,同時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動、力、熱情,它不僅是一切藝術表現的究竟狀態,且是宇宙創化過程的象征。藝術家在這時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窮元妙于意表,合神變乎天機”(唐代大批評家張彥遠論畫語)。“是有真宰,與之浮沉”(司空圖《詩品》語),從深不可測的玄冥的體驗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在這時只有“舞”,這最緊密的律法和最熱烈的旋動,能使這深不可測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在這舞中,嚴謹如建筑的秩序流動而為音樂,浩蕩奔馳的生命收斂而為韻律。藝術表演著宇宙的創化。所以唐代大書家張旭見公孫大娘劍器舞而悟筆法,大畫家吳道子請裴將軍舞劍以助壯氣說:“庶因猛厲以通幽冥!”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上說:
“唐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于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于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擲劍入云,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栗。道子于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于此。”
詩人杜甫形容詩的最高境界說:“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前句是寫沉冥中的探索,透進造化的精微的機緘,后句是指著大氣盤旋的創造,具象而成飛舞。深沉的靜照是飛動的活力的源泉。反過來說,也只有活躍的具體的生命舞姿、音樂的韻律、藝術的形象,才能使靜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德國詩人侯德林(Hoerdelin)有兩句詩含義極深:
“誰沉冥到
那無邊際的‘深’,
將熱愛著
這最生動的‘生’。”
他這話使我們突然省悟中國哲學境界和藝術境界的特點?中國哲學是就“生命本身”體悟“道”的節奏。“道”具象于生活、禮樂制度。道尤表象于“藝”。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莊子《天地》篇有一段寓言說明只有藝“象罔”才能獲得道真“玄珠”:
“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司馬彪云:玄珠,道真也)使知(理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色也,視覺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辯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呂惠卿注釋得好:“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非無非有,不皦不昧,這正是藝術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虛幻,藝術家創造虛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際。真理閃耀于藝術形相里,玄珠的皪于象罔里。歌德曾說:“真理和神性一樣,是永不肯讓我們直接識知的。我們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觀照它。”又說:“在璀燦的反光里面我們把握到生命。”生命在他就是宇宙真際。他在《浮士德》里面的詩句:“一切消逝者,只是一象征”,更說明“道”、“真的生命”是寓在一切變滅的形相里。英國詩人勃萊克的一首詩說得好: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國,
君掌盛無邊,
剎那含永劫。”
這詩和中國宋僧道燦的重陽詩句(譯):“天地一東籬,萬古一重九”,都能喻無盡于有限,一切生滅者象征著永恒。
人類這種最高的精神活動,藝術境界與哲理境界,是誕生于一個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這充沛的自我,真力彌滿,萬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脫自在,需要空間,供他活動。(參見拙作《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于是“舞”是它最直接、最具體的自然流露。“舞”是中國一切藝術境界的典型。中國的書法、畫法都趨向飛舞。莊嚴的建筑也有飛檐表現著舞姿。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首段云:
“昔有佳人公孫氏,
一舞劍器動四方,
觀者如山色沮喪,
天地為之久低昂……”
天地是舞,是詩(詩者天地之心),是音樂(大樂與天地同和)。中國繪畫境界的特點建筑在這上面。畫家解衣盤礴,面對著一張空白的紙(表象著舞的空間),用飛舞的草情篆意譜出宇宙萬形里的音樂和詩境。照像機所攝萬物形體的底層在紙上是構成一片黑影。物體輪廓線內的紋理形象模糊不清。山上草樹崖石不能生動地表出他們的脈絡姿態。只在大雪之后,崖石輪廓林木枝干才能顯出它們各自的弈弈精神性格,恍如鋪墊了一層空白紙,使萬物以嵯峨突兀的線紋呈露它們的繪畫狀態。所以中國畫家愛寫雪景(王維),這里是天開圖畫。
中國畫家面對這幅空白,不肯讓物的底層黑影填實了物體的“面”,取消了空白,像西洋油畫;所以直接地在這一片虛白上揮毫運墨,用各式皺文表出物的生命節奏。(石濤說:“筆之于皴也,開生面也。”)同時借取書法中的草情篆意或隸體表達自己心中的韻律,所繪出的是心靈所直接領悟的物態天趣,造化和心靈的凝合。自由瀟灑的筆墨,憑線紋的節奏,色彩的韻律,開徑自行,養空而游,蹈光揖影,摶虛成實。(參看本文首段引方士庶語)
莊子說:“虛室生白。”又說:“唯道集虛。”中國詩詞文章里都著重這空中點染,摶虛成實的表現方法,使詩境、詞境里面有空間,有蕩漾,和中國畫面具同樣的意境結構。
中國特有的藝術——書法,尤能傳達這空靈動蕩的意境。唐張懷瓘在他的《書議》里形容王羲之的用筆說:“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余裕。然字峻秀,類于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在這里,我們見到書法的妙境通于繪畫,虛空中傳出動蕩,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中國藝術的一切造境王船山在《詩繹》里說:“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一勢字宜著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于咫尺,直是《廣輿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為落想時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高日甫論畫歌曰:“即其筆墨所未到,亦有靈氣空中行。”笪重光說:“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三人的話都是注意到藝術境界里的虛空要素。中國的詩詞、繪畫、書法里,表現著同樣的意境結構,代表著中國人的宇宙意識。盛唐王、盂派的詩固多空花水月的禪境;北宋人詞空中蕩漾,綿渺無際;就是南宋詞人姜白石的“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周草窗的“看畫船盡入西泠,閑卻半湖春色”,也能以空虛襯托實景,墨氣所射,四表無窮。但就它渲染的境象說,還是不及唐人絕句能“無字處皆其意”,更為高絕。中國人對“道”的體驗,是“于空寂處見流行,于流行處見空寂”,唯道集虛,體用不到.
二,這構成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和藝術意境的實相。
王船山又說:“工部(杜甫)之工在即物深致,無細不章。右丞(王維)之妙,在廣攝四旁,圜中自顯。”又說;“右丞妙手能使在遠者近,摶虛成實,則心自旁靈,形自當位。”這話極有意思。“心自旁靈”表現于“墨氣所射,四表無窮”,“形自當位”,是“咫尺有萬里之勢”。“廣攝四旁,圜中自顯”,“使在遠者近,摶虛成實”,這正是大畫家大詩人王維創造意境的手法,代表著中國人于空虛中創現生命的流行,細組的氣韻。
王船山論到詩中意境的創造,還有一段精深微妙的話,使我們領悟“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的終極根據。他說:“唯此窅窅搖搖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內,可興可觀,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詩。然因此而詩則又往往緣景緣事,緣以往緣未來,經年苦吟,而不能自道。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是詩家正法眼藏。”“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這兩句話表出中國藝術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唐、宋人詩詞是這樣,宋、元人的繪畫也是這樣。
尤其是在宋、元人的山水花鳥畫里,我們具體地欣賞到這“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畫家所寫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無邊的虛白上。空中蕩漾著“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道”,老子名之為“夷”、“希”、“微”。在這一片虛白上幻現的一花一鳥、一樹一石、一山一水,都負荷著無限的深意、無邊的深情。(畫家、詩人對萬物一視同仁,往往很遠的微小的一草一石,都用工筆畫出,或在逸筆撇脫中表出微茫慘淡的意趣)萬物浸在光被四表的神的愛中,寧靜而深沉。深,像在一和平的夢中,給予觀者的感受是一澈透靈魂的安慰和惺惺的微妙的領悟。
中國畫的用筆,從空中直落,墨花飛舞,和畫上虛白,溶成一片,畫境恍如“一片云,因日成彩,光不在內,亦不在外,既無輪廓,亦無絲理,可以生無窮之情,而情了無寄”(借王船山評王儉《春詩》絕句語)。中國畫的光是動蕩著全幅畫面的一種形而上的、非寫實的宇宙靈氣的流行,貫徹中邊,往復上下。古絹的黯然而光尤能傳達這種神秘的意味。西洋傳統的油畫填沒畫底,不留空白,畫面上動蕩的光和氣氛仍是物理的目睹的實質,而中國畫上畫家用心所在,正在無筆墨處,無筆墨處卻是飄渺天倪,化工的境界。(即其筆墨所未到,亦有靈氣空中行)這種畫面的構造是植根于中國心靈里蔥蘢絪緼,蓬勃生發的宇宙意識。王船山說得好:“兩間之固有者,自然之華,因流動生變而成綺麗,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榮,如所存而顯之,即以華奕照耀,動人無際矣!”這不是唐詩宋畫給予我們的印象嗎?
中國人愛在山水中設置空亭一所。戴醇士說:“群山郁蒼,群、木薈蔚,空亭翼然,吐納云氣。”一座空亭竟成為山川靈氣動蕩吐納的,交點和山川精神聚積的處所。倪云林每畫山水,多置空亭,他有: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的名句。張宣題倪畫《溪亭山色圖》詩云:“石滑巖前雨,泉香樹杪風,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坡《涵虛亭》詩云:“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金。”唯道集虛,中國建筑也表現著中國人的宇宙意識。
空寂中生氣流行,鳶飛魚躍,是中國人藝術心靈與宇宙意象“兩鏡相入”互攝互映的華嚴境界。倪云林詩云:
“蘭生幽谷中,
倒影還自照。
無人作妍嬡,
春風發微笑。”
希臘神話里水仙之神(Narciss)臨水自鑒,眷戀著自己的仙姿,無限相思,憔悴以死。中國的蘭生幽谷,倒影自照,孤芳自賞,雖感空寂,卻有春風微笑相伴,一呼一吸,宇宙息息相關,悅懌風神,悠然自足。(中西精神的差別相)
藝術的境界,既使心靈和宇宙凈化,又使心靈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脫的胸襟里體味到宇宙的深境。
唐朝詩人常建的《江上琴興》一詩最能寫出藝術(琴聲)這凈化深化的作用:
“江上調玉琴,
一弦清一心。
泠泠七弦遍,
萬木澄幽陰。
能使江月白,
又令江水深。
始知梧桐枝,
可以徽黃金。”
中國文藝里意境高超瑩潔而具有壯闊幽深的宇宙意識生命情調的作品也不可多見。我們可以舉出宋人張于湖的一首詞來,他的念奴嬌《過洞庭湖》詞云: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片舟一葉。素月分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悠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發蕭疏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吸盡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對空間之超脫)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對時間之超脫)”
這真是“雪滌凡響,棣通太音,萬塵息吹,一真孤露。”筆者自己也曾寫過一首小詩,希望能傳達中國心靈的宇宙情調,不揣陋劣,附在這里,借供參證:
“飆風天際來,
綠壓群峰暝。
云罅漏夕暉,
光寫一川冷。
悠悠白鷺飛,
淡淡孤霞迥。
系纜月華生,
萬象浴清影。”
(柏溪夏晚歸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