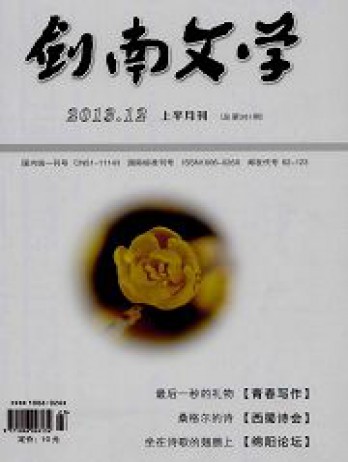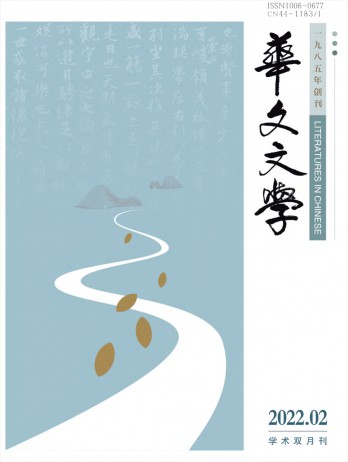文學博士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3-20 16:17:5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學博士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fā)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楚辭》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福《論李賀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fā)展期(隋唐五代)和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tài)和歷時形態(tài)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fā)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xiàn)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xiàn)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tǒng)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詩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四人的詩歌在唐五代和兩宋時期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論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追摹與接受》(2009)、趙艷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論文對白居易的宋代接受進行了論述。陳文忠《〈長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陳友康《〈長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論文則對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此外,白愛平《姚賈接受史》(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對賈島、姚合并稱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張朝麗《論宋末元初文人對李賀詩歌的接受》(2004)、陳友冰《李賀詩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論文對李賀詩歌接受進行了探討;李春桃的博士論文《〈二十四詩品〉接受史》(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接受進行了論述。五代時期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以《花間集》為典型。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花間集》的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范松義《宋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10)、范松義、劉揚忠《明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04)等論文也對《花間集》接受進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宋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變”的立論點,從文體正變、詞史流變、詞風消長、時運盛衰、才性各異等各個方面,對蘇詞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仲冬梅《蘇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對蘇詞接受情況也進行探討。陳福升《柳永、周邦彥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詞在歷代的接受情況。程繼紅《辛棄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討了辛詞的接受情況,上編從南宋慶元以前到當代各大學通行的詞選本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18種選本作為抽樣調查的對象,以總結歸納歷代辛詞接受與消費的規(guī)律;下編通過自南宋至近代王國維的評論,探討批評史中的辛詞接受情況。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齊魯書社2005年版)則對清代辛棄疾詞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時期稼軒詞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宋元時期辛棄疾詞接受進行了探討。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清代前中期的黃庭堅接受情況進行較為詳細地的研究。金元時期的文學接受個案研究以元好問和《西廂記》接受研究為代表。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把元好問詩歌接受史分為三個時期,即形成時期(金元)、曲折發(fā)展時期(明代)、時期(清代)。全書主要是梳理各個時期詩評家對元好問詩歌的闡釋、詩人創(chuàng)作受到元好問詩歌影響的情況,并輔以選本、集本的效果和傳播研究。伏滌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黃山書社2008年版)從刊刻、選本與曲譜收錄、演唱、本文批評、題評考訂、改續(xù)之作、文學影響等各方面探討了《西廂記》在明清時期的接受情況。
(四)小說接受個案研究
古代小說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來研究小說的專著是劉宏彬《〈紅樓夢〉接受美學論》(1992),但該書更多的是美學意義上的探討。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水滸傳》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把《水滸傳》接受史分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現(xiàn)代和當代幾個時期。郭冰《明清時期“水滸”接受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則對明清時期的“水滸”接受進行了探討,分統(tǒng)治者、文人和民眾三個層面來論述。宋華偉的博士論文《接受視野中的〈聊齋志異〉》(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對《聊齋志異》的接受進行了論述,分古典接受階段、建國前的現(xiàn)代接受、建國初期的接受階段、新時期的接受階段幾個時期,并考察了《聊齋志異》的域外接受情況。
二、古代文學接受研究的反思
無庸置疑,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借鑒外來的接受美學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方面,經過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廣泛地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當中,不僅使外來理論得到了本土化轉換和運用,而且開拓了從讀者接受視角研究文學的新視野,促進了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古代文學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經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這既充分體現(xiàn)了“經典”的藝術價值、藝術魅力和藝術影響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對于“經典”研究對象選擇的學術銳敏性,有助于幾千年的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價值得到當代重估和轉化,有助于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復興和繁榮。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古代文學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是接受理論的進一步轉化和深化問題
接受研究強調從讀者視角來研究文學的傳播問題,而讀者接受往往是與文本傳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如何區(qū)分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現(xiàn)實難題。如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雖題為接受史,但一些章節(jié)內容涉及到傳播的問題,如元好問詩文集編定、刊刻顯然是屬于傳播范疇。而有些問題的討論則很難區(qū)分是傳播還是接受。像元好問詩歌的選錄研究,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它是傳播范疇;從詩歌選錄者來看,它又是接受范疇。再如清代元好問詩歌的評點與箋注,從評點與箋注者來看,屬于接受范疇;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又屬于傳播范疇。盡管有些學者已經對文學接受的理論作過一些探討,并且有過文學接受研究的學術反思,但這些理論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圓滿解決研究中的難題。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理清接受與傳播、接受與研究的本質區(qū)別,這樣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開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決傳播與接受的區(qū)分,突出文學接受,還是應該抓住“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因為文學傳播本質上是離不開讀者接受的,沒有讀者接受就沒有文學傳播,在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下,既可以厘清傳播與接受的區(qū)分,也可以對傳播材料作接受解讀,從而深入探討文學接受之于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二是接受研究實踐進一步拓展和創(chuàng)新問題
古代文學接受研究以經典文學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為主,同時也有一些宏觀上的接受研究。其中,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莊子》、《楚辭》、《史記》、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無疑這些個案研究突出了中國文學的經典性,特別是唐詩和宋詞的經典性。但無論是時代的分布上,還是研究對象的數(shù)量上,個案研究中經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廣泛性,采集面顯得較為狹窄。因此,突破唐詩宋詞的視閾局限,進一步拓展經典作家作品對象采集是個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綜述所論,其研究也在存較大問題。宏觀研究一方面要從時間視閾出發(fā)進行通代或斷代接受梳理,探討中國文學的通代或斷代接受情況;另一方面也要從空間視閾出發(fā)進行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情況,探討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或被接受情況。同時,宏觀研究還可從作家群體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學家族接受等方面來創(chuàng)新。宏觀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學與次流文學、主要作家與次要作家之間關系處理,否則宏觀的接受研究就容易變成為個案研究的拼盤,而顯示不出宏觀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視閾問題
篇(2)
漢字視覺造型的“形”與“意”
“形符通過自身形象來其表意作用,義符通過自身所代表的意義來其表意作用”。就像這幅字體設計3-1-1那樣,巧妙的文字組合使得“形”與“意”和諧統(tǒng)一,更好的表達了自身的含義。計以詞義本身以及漢字自身的形體結構為基礎,漢字筆劃與表現(xiàn)水特性以及山間那種悠然與清爽的感覺,對漢字的外形、結構與筆劃的走向做了新的布局,使文字由于重新的組合而產生不同的意境。元素從形式與內涵兩方面反映其信息內容,同時也添加了現(xiàn)代的設計觀念。>>>>>博士論文的初稿完成步驟
漢字最原始的形態(tài)就是人類記錄事物的記號或圖案,逐步的發(fā)展成為象形符號,經過簡化才成為我們現(xiàn)在的漢字。漢字又可分為“有形”和“無形”兩種。“有形”即有外部的輪廓造型,它注重“形”;而“無形”就是人們對這一具象字體的理解,它注重“意”。漢字與其他民族文字的表現(xiàn)形式不同,漢字至今仍然保存著象形文字的圖畫感覺,字型外觀大體呈現(xiàn)出方形,在筆劃的變化上呈現(xiàn)出不同的含義,這種形與意的結合使得文字兼?zhèn)淞藞D形的形象感與文字的抽象感。
篇(3)
平面設計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文明的起源。古老洞穴上的壁畫就可以看作最早的平面設計作品。它的發(fā)展史也是從最為抽象的漢字符號開始的。在近現(xiàn)代,漢字的圖形化設計最早開始于日本、臺灣等地區(qū)。在日本當代的平面設計中,設計師們對漢字和中國書法的研究和利用似乎更早一些,但日本的設計師主要是從漢字與書法的形式美的角度去尋找可用的設計元素。現(xiàn)在文學碩士論文小編就來給大家講講,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中國的漢字作為獨立的載體,它有著雙重的屬性。它不僅具有傳達信息的功能,同時也具有著圖形化的意境,即可傳情達意。平面設計作為一門視覺藝術,也決定了漢字在其中會占據(jù)重要的地位。
我們也可以見到大量的以漢字或日語假名為基礎元素,用中國書法的表現(xiàn)方式并且加入現(xiàn)代平面構成理念的而形成的作品。從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漢文化的魅力和漢字對世界平面設計領域獨特的影響力。相對于外國設計師來說,中國設計師似乎更善于從中國文化所蘊含的深層意義中去探尋設計元素和靈感,去表現(xiàn)更為本土的民族文化特色。>>>國字產生和變遷中漢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中國現(xiàn)代平面設計的真正興起是在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藝術設計學科的建立和完善,平面設計這一學科也開始逐漸開始出現(xiàn)。而隨著中國平面設計的發(fā)展與成熟,中國的平面設計師將更多的精力轉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挖掘。大多數(shù)平面設計師,已經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汲取漢字以及其它藝術形式的精髓,進行研究與創(chuàng)作,將它們運用到平面設計中,達到更為理想化的完美效果。
希望的文學博士論文等更能吸引您的眼球,能幫助到您,如果要進行,也可以到網站查看。
篇(4)
關鍵詞:劉半農;泰戈爾詩歌翻譯;改寫;社會意識形態(tài);詩學價值
中圖分類號:H15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1)-12-0-02
一、劉半農和泰戈爾詩歌翻譯
“五四”運動前夕劉半農翻譯了泰戈爾的4首散文詩。前兩首發(fā)表在5卷2號(1918年8月15日),題為《Tagore詩二首》,即《惡郵差》和《著作資格》;同年9月又在《新青年》5卷3號上發(fā)表了另外兩首譯作:《海濱五首》和《同情二首》,均是無韻詩。這些譯詩后被收入了《劉半農詩選》中,共收入譯詩40多首,泰戈爾的詩歌占了9首[1]。
以下是他翻譯的《海濱》:
海濱
在無盡世界的海濱上,孩子們會(匯)集著。
無邊際的天,靜悄悄的在頭頂上;
不休止的水,正是喧騰湍激。
在這無盡世界的海濱上,
孩子們呼噪,跳舞,會(匯)集起來。
原詩:
On The Seashore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
The infinite sky is motionless overhead
And the restless water is boisterous.
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The children meet with shouts and dances.
從這則翻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劉半農采用了直譯的翻譯策略,使用的翻譯語言相當?shù)钠綄崳渥咏Y構也幾乎未作任何改變。
另一首他翻譯的泰戈爾的《惡郵差》,同樣體現(xiàn)了非常直白的散文詩的文體特征[2]:
你為什么靜悄悄的坐在那地板上,告訴我罷,好母親?/
雨從窗里打進來,打得你渾身濕了,你也不管。/
你聽見那鐘,已打四下了么?是哥哥放學回來的時候了。/
究竟為著什么,你面貌這樣稀奇?/
是今天沒有接到父親的信么?/
我看見信差的;他背了一袋信,送給鎮(zhèn)上人,人人都送到。/
只有父親的信;給他留給自己看了。我說那郵差,定是個惡人。
這一翻譯策略的選擇植根于當時的社會文化及文學背景,以下做簡要分析。
二、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特征
一種文學形式在文體特征上展現(xiàn)的是文學作品的文本結構形式,在更深層次上卻可以體現(xiàn)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在長期歷史積淀中形成的思維模式和心理建構。這種形式深深植根于這個民族人民的意識形態(tài)中,并同時影響著他們對外在世界的感知和認識。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只有完全沖破舊形式的束縛,才能顛覆舊思維的限制,從而徹底與舊傳統(tǒng)決裂。
當時的的先驅們很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首先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他認為“文學革命”首先應從文學形式入手改革,中國新詩應該使用白話文寫作。1917年,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fā)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他的詩學革命“八事”: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做無病之;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3]。
然而,提倡新詩的先鋒斗士們深知傳統(tǒng)的道德價值觀和文學模式已根深蒂固,一場徹底的文學變革絕非易事。于是他們迫切要求擺脫舊有的詩學模式,從僵化的文言文古體中解放出來,用最平實,最通俗的白話表達他們與舊傳統(tǒng)決裂的決心。因而,相對于詩歌的內容,他們當時文學革命的重點更在于語言的徹底革新。
劉半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文學革命的先行者,和周作人錢玄同俞平伯等一道熱情支持的觀點,并積極投身“白話運動”,“提倡白話,反對文言”。他也是中國最早關注并翻譯外國詩歌的文學家之一,他在“五四”運動爆發(fā)前夕翻譯了一些散文詩,并在他的《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中清楚地闡明了他翻譯這些詩體的目的。他翻譯這些詩歌的意圖是配合當時正蓬勃興起的,希望在詩歌方面打破古典詩歌舊格律的束縛。因為這種詩歌字數(shù)多少不拘,無嚴格的韻律要求,有助于詩體解放和沖破舊格律的束縛。
三、劉半農在那個時期自身的創(chuàng)作風格
劉半農嘗試用白話文翻譯外來詩同他自己白話詩的創(chuàng)作是相輔相成的。以下是他寫于1917年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白話詩,被收錄在他的《揚鞭集》里:
相隔一層紙
屋子里攏著爐火,
老爺分付開窗買水果,
說“天氣不冷火太熱,
別任它烤壞了我。”
屋子外躺著一個叫化子,
咬緊了牙齒對著北風喊“要死”!
可憐屋外與屋里,
相隔只有一層薄紙。
不難看出,這首詩相當?shù)闹卑缀秃唵危灾劣诓幌裨姟km然似乎用詩的形式呈現(xiàn),但所使用的語言更像是日常用語,根本談不上“詩意”。
這種表現(xiàn)手法同樣清楚的體現(xiàn)了中國新詩在初期創(chuàng)立階段對傳統(tǒng)的顛覆和對新語言模式的嘗試。初期新詩一方面表現(xiàn)為,用散文的語言來表述和規(guī)范新詩的語言形態(tài),將作詩如說話視為現(xiàn)代新詩語言的表述理想。如所說的,初期新詩的語言應該是一種“說話”語言:“要須作詩如作文”,“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另一方面則是以傳統(tǒng)漢語詩歌的語言表述為參照,試圖取消任何規(guī)則化的詩歌語音表述[4]。
四、結語
結合以上分析,劉半農這種翻譯策略的選擇和他自身的詩歌創(chuàng)作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文學界普遍的迷惘和困惑,眾多的作家進行著嘗試,但努力的方向似乎更傾向于徹底打破中國舊有的詩學傳統(tǒng),而對于中國新詩的模式沒能形成統(tǒng)一的認識,以至于形成如此“直白如話”的“詩”體語言,把詩寫成了分行的散文。這種翻譯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作出的選擇,是對原作的改寫與操控。可見,翻譯不是單純的文學行為,它受到目標語文化系統(tǒng)中各因素的影響,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并與其他子系統(tǒng)交相輝映。
參考文獻:
[1]劉半農.劉半農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張羽.泰戈爾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D].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2:150.
篇(5)
一、現(xiàn)當代文學的現(xiàn)代性內涵
針對現(xiàn)代性的探討,部分學術界專家認定其屬于時間概念,還有一些認定其是與傳統(tǒng)觀念相區(qū)別的概念,是不斷發(fā)展、變化并且逐漸自我完善的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在學術界里,許多的專家認為,文學的現(xiàn)代性是與審美相互關聯(lián)的,這是由于文學自身就具有審美的意義。總的來說,文學現(xiàn)代性是難以被全面解釋的,它屬于一個整體,具備著啟蒙、審美的作用,它的核心就是審美現(xiàn)代性。
二、現(xiàn)當代文學的現(xiàn)代性特征
(一)審美現(xiàn)代性有悖論性
文學中的審美現(xiàn)代性和社會中的現(xiàn)代性具有很大的不同,文學中的審美現(xiàn)代性不但研究了技術現(xiàn)代性,同時對個體、語言、審美觀念以及主題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文學現(xiàn)代性包含了我國人民價值觀念、理想、現(xiàn)實生活以及情感寄托等方面。從屬于文學現(xiàn)代性的審美現(xiàn)代性具備稍縱即逝的特點,它所包含的一部分輕易就會流失,而與其相對的另一部分卻會永垂不朽,所以就需要利用各種方式把易逝的這部分保存下來并且將其轉變成不會消失的特質。文學審美的現(xiàn)代性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推動審美意識的發(fā)展與成熟的同時,也會對傳統(tǒng)的觀念帶來負面影響。在我國的現(xiàn)代文學的現(xiàn)代性中,具有經驗世界具體性與當代經驗片面性的特點,因此,就需要認真地研究每個國家的文學現(xiàn)代性,利用其他國家正確的觀念來完善我國現(xiàn)代文學的整體性。
(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現(xiàn)代性發(fā)展兩難性
我國現(xiàn)代文學所具備的現(xiàn)代性,不只是吸取了歐洲的研究成果,也有著本身的明顯特征,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歷史差異。歐洲的現(xiàn)代文學中的現(xiàn)代性是為了對抗古典文學,然而我國的現(xiàn)代文學不但要展現(xiàn)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特色,同時還要在完善現(xiàn)代性的同時避免出現(xiàn)因副作用而產生的影響。第二,表達方式差異。在歐洲的現(xiàn)代文學中,它的現(xiàn)代性特征是推翻傳統(tǒng)藝術后所展現(xiàn)出來的,是利用比喻、象征等方式來表達一個非理性的世界;而我國的現(xiàn)代文學則是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這兩座大山中艱難生長,具備文學藝術中的先進性與探索性的特征,是用積極的方式展現(xiàn)我國人民具有的獨特的民族精神。第三,自身體制差異。歐洲的現(xiàn)代文學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資本制度為基礎,對個體的精神異化展開研究,尋找個體最適合的定義;我國現(xiàn)代文學以集體為基礎,社會現(xiàn)代化和民族解放獨立就是其核心目標。歐洲的現(xiàn)代文學盡管給我國的文學發(fā)展產生了較好的影響,不過依然難以創(chuàng)造一個更好的平臺,這也就造成了我國的現(xiàn)代文學不但質疑我國的傳統(tǒng)藝術,同時也質疑歐洲的文學藝術,使其難以繼續(xù)發(fā)展。
(三)文學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的怨恨情結
我國的現(xiàn)代文學在不斷探索現(xiàn)代化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抵制現(xiàn)代性,在傳承文化的基礎上,又難以正確處理其落后性,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術界也就有必要理清我國現(xiàn)代文學利弊共存的局面,使其不會將審美觀念總結為“怨恨”。然而我國現(xiàn)代文學所具備的現(xiàn)代性卻和這種怨恨相互關聯(lián)。由于我國現(xiàn)代文學所具備的這種現(xiàn)代性是在歐洲文學的啟發(fā)下進一步發(fā)展而來的,所以,我國現(xiàn)代文學所具備的現(xiàn)代性不但表現(xiàn)在現(xiàn)代化和傳統(tǒng)相互矛盾的怨恨,同時也表現(xiàn)在中國與歐洲文化差異的怨恨。
(四)文學現(xiàn)代性的轉型
在觸及到我國現(xiàn)代文學中現(xiàn)代性所引發(fā)的研究,我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變化,在作者看來,我國現(xiàn)代文學中存在的現(xiàn)代性變化是由的《文學改良芻議》引發(fā)的,從現(xiàn)實社會來看,魯迅是在文學藝術以及個體精神等層次來表達文學現(xiàn)代性。茅盾在《蝕》中,利用知識青年的精神感覺來表達文學現(xiàn)代性,《子夜》就是利用渡船、炊煙、火車來表達人物的內心感受。在魯迅、茅盾、等現(xiàn)代作家的帶頭下,我國現(xiàn)代文學具備的這種現(xiàn)代性日益變化,同時將我國現(xiàn)代文學推向了現(xiàn)代性的潮流中,并且慢慢地剔除了我國現(xiàn)代文學中現(xiàn)代性的缺點。
篇(6)
印象最深的是他塑造的福斯塔夫這個角色。他出現(xiàn)在《亨利四世》和《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是以惡為天職的一個無惡不作但又極具喜劇效果的一個角色,一個寧愿全天下人去送命而他自己絕對不想去面對任何危險的人。他自私、邪惡,撒謊、偷盜、賴賬等無所不做,用他自己的話說:“難得賭幾次咒;一星期頂多也不過擲七回骰子;一年之中,也不過逛三四百回窯子。 ”(《亨利四世》朱生豪譯)
他在《亨利四世》中曾經討得哈爾親王的歡心,謀得一軍職,是哈爾親王“放蕩行為的教師和向導”。在《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他是沒落的爵士,在溫莎的小店里打發(fā)時光,調戲福特太太和佩奇太太最后卻被他們捉弄。福斯塔夫滿口的“死烏龜”“勾搭”“綠帽子”等,我有時候讀著會想,這些話與我們經常說的“污言穢語”又有什么區(qū)別。莎士比亞的劇本有不少這類的語言,就算是在他最著名的悲劇《李爾王》中,李爾王罵起自己的女兒貢納莉來,也是口出“沒有良心的”(朱生豪譯)之類。這樣的語言讀
艾文河景色
前兩年春天的一個周末,當時我還在英國。正在一邊吃飯一邊看《英國達人秀》,我被評委西蒙?考威爾(Simon Cowell)一句“Ihate Shakespeare”(我討厭莎士比亞)給逗樂了。好笑之余,我感到一些吃驚,畢竟,這位英國娛樂節(jié)目的大亨是在收視率如此高的電視節(jié)目上,那般坦率地表達對他們偉大的民族詩人的嫌惡。考威爾為什么討厭莎士比亞對我來說是一個謎,但我也曾討厭過。
無論是幼時的我,還是讀碩士時候的我,甚至于工作以后很多年的我,在讀莎士比亞時,從來都沒有讀出他的偉大,更多的是感覺粗鄙。
起來太不符合我對“偉大”的期待了。
在我過去對莎士比亞的閱讀中,另外一點我無法接受的是他的戲劇作品中的人物的“膚淺”。這個在很多作品中都有,男主人翁或女主人翁往往是被對方的容貌一下傾倒,由此而發(fā)的愛情誓言讀來甚是別扭。
在《第十二夜》中,幾乎以“厭男癥”形象出現(xiàn)的奧麗維婭幾乎拒絕了所有向她示愛的男子,無論他們是什么樣的身份,也不管他們如何堅持不懈。以奧西諾公爵為例,他幾次親自或派自己的仆人去向這位美麗冷峻的小姐表達自己的愛意,但總是得到毫無例外的拒絕。然而莎士比亞卻讓她傾心于奧西諾公爵的俊美仆人西薩里奧。西薩里奧本是女兒身,本名是薇奧拉,她女扮男裝做奧西諾公爵的仆人是出自對奧西諾公爵的愛戀。西薩里奧俊美、年輕,奧麗維婭毫不顧忌對方的男仆身份,大膽示愛。
莎士比亞安排一個薇奧拉的雙胞胎哥哥西巴斯辛的出現(xiàn)才算解了圍。西巴斯辛莫名其妙地被奧麗維婭當成了西薩里奧,不明就里地跟這位美麗的小姐去了教堂,準備結婚。莎士比亞筆下并不乏這樣的角色,哈姆雷特對奧菲利亞的傾心,朱麗葉對羅密歐的愛等等。
總之,我奔著莎士比亞的偉大去閱讀了他所有的作品,但在與他的作品的相遇中,我卻不是那位容易動心與傾心的讀者,而是充滿了各種懷疑與不置可否,并且在遇到像英國著名作家塞繆爾 ?約翰遜這樣不贊成莎士比亞作品的大家時還暗自稱其為知音。
《莎士比亞導論》――轉變的開始
2013年9月,我去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華茲華斯研究中心做我的博士論文,一年之后,我除了完成博士論文之外還收獲了另外一種與論文無關的情感,即對莎士比亞的認識轉變。這種轉變源于一本小
60 China Campus
123
1.
我們只是負責收集他的作品,將它們呈現(xiàn)給你們,而贊美它們不是我們的職責。這事兒應該由作為讀者的你們來做因此,去讀他,反復閱讀他,如果你仍然不喜歡他,你肯定是還沒有讀懂他。
這是多么及時的遇見,我感覺似乎是莎士比亞自己透過這些紙頁在指點我,所以我又開始了對莎士比亞新一輪的閱讀。當然,在英國無法找到漢譯本,我只能去讀全英文版的。也可能是語言的問題,也可能是我在這次閱讀中考慮到了作為演員的莎士比亞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他根據(jù)自己的演出經驗,考慮到觀眾的反應,所以那些我曾感覺到的粗鄙的語言也似乎并不是什么影響他的偉大之處的污點了。
閱讀他的作品感覺不到一個時不時出來教導讀者的作者的存在,他的作品不是說教式的,也正是這一點得到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約翰 ?濟慈的贊美。濟慈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曾經提到文學史上有兩種崇高,一種是莎士比亞式忘我的崇高,一種是華茲華斯式的自我式崇高。前者是他追求的,而后者是他所不及的。
人性的真實
真正改變我對莎士比亞認識的是我在作品中所讀到的人性的真實,而這恰非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不能為之。莎士比亞對《威尼斯商人》中猶太人夏洛克的刻畫是讓我重新思考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課堂上,在學術文章的閱讀中,我曾經一直認為莎士比亞與當時仇視猶太人的英國人沒有太大的區(qū)別,無論是他所安排的鮑西婭對夏洛克的非難,還是夏洛克最后悲慘的結局,都曾經誤導我的理解。在是非觀充斥我意識的閱讀過程中,夏洛克自然落入了“非”的那一方,那么他所有的悲慘遭遇似乎都是值得鼓掌的事情,而作為讀者的我們頂多會說一句,莎士比亞對猶太人有歧視。
然而我再次閱讀夏洛克時,我發(fā)現(xiàn)了不同之處。莎士比亞給了夏洛克足夠多的筆墨讓他展現(xiàn)作為一個人而非只是猶太人的一面:你們要是用刀劍刺我們,我們不是也會出血的嗎?你們要是搔我們的癢,我們不是也會笑起來的嗎?你們要是用毒藥謀害我們,我們不是也會死的嗎?(朱生豪譯)尤其是那句:“你們要是用刀劍刺我們,我們不是也會出血的嗎?”這在一個想當然認為猶太人就是邪惡的時代是一個多么有力的發(fā)問!
莎士比亞不相信這些所謂天生的邪惡,因此他的夏洛克無論有多么讓人嫌惡的一面,終究也是有讓人憐憫的一面。而讓我深信這一點是莎士比亞所極力展示給世人的是他對其他角色的塑造,比如我在前文提到的福斯塔夫和哈爾親王。福斯塔夫雖然看上去百無一是,但他在《亨利四世》中對蒼老的恐懼獨白多么有力地觸動讀者的心靈。這也是為什么作為讀者的我們雖然覺得他是個惡棍,卻還是有些喜歡這個角色。
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伊麗莎白女王,她如此喜歡福斯塔夫這個角色而希望莎士比亞要再寫一部與他有關的劇作。據(jù)說,《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便是這種希望的產品,此劇顯示了戀愛中的福斯塔夫。雖然福斯塔夫的惡行多了些,極端了些,然而我們也并非不能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們自己的影子,也并非沒有他所有的對時間的恐懼。
《亨利四世》中的哈爾親王成為《亨利五世》中的亨利五世。亨利五世這位戰(zhàn)績輝煌的大英雄也會下令讓自己的士兵在攻打法蘭西的時候奸擄掠,不放過嬰兒和婦女,而且認為這是軍人理應做的事情。因此,莎士比亞在塑造這個大英雄的時候也展示給讀者他狠毒陰暗的一面。這樣的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莎士比亞的作品在我的再次閱讀中似乎都會說話了,告訴我這位讀者曾經落下的精華。
2014年夏天我去了斯特拉福德小鎮(zhèn),徒步走完了莎士比亞的故居,他安息的教堂以及教堂外那長流的艾文河。莎士比亞在家鄉(xiāng)去世時,雖然榮耀地在教堂圣壇欄桿內取得安息的位置,但這并不是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劇作家、詩人或演員,而是因為他繳納一些教堂的什一稅而獲得的教區(qū)長一職。然而如今,全世界的游客來這小鎮(zhèn)卻是奔著這偉大的作家而來。我站在圣壇欄桿外,向莎士比亞的墓碑致以最尊敬的無聲問候。轉身離去走在喧鬧的艾文河畔時,我突然感覺自己與莎士比亞終于和解。
篇(7)
在中國文化史上,散文家陳之藩和小說家金庸與劍橋大學有著奇妙的因緣:兩人皆是劍橋大學的博士。更有意思的是,陳之藩是當了美國大學教授之后到劍橋讀博士,金庸則在中國多所高校有教授之譽后才到劍橋讀博士。在取得名副其實的博士學位時,一個是成就卓越的電機工程專家和散文家,一個則是名揚天下的報人和武俠小說家。兩位杰出華人與劍橋大學的“博士因緣”,堪稱別致的文化奧林匹克精神。
陳之藩:在聊天中探索真學問
本報記者 李懷宇
1969年,在美國任教授的陳之藩獲選到歐洲幾個著名大學去訪問,于是接洽劍橋大學,可惜該年劍橋大學的唯一名額已選妥。陳之藩不想到別的大學,索性到劍橋大學讀博士研究生。
一到劍橋大學,每個人都叫陳之藩為陳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釘上大牌子:“陳教授”。在那里,陳之藩寫下了名著《劍河倒影》。他說:“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從無一人過問你的事。找你愛找的朋友,聊你愛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無所謂。”
英國紳士的中國情懷
陳之藩在劍橋最愛做的事是聊天。讀《劍河倒影》,仿佛是在旁聽一部“聊天錄”。陳之藩說,劍橋的傳統(tǒng),一天三頓飯,兩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著黑袍一塊吃。每天同樓的人都可最少見三次,最多見五次面。“誰知哪一句閑談在心天上映出燦爛的云霞;又誰知哪一個故事在腦海中掀起滔天的濤浪?我想劍橋的精神多半是靠這個共同吃飯與一塊喝茶的基礎上。這個基礎是既博大又堅實的:因為一個圣人來了,也不會感覺委屈;一個飯桶來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飯桶。”
陳之藩聊天的對象都是博學之士,正合劉禹錫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和各門各類的人物的聊天,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道理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證。在《風雨中談到深夜》中,他寫道:“很多有成就的劍橋人,對于在風雨中談到深夜的學院生活,都有一種甜蜜的回憶。比如懷德海、羅素、吳爾夫、莫爾、凱因斯、富瑞,這些是在一室中聊過多少夜的一堆人。他們的行,全不相干,但他們卻有一種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種味道影響到他們的名著的書名。懷德海與羅素的書叫《數(shù)學原理》,莫爾的書叫《倫理原理》,吳爾夫的書叫《政治原理》,凱恩斯寫《貨幣原理》,富瑞寫的是《藝術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為晚上聊天彼此影響出來的。”
身在劍橋,陳之藩已然是英國紳士的做派,但骨子里不時流露出“中國情懷”。陳之藩去看邱吉爾的出生地和墓園,在一幅典型的英國風景畫中,他忽然想起小時念的祖父論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蕩之秋,不有人焉,屈身為將伯之呼,則宗社淪沉,萬劫不復。士不幸遇非其主,無由進徙薪曲突之謀。一旦四郊多變,風鶴頻驚。”他連一個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說成邱吉爾。“當然英國的君主沒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權。這里的‘主’可以解釋成英國人民。我們看只要是英國岌岌可危時,邱吉爾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聽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時,邱吉爾卻總是從容授命,拜閣登臺,扶大廈于將傾,挽狂瀾于既倒。”這樣的奇思妙想也許只有陳之藩才想得出來。
中英文化差別的微妙
同樣妙的是,陳之藩整天東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勸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針。他從未去打針。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談起凱恩斯小時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針的那座樓的斜對面。陳之藩立時就去打針了。陳之藩顯然對凱恩斯這位不世出之天才的見解十分心折,在發(fā)懷古之幽思時,陳之藩更生懷鄉(xiāng)之嘆:“我常常想:我們中國如果有個劍橋,如果出個凱恩斯,也許生靈涂炭不至于到今天這步田地。因為沒有真正人才的地方,所以沒有真正人才出現(xiàn);因為沒有澄明清晰的見解,所以沒有剛毅果敢的決策與作為。”
有一回,陳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鎖自行車的查理王子。陳之藩便同彼得講了宣統(tǒng)在紫禁城里學騎腳踏車的故事,又繼續(xù)講了另一個故事:“那時候,電話剛發(fā)明,當然皇帝的皇宮里也裝上了電話。皇帝想試試電話靈不靈,拿起電話筒來,卻感到茫然;不知打給誰。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認識的人是曾聽過一個楊武生的戲的楊武生。于是只有向楊武生家搖通電話,大喊:‘來者可是楊小樓嗎?’”就在陳之藩大笑之時,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見解:“你覺得一個社會這樣對待一個人,公平嗎?”彼得舉的例子是這位查理王子在每個學生都邀女孩子開舞會時,還未用腿走半步,剛用眼一掃,第二天即上了報。有汽車時,人家說查理王子招搖過市;騎腳踏車,卻總跟來一群人,在旁指手畫腳。“好像命運注定了該受寂寞的包圍,寂寞像濕了的衣服一樣,穿著難過已極,而脫又脫不下來,你說這不是社會在虐待一個人嗎?”足證中英文化差別的微妙,并不是任何一方想當然便可體會。
在聊天、演講、讀書之間,陳之藩提出的論文頗有創(chuàng)見,被推薦到學位會,作為哲學博士論文。畢業(yè)時,陳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適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拿到哲學博士學位。老童生的淚,流了一個下午。我想:適之先生如仍活著,才81歲啊。我若告訴他,‘碩士念了兩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會比我自己還高興的。”
在陳之藩拿到博士學位的四年之后,金耀基去了劍橋大學,寫下了《劍橋語絲》。中國人寫劍橋大學的《劍河倒影》與《劍橋語絲》,為文學史上的“雙璧”。陳之藩是電機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會學教授,都是獨具一格的“文體家”。多年后,兩人在香港中文大學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