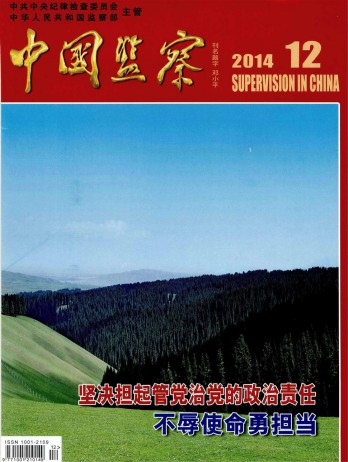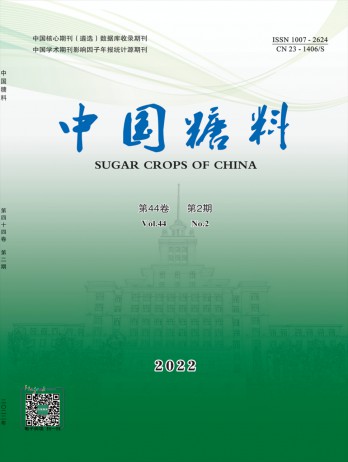中國政治制度史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02-14 06:29:57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政治制度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唐代兵制較為復雜。從兵制演變的角度看,存在著一個從府兵制向節度使兵制變化的過程。這個變化是以士兵的職業化為中心,以士兵身份(或集兵方式)和統領系統為線索展開的。我們將前者稱為府兵制時代,后者稱為節度使兵制時代。
在府兵制時代,存在著多種兵員。從軍隊作用上看,有禁軍、有到京師番上的府兵,有駐屯防戍的防人和鎮軍,還有專事征討的行軍;前兩種是常備軍,后一種屬臨時組建,而不上番和不從征行的在家府兵,則屬預備軍。從士兵的身份上看,既有府兵,又有募兵;前者是征點,后者是召募,因此這也是集兵方式的不同,但二者都有強制性。在行軍和鎮軍中,既有府兵也有募兵,還有以力役的形式承擔軍事任務的民眾,如防丁等。從軍隊的統領系統來看,府兵平時統于十六衛,行軍則臨時設行軍總管,防人統于都督府,而鎮軍則成為由府兵制時代向節度使兵制時代演進的中介。從軍隊的編制上看,府兵平時的編制和行軍的編制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府兵是身份性的終身兵,但不是職業兵。當他服役時,需要自備一些軍資,但當他不服役時,卻不必向政府承擔其它義務;同時,他們服役也有時間限度。逾期服役的府兵,雖然身份仍是府兵,但政府會對其超役時間予以補償,這就使他們與募兵一樣得到了政府的酬勞,使“府兵募兵化”了。“府兵的募兵化”是政府放棄府兵制的方式。于是,禁軍也直接全部改成了召募。
隨著國家軍事形勢的變化,駐屯于邊地的軍隊日漸增強。承擔這部分任務的軍隊,起初是由都督府統領的鎮戍防人;此后在征服邊地部族后,設置都護府或都督府對他們進行監管,這些都護府或都督府所統領的駐兵,我們稱之為鎮軍或邊軍。再后,隨著這些被征服部族的復興,他們對唐朝邊地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唐廷不得不增加鎮軍的數量和駐屯的地點(這些軍隊主要有兩種來源,一種是行軍結束后留下的屯防軍隊,另一種是面對邊地形勢的惡化,專門在某地設立的屯駐軍隊),這些軍隊突破了原來都護府或都督府的統領范圍,出現了單獨的編制,這就是軍、鎮、守捉、城等。為了加強彼此的配合,充分發揮其作用,唐廷以劃分防區的形式,確立了這些駐屯軍隊之間的統屬關系,形成了安史之亂以前的八個(后分為十個)邊地節度使及其下屬的軍、鎮、守捉、城,于是新的防御體系(各節度使之間的配合)和軍隊統領體系(節度使所統領的軍、鎮、守捉、城)最終得以確立。
無論是府兵制時代,還是節度使兵制時代,從軍隊的性質來看,都有中央軍隊和地方軍隊之別;在安史之亂發生以后,節度使兵制下本屬中央的軍隊逐漸地方化。從士兵的種族來看,又有漢兵與蕃兵之異。
下面,我們就根據唐代兵制的構成和變化情況,對近五十年來大陸地區的唐代兵制研究作一回顧。因已出版多種相關論著目錄,[1] 我們對成果不再一一羅列,僅就自己的理解所及,談些認識;囿于見聞和理解,不當之處,敬請教正。
一 府兵制時代的兵制研究
(一) 關于府兵制
府兵,既是泛稱也是專稱。我們所講的府兵制是專稱,是指起源于西魏、北周,經隋代的變化而入唐的一種軍事制度。它既表明這一制度下的士兵具有身份性,也表示這種兵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軍隊組織體系;同時,其內涵前后又有變化。在唐朝的府兵制時代,府兵制當然是兵制的主體,但還有其它相關制度與之配合,為其補充。府兵制淵源于西魏、北周,但唐代的府兵制纔是本文的重點,對其淵源的研究,祇在必要時作些回溯而不予展開。
關于府兵制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對相關史料的補充和訂正。《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了各地折沖府的設置,《新唐書·兵志》又較為集中地記載了府兵制的各個方面,而《唐六典》、《通典》、《舊唐書·職官志》、《唐會要》、《新唐書·百官志》等記載典章制度的史籍中,也從官制的角度,談到了府兵制的組織、設官、祿秩等。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對唐代兵制記載最為集中和系統的《新唐書·兵志》進行了全面梳理,考辨異同,定其是非,為進一步研究兵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學基礎;其中卷一是對府兵制的箋正。[2]
折沖府的設置和分布,是最早引起學者注意的一個方面。勞格、羅振玉、谷霽光、岑仲勉等都曾利用金石、敦煌文書、時人文集等史料,對折沖府的府名、分布、數目進行了考訂,證實了折沖府設立最多的地區是關內道,表現了李唐王室居重馭輕的政治意圖。[3] 其中,對折沖府的總數和河北道的設府與否成為爭論的一個焦點。[4]
另一方面,是對府兵制的淵源、流變、運作等情況所進行的研究;當然,這一研究的基礎仍然是對相關史料的解讀和辨析。陳寅恪在《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中,[5] 首先揭示出府兵制淵源于鮮卑部落兵制,有一個復雜的變化過程,即“由西魏制變為唐代制”,特別指出不能以后期的史料來認識前期的制度。具體而言,在軍隊統領上,是由鮮卑部落兵制下的酋長領兵制變成為君主直轄制;這一變化發生在北周。從士兵的身份上看,則是由兵農分離的職業兵,變成為兵農合一之制;這一變化發生在隋代。這篇文章點出了府兵制的關鍵之處,將府兵制研究提高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此后的研究,或許對他的看法存在著不同意見(如對府兵淵源于鮮卑部落兵制含義的論證,對兵農合一的爭論等),或許對府兵制的勾勒更為具體,但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對府兵制的理解和認識大致不出這一范圍。換句話說,此文對府兵制的研究具有質的推進,后人的許多研究都是在此基礎上的量變。當然,這篇文章的范圍是府兵制的前期,對唐代府兵制的情況涉及不多。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在對府兵制研究進行全面清理的基礎上,對府兵制作了系統的勾勒,使我們對這一制度的了解更加清晰。可以說,這是一部府兵制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與此前的研究相比,特別是與陳寅恪的研究相比,他不僅勾勒了府兵制的組織系統,還強調了家兵部曲與鮮卑兵制的關系、北周府兵與鄉兵的關系(鄉兵是如何通過納入府兵系統而中央化的)、府兵與其它兵制的關系(如府兵與禁軍的關系)、隋后期府兵與內外宿衛軍及中外軍的關系、府兵制與軍鎮城戍及邊兵的關系等,糾正了府兵制是隋唐惟一兵制的誤解(這一點,是我們認識府兵制上的又一個重要的躍進,可惜當時未能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同時,還指出了府兵制與地方州郡的關系等。總的來說,這部著作使府兵制的研究更為具體而深入了。[6]
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以后,大多數歷史研究者已將史學觀作為自己研究歷史的指南,多從經濟的角度來認識歷史上的方方面面。研究者將府兵制作為上層建筑,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加以審視,是當時研究府兵制的一個主要方向(《府兵制度考釋》也從經濟角度對府兵制進行了思考,探討了府兵制與均田制、賦稅制的關系;還運用的國家學說,探討了府兵制的職能等)。這樣的研究,一方面為研究者認識這一制度提供了新的視野,但也過于公式化。比如,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作為上層建筑的府兵制,其經濟基礎就是均田制;府兵制的設置、破壞,都是由均田制的實施和破壞決定的。從邏輯上說,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但并不是說,上層建筑的一切變化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事實上,所謂府兵制的破壞,是政府為適應新的軍事形勢的要求,通過將府兵變成募兵的方式,放棄了府兵制。國家能夠對上層建筑進行主動的調整,而不都祇是被動的接納。
總之,陳寅恪之后的對于府兵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府兵制的淵源和演變,(二)府兵制的組織體制及其與其它武裝力量和地方州郡的關系,(三)府兵制這一在中國古代史上頗具特色的兵制,其存在及崩壞的原因,(四)對唐代府兵制研究的加強。
敦煌、吐魯番文書在府兵制研究中的應用,使我們對府兵制的了解更為具體,還印證或補充了相關史料的記載。史料中記載了府兵的主要職責是番上和征行、鎮守,但對鎮守的記載很少且很模糊。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西州府兵》,[7]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對西州府兵的檢點、衛士所承擔的征鎮防戍之役作了全面勾勒。特別是對史籍中語焉不詳的府兵的鎮戍鎮守(鎮守分為兩種,一種是軍鎮的鎮守,一種是鎮戍的鎮守),即充當防人的服役情況,以及在此期間所承擔的各種雜役的勾勒,尤為重要。另外,按規定,府兵需到京師上番宿衛,但文書中并沒有發現當地府兵到中央上番宿衛的史料。唐先生特別點出了這一點,但未作論述。張國剛則認為府兵上番分為到中央服役和在當地地方服役兩種。[8] 我們認為,張先生舉出的府兵在地方所服之役,與唐先生所舉出的府兵在充當鎮戍防人期間所服的各種雜役之間的關系,可能是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這一問題的解決,無疑會進一步加深我們對府兵番役的認識。
府兵的資裝問題,史籍記載更為簡略和原則;吐魯番文書則提供了許多詳細的情況。孫繼民《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府兵裝備》,討論了府兵的馬匹、器仗、資裝等情況;[9] 陳仲安、張國剛等則對“府兵隨身七事”也進行了考辨和分析。[10]
(二) 與府兵制相關的諸方面
府兵制無疑是唐府兵制時代的兵制的主體,但從兵員上說,府兵并不是當時惟一的兵員;政府常常通過召募結集軍隊,這就是所謂的募兵或兵募。
募兵是相對于府兵而言的。從集兵方式來說,府兵是征,募兵是政府出資召募,二者都具有強制性;從身份上看,府兵具有身份性,而募兵則不具有身份性,事畢放歸,仍為百姓。唐耕耦較早注意到了這一問題,[11] 張國剛則對其行賜與資糧作了進一步探討。[12] 但他們二位都強調了兵募制是既區別于府兵又區別于唐后期募兵制的一種獨立的兵制。其實,唐前期之所以強調募,主要針對的是府兵;唐后期的士兵無論是長期服役還是短期服役,都是由募而來。士兵服役由短期而變為長期乃至終身,是軍隊職業化的過程,與上述相對于府兵來討論的募兵并不完全是同一個問題。至于唐后期“兵募”這一名稱已不易見,是因為這一時期兵士都是由募而來,而且對他們有了固定的稱呼,即“健兒”;這并不涉及制度的變化。
其次,府兵是輪番服役,且以防戍為主。正在上番的軍人,總數不過十幾萬人。遇有戰事,即需臨時組建軍隊,這就是所謂的“行軍”。可以說,行軍是府兵制的一個組成部分。
較早注意并對行軍進行系統研究的是孫繼民。他在1984年完成了《從吐魯番文書所見的行軍制度》;[13] 此后,在一系列有關行軍研究的文章的基礎上[14],出版了《唐代行軍制度研究》一書[15]。該書對行軍的統帥、軍將及其僚佐,行軍的編制、兵種,行軍的偵察、預警,戰略戰術、后勤保障等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盡的考述。這是學術界對這一問題所作的第一次系統周密的研究。他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對行軍所作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在其《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第三編與行軍有關的文書”中。
敦煌吐魯番文書也提供了許多行軍個案及相關細節。唐長孺《唐西州差兵文書跋》對金牙道行軍總管命令地方結集兵員的情況進行了考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指出垂拱年間隨著軍事形勢的漸趨緊張,兵員也漸感不足,按常規征點府兵和白丁從軍已不足應付當時的戰局,為此,他們要求征發本不應參與征行的三衛。垂拱年間成為唐前期兵制轉變的一個關鍵時期。[16] 還有不少利用文獻對文書中所出現的具體行軍個案進行過勾勒和稽考,但總的來說,對文書的考釋超過了對行軍本身的研究。
既非府兵,又不經政府召募,而是以徭役的形式承擔軍事任務的人,就是防丁。唐長孺在《敦煌所出郿縣尉判集中所見的唐代防丁》中,對此作了討論。[17]
二 節度使時代的兵制研究
唐前期存在一個府兵制向新的兵制演變的過程。唐長孺是首先注意到這一問題,并對此進行了系統論證的學者。他把這一變化過程概括為從府兵制向軍區的演變,這不僅打破了人們對府兵制的理想化的理解,指出了軍區(即軍鎮守捉)的成立更有利于完成軍事任務,而且打破了將府兵制視作唐代惟一兵制的誤解,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唐代兵制的認識。此后關于唐代兵制演變的研究基本上是順著這一思路來進行的。 [18]
孟彥弘《唐前期的兵制與邊防》對府兵制、節度使兵制的內涵作了明確界定,以士兵身份和軍隊統領系統為線索對其間的演變軌跡作了勾勒。特別是點出了“府兵的募兵化”,認為所謂府兵制的破壞,實際上是政府在新的軍事形勢下,對府兵制的放棄。均田制是府兵制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它破壞的原因(政府放棄府兵制時,均田制還沒有破壞到連府兵制都無力支持的程度)。在統領系統上,則經過了從都督府到都護府再到節度使的變化。[19]
對這一變化,許多學者歸納為從行軍到鎮軍。這是從軍隊作用的發揮形式著眼的。這確實是軍制轉變的一個方面,但卻忽略了軍人或兵員本身的變化。同時,并不是所有的鎮軍都是由行軍變化而來的,如鎮戍防人,如都護府所統領的軍隊,如平高昌后調往鎮守的軍隊等。岑仲勉就直接視之為廢府兵制之后出現的“邊兵”,而沒有把它視作與府兵制有內在關聯的變化。[20] 因此,這一概括不夠全面和準確。
所謂節度使兵制下的軍隊,就是藩鎮軍隊。軍隊的性質前后有很大變化,即由國家的軍隊一變而成為地方的軍隊;其契機就是安史之亂。[21] 對藩鎮以及藩鎮軍隊研究最多的是張國剛。他關于藩鎮分類、兵變等問題的研究,對后來正確理解唐后期的所謂藩鎮割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成果都收集在其《唐代藩鎮研究》論集中。[22] 他在《唐代健兒考》中,對藩鎮軍隊的士兵待遇和家口糧作了很好的勾稽,[23] 打破了士兵為爭得對家口的供給而要進行兵變的認識。[24] 《唐代藩鎮軍將職級考略》對嚴耕望所未考或所考未詳者作了考證,主要有都頭(都知兵馬使)、兵馬使、同兵馬使·散兵馬使·同散兵馬使、十將、散將·同十將(同正將)·同副將·同散將、押衙(牙)、虞候、教練使等。[25] 在《唐代藩鎮的軍事體制》中,指出了藩鎮軍隊包含三個部分,即駐守于州的牙兵、各個支州支郡的駐兵、各縣的軍鎮等。[26] 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對唐代方鎮的文職僚佐進行了稽考編年。[27] 這雖然不是對制度的考察,但這一工作卻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相關問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三 其它方面
唐代兵制的一些方面是通貫有唐一代的,或者說,是兼跨府兵制時代和節度使兵制時代,雖然也可能因兵制時代不同而內容有異。比如蕃兵、團結兵、軍事武器、烽燧制度等。
在兵員的民族成分上,除漢人充兵外,還有大量的游牧部族參與了唐廷的軍事行動,這就是所謂的蕃兵。但同是蕃兵,他們之間又有區別。一種是保有其部落,而且也未必降附唐廷;另一種是不僅歸附唐廷,而且不再有部落的組織形式。[28] 同時,唐前期還有一種見諸史籍的“兵員”,就是城傍或城傍子弟。
方積六在討論團結兵時,糾正了日本學者認為城傍是團結兵的看法,指出他們是因戰敗或主動歸附而遷入唐境的北方游牧部族,因此,他們主要是在河北、朔方地區,時間是在天寶年間以前。他們不是團結兵。這是對城傍認識的一個質的突破。[29] 在此基礎上,李錦繡不僅將因歸附而被安置在軍鎮周圍的“城傍”一一坐實,而且指出從武后時開始,他們逐漸被納入到了邊軍的正式軍額中,變成了唐廷邊軍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過程完成于安史之亂中。至此,作為兵員之一種的“城傍子弟”已基本搞清。但她將“側近軍州”、“側近人”等都視作城傍,則似嫌寬泛。同時,她從陳寅恪所提出的文化史觀著眼,認為這部分人是造成唐后期藩鎮割據的主要原因。[30] 這一看法,雖是對作為兵員的城傍研究的深入,但結論本身卻有些簡單化(陳寅恪以“胡化”來解釋河北的割據,是把具有強制力的國家控制與文化、民族差異等同看待,已使問題簡單化了)。
至于以部落或種族形式參加唐廷軍事行動的“蕃兵”,實際上并不是唐廷的兵員,而是向他們借兵而已,如幫助唐廷討伐安史之亂的回紇等。[31] 嚴格說來,這并不是一種軍事制度。
從武則天時起,唐廷在地方組建屬于民兵性質的地方部隊,即團結兵。方積六對團結兵的數量、團練使與團結兵之間的關系作了精辟的辨析,糾正了日本學者的誤解;并對唐后期團結兵情況作了描述。[32] 張國剛《關于唐代團結兵史料的辨析》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除健兒、彍騎之外的兵募、防丁、屯丁或土鎮兵都是團結兵;這些人不是職業兵,不具有身份性,在役為兵,放役為民。兩人對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書中所提到的“團結”的含義有很大分歧:方積六認為是動詞,而張國剛則認為是指團結兵。[33] 對史料理解的不同,導致了對團結兵人數估計的不同,從而決定了兩人對“團結兵”之所指也有了分歧。我以為方先生的理解更為妥當。唐后期朝廷對軍隊進行過一次整頓,這就是《唐會要》卷七八“諸使雜錄上”所載:“其兵士量險隘召募,謂之健兒;……當上百姓,名曰團練。”此后,地方上民兵性質的軍隊就有了統稱。當然,可能團結兵本身有一個從專稱到統稱的過程,因此也就有所指內涵不盡一致的情況,而不應一概視之。
與此相關,還有“子弟”,它是一種類似于兵役的役。有人徑視之為兵役,而且認為這是兵役之一種。這種理解或欠妥,因為子弟在唐代并不是專稱。只能說在“役”中,有子弟一項;雖然此役與軍事密切相關。
唐前期在府兵系統之外,有獨立的禁軍。安史之亂以后,隨著軍隊的地方化,中央不得不再組建軍隊,這支軍隊就是以神策軍為中心的中央直屬部隊。這支部隊與其說是禁軍,不如說它是相對于地方藩鎮部隊而言的中央部隊;或者說是中央軍隊與禁軍的合二為一。關于唐前期的禁軍,唐長孺在《唐書兵志箋正》卷三中有所考證。唐后期的禁軍因與宦權專權關系密切而受到大家的普遍關注,成果也較多,比如齊勇鋒《說神策軍》、[34] 賈憲保《神策中慰與神策軍》、[35] 張國剛《唐代的神策軍》等[36]。
關于軍費支出,陳明光《唐代財政史新編》和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都有論述。[37]前者過于簡單,后者雖僅出版上卷,所敘述的只是唐前期的情況,卻很詳盡。但是,由于對兵制的情況認識不夠,后者在敘述的分類上頗顯紛亂。她將軍費開支分作隴右監牧費、禁軍及京師宿衛兵費和邊兵費三類,在邊兵費下又對軍器、軍糧、軍衣賜、其它雜費分別作了敘述。在這四類開支之下,是將府兵、募兵、行軍等混同敘述,這就使邊兵與府兵的關系、行軍與府兵·募兵的關系弄得非常混亂,從而影響了我們對唐前期不同兵員、不同費用的認識。
烽候制度與兵制密切相關。關于唐代烽候的情況,可參程喜霖《漢唐烽燧制度研究》中的唐代部分。[38]
四 結語
從研究的時間和過程上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是以府兵制為研究中心。最早是利用墓志等史料對史籍(特別是對《新唐書·地理志》)中所記載的折沖府進行考訂和補充,此后則對府兵制的其它更為重要的方面更加關注,使府兵制的研究取得了質的進步。第二階段是擴大了研究的范圍,注意到了府兵制之外的如募兵、團結兵等方面;節度使兵制也受到了注意(如健兒、方鎮幕府等)。同時,還利用新發現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對府兵制的一些細節和一些史籍記載不甚明了之處進行了勾勒和補訂,取得了不少成果。
從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來看,已有的成果大致可分作以下幾類。第一類成果是對兵制的某一個方面所進行的勾稽,比如勞格、羅振玉等利用金石等史料對折沖府的數目和分布地區所進行的考訂(嚴格說來,這還沒有脫離史料收集的范圍)。第二類成果是對有關兵制的各種不同記載進行辨析,這種辨析是以對史料所記載的制度有相當深入的理解為前提,否則就不可能通過辨異同而定是非;如唐長孺對《新唐書·兵志》所作的全面整理。與此相關,就是靜態地、個案式地恢復兵制某個方面的原貌,比如對兵募、團結兵、健兒等分別進行的勾稽。第三類成果是將兵制視作一個變化的有機整體,研究其演變的過程和契機,探討其與其它相關方面的聯系,比如陳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對府兵制演變的研究,唐長孺《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對府兵制向軍區演變的勾勒(對唐代兵制來說,《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的眼界更寬、范圍更廣)。第四類成果是把兵制放到唐代的社會歷史背景中來考察其意義,比如陳寅恪認為在府兵制時代,軍府的分布和這種兵制本身所具有的兵農合一之制,是地方革命不易成功的原因之一。
從已有的成果看,對府兵制時代的兵制,研究得較為充分;對府兵制向節度使兵制演變的研究也較有深度;而對節度使兵制的研究,則還處在個案研究的階段,缺少全面、綜合性的研究。將兵制置于社會政治中來研究其意義,最為欠缺;但這方面的研究,與研究者對這一時期社會狀況的全面理解密切相關,稍一不慎,就會牽強附會,或求之過深。
從府兵制的研究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出現補充了我們過去對一些問題知之甚少或模糊不清的認識,對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是,它并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基本史籍的基本記載。比如對行軍的認識,對府兵制本身的認識,都因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出現而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細節,為我們認識的深化提供了條件。因此,我們以為,新史料對我們研究唐代兵制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但對唐代兵制總體的認識和理解來說,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魏晉隋唐史研究室編《隋唐五代史論著目錄》(1990—1981),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胡戟主編《隋唐五代史論著目錄》(1982—1995),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第三編(1949—1976),中華書局,1995;盧善煥、師勤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1909—1984),師勤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續編》(1985—1989),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印刷;鄭阿財、朱鳳玉主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出版,2000;等。
[2]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科學出版社,1957。
[3] 勞格《唐折沖府考》,羅振玉《唐折沖府考補》、《唐折沖府考補拾遺》,谷霽光《唐折沖府考校補》;以上四文均收入開明書店輯印的《二十五史補編》中。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二十一節,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4]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5] 該文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三分,1936;后收入《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六節“兵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何茲全撰有書評《讀〈府兵制度考釋〉書后》,刊《歷史研究》1962年6期。后收入其《讀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 該文刊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著《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8] 《唐代府兵淵源與番役》,刊《歷史研究》1989年6期。
[9] 孫繼民《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府兵裝備》,刊《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后收入其《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0] 陳仲安《唐府兵隨身七事辨》,刊中國唐史學會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張國剛《所謂府兵“隨身七事”辨》,收入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
[11]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刊《歷史研究》1981年4期。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二十一節中已注意到了募兵制,但他認為這是在府兵制廢止后才出現的(“隨廢府兵而連帶引起者尚有募兵、邊兵兩個問題”,第213頁),而他所舉的幾個例子又都是太宗、高宗時期。
[12] 張國剛《關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幾個問題》,刊《南開學報》1988年1期。
[13] 該文系武漢大學碩士論文,1984。
[14]《跋〈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隊佐張玄泰牒為通當隊隊陪事〉》,刊《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唐長孺先生在《唐先天二年(713)西州軍事文書跋》中也涉及到行軍中隊的問題,但他認為他考證的這幾件文書是在特定軍事形勢下的地方軍隊。該文也刊于《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15] 該書由臺灣文津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張國剛撰有書評,刊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6] 刊《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
[17] 載其《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
[18]《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刊《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9卷第1號,1948;后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究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二集下冊,中國人民大學,1957。此后,在《魏晉南北朝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第三編第三章“軍事制度的變化”中再次出了更為系統的論說。
[19] 刊《唐研究》第一卷。
[20] 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二十二節。
[21] 見孟彥弘《論唐代軍隊的地方化》,刊陳祖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一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22]《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3] 刊《中國史研究》,1990年4期。
[24] 胡如雷《唐五代時期的“驕兵”與藩鎮》,刊《光明日報》1963年7月3日。
[25] 刊《學術月刊》,1989年7期。
[26] 刊《晉陽學刊》,1991年3期。按:以上各文均收入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中。
[27] 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28] 陳寅恪:《記唐代之蕃將與府兵》,刊《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1期;后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1982。
[29] 方積六《關于唐代團結兵的探討》,刊《文史》第25輯,中華書局,1985。
[30] 李錦繡《“城傍”與大唐帝國》,刊《學人》第8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后收入其《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31] 參張國剛《唐代的蕃部與蕃兵》,載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
[32]《關于團結兵的探討》,刊《文史》第25輯。
[33] 該文見《冊府元龜》卷九九二。
[34] 刊《陜西師大學報》,1983年2期。
[35] 刊《唐史論叢》第5輯,三秦出版社,1990。
[36] 刊《卞麟錫教授還歷紀念唐史論叢》,1995;后收入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