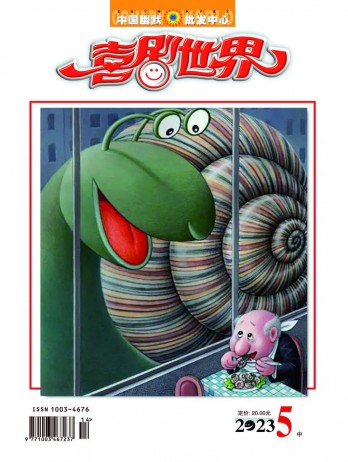世界史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02-09 01:22:4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世界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環境史 環境問題 歷史研究對象 歷史認識論 歷史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環境史研究和教學實踐中,無論是自己的思考,還是同學們的詢問,都涉及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筆者有些心得體會,并通過多種方式,與學生們做過或深或淺的交流。這里,將近年來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總結出來,以饗讀者。
關于環境史研究的意義,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對于不同的受眾來說尤其應該如此。對于從事環境史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學專業的同學來說,筆者重點強調的是,從推動歷史學發展的角度來理解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具體而言,是從歷史研究對象、歷史認識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們知道,史學界已有人認識到,環境史的一個突出的貢獻,是使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時下關注的引起全球變化的環境問題上來,這些問題包括:全球變暖,氣候類型的變動,大氣污染及對臭氧層的破壞,森林與礦物燃料等自然資源的損耗,核輻射的危險,世界范圍的森林濫伐,物種滅絕及其他的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外來物種向遠離其起源地的生態系統的入侵,垃圾處理及其他城市環境問題,河流與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場所的喪失,武裝沖突所造成的環境影響,等等。[1] (P2) 上述認識,顯然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角度對環境史研究意義的一種闡發。簡言之,環境史研究大大拓寬了史學的范圍,其中一個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學家已經將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環境問題或環境災害納入史學的范疇,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對人類歷史內容之認識的一個很有意義的突破。關于這個方面,筆者曾結合洛維特的《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中的一個觀點,[2] 談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維特在書的“緒論”中說到:“無論是異教,還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即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展,這種發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2] (P7) 針對洛維特的這一說法,筆者不敢肯定異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但筆者認同,世界歷史進程的確催生了這樣一種現代思維現象,即歷史在進步,時代在發展;其中一個衡量標尺,是“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體現,則可能是物質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將這種“歷史不斷進步的發展”認識,全然說成是一種“現代幻想”,肯定會惹來眾多的非議,因為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無需用什么深奧的道理,只要列舉憑經驗就能感知并觸摸的諸多事例,就可以指證洛維特的“現代幻想說”的虛妄。
然而,愚見以為,洛維特的上述說法是有著深刻的道理的,因為,時下的環境史研究幾乎可以證明的,不是“現代幻想說”的虛妄,而是“那種現代幻想”的虛妄。換言之,環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展,這種發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確乎是一種現代幻想,因為它可以通過并已通過一個個實證研究,無情地向人們揭示,人類在維系自身存在的同時,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說切斷了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Chain of Being)。這樣,不管他如何抗爭,到頭來未必能逃脫“弒父娶母”的悲慘命運。所以,我們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類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來以“現代化”為發展方向的歷史進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為了現代化進程的祭品。可以說,人類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的同時,也在“自毀長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難與惡;其中最為深重的,可能莫過于人類自己制造的核彈有可能將人類文明及其賴以支撐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還是毀滅”,的確成了問題。并且,今天人類的生死之憂,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樣對“人”的生生死死這一個體問題的憂慮,而是對生養人類的大地母親及其養育的無數生命之存亡的整體問題的思索。因為,如果不諱疾忌醫的話,我們就應該坦承,人類文明的發展其實包含著重重悖論。在一定意義上,人類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無意地破壞了“存在之鏈”。創造即毀滅。人類為改善衣食住行所創造的哪一項物質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為代價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們在發明堅固耐久的材料,用它來構筑平整光潔的路面時,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養,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況,這樣的材料可能還是以挖空、炸碎山體而取得的。
的確,環境史家所研究的各類環境問題,是一個事關包括人類自身的整個地球的“生死之憂”的大問題。由此,筆者認為,即使環境史研究停留在這一層面,也足以體現它存在的價值,因為它已驚醒一度沉睡在“發展”、“進步”之春秋大夢中的人類。在人們當下所制定的應對環境問題的各種措施中,不能說沒有環境史學家所貢獻的智慧。關于這一點,美國環境史學家沃斯特在《我們為什么需要環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頗具代表性。
當然,環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應停留在為人類文明大唱挽歌的層面,畢竟,人類所擁有的理性“又是一個最坦誠的監督者,會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出調整的信號”。[4] (P431) 其實,理性在“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出調整的信號”時,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們斷不能將它們兩者割裂開來。實際上,人類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發出要求人類自身調整的強烈信號的。梭羅、繆爾、利奧波德、卡遜……無數先賢往圣的言與行,正是他們在面對人類偏頗行為時所發出的這樣的信號。我們既然有志于環境史研究,就不僅要學會傾聽和接收這樣的信號,而且還要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宣揚這類榜樣的力量。
從這個方面來說,納什在《大自然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史》一書中,[5] 已經為我們勾勒了如何把握這種“信號”的清晰線索。筆者近幾年在這一領域也有所探尋,并擬定了系統研究的計劃。目前,已從政府立法和民間環保兩大層面著手,指導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導同學研究過英國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針對空氣污染的《堿業法》(制堿業在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被英國人視為污染空氣的大戶)。[6] 在民間環保方面,我們目前關注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相關內容。譬如:關于美國,有同學研究了以繆爾為首的自然保護主義者和以平肖為代表的資源保護主義者之間的交鋒。[7] 關于英國,有同學研究了“國民托管組織”(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環境保護行動,[8] 有同學梳理了“皇家鳥類保護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興起和發展的歷史,并分析了其活動的意義和影響,[9] 還有同學正在研究和總結“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歷史和成就。關于日本,有一位同學從環境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俁病問題,探討水俁病患者與同情他們的人士的維權行為。為此,他去日本留學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資料,還作了必要的調研工作,從而將一個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積極支持水俁病患者并倡導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現出來。他在畢業論文中,花了一節的篇幅記錄了他對旗野秀人的采訪。從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這位“怪人”在幫助那些面對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時,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喚著人們對人與自然之愛的追求。[10]
2006年,我們編寫了《和平之景――人類社會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一書,[11] 該書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紀人類社會存在的環境問題和環境災害,人們面對環境問題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針對環境問題所采取的行動。這項工作的開展,從兩個方面增進了我們的認識。一方面,我們從學科層面認識到了環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歷史內容,以及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我們認為,環境史在開辟新的研究領域,譬如物質環境史的同時,還可以與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軍事史等相結合,從而發展出環境政治史、環境社會史、環境思想史、軍事環境史等眾多的次分支領域。并且,我們已對其中某些領域及相關的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12] 另一方面,我們在思想層面領悟到環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類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劇精神。自近代以來這種悲劇精神的某種體現,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終在與克勞狄斯式的冷靜計算相較量。雖然后者可能一時占上風,甚至仍在變本加厲,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人類文明史中,對真實的、有機的“家園”之愛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斷;對自然之內在價值的倡導似乎越來越成為這個時代的強音。①
以上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層面來談環境史研究的意義的。對此,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就歷史研究領域和主題的擴大,以及重新探討與解釋眾多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討19世紀英國的霍亂,[13] 重新解釋近代歐洲國家的殖民活動[14] 等,環境史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二
那么,從歷史認識論層面,我們又如何把握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呢?對于這一問題,筆者在《世界近現代史基本理論和專題》研究生課程教學中,講過“環境史:作為一種反思的史學理論”這一專題。在此筆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這樣的問題,當史學工作者受到當代環境問題和環境保護運動的影響,而著手研究環境史時,他們看待歷史的視角有什么變化?他們對史學作出了什么樣的新的思考?為此,筆者從認識對象、認識主體和認識中介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強調,當我們說環境史學工作者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來認識歷史運動,意識到人與環境的關系自古以來在每一個時期都具有塑造歷史的作用時,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并深入研究,環境史到底應如何認識人、認識自然、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
關于環境史對人的存在的認識及其意義,筆者曾做過專門的分析。[15] 目前筆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環境史對自然、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認識和書寫問題。對前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高國榮先生在其博士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研究》中有一章專門談及,而且談得比較透徹。筆者認為,環境史研究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時期各文明(包括各學科)中的人們關于自然的“實然”認識外,還應該進一步挖掘他們針對人類自己、約束人類自己而賦予自然的“應然”蘊涵。在這方面,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學無疑是我們從中汲取思想養分的寶庫。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倫理學、深生態學、自然價值論、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等學說或主張,對于我們如何認識和定位環境史的自然觀,可能會很有啟發。在筆者看來,生態價值或自然價值本身,不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為真即可。誰都能感覺到,人類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賴著大自然的恩澤;迄今,人類也只能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得滋養的乳汁,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饒有興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權利和價值作為不爭的事實為何在今天非得經過論證還要大力倡導不可呢?這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而納什在其著作中已為我們勾勒了這一研究的線索。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筆者在教學中從物質、能量和信息之交換的角度進行了論述,現在看來,我們的認識停留在這一步是很不夠的。固然,環境史研究作為多學科交叉的產物,必然要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所提供的數據資料,① 乃至范疇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應滿足于對有關事實的陳述和對外在關系的認識。我們不要將環境史局限于專門之學,而要首先將其主張的人與自然互動的核心理念視為一種通識觀念,以重新考察人類的歷史運動,從而如上文所述,對許多歷史現象作出新的解釋。其次,還要將環境史的人與自然互動理念內化為一種情感。這樣,在涉及人與自然之關系問題時,雖然我們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勝”的論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們仍然主張,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內在的生命關聯,人應該踐行對自然的無條件之愛,而這種愛是不需要論證和計算的。為此,也需要我們通過研究將歷史上本來存在的這類愛與美的言行揭示出來,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之中。
三
還有,從歷史方法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認識和分析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對此,筆者從治史原則、敘述模式與具體方法等方面,談過環境史應有的特色及其推動史學發展的重大意義。譬如,關于環境史的治史原則,筆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這是從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出發,并結合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原則而生發出來的。具體而言,“上下左右”是對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中的上層、下層,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圍的動、植物和其他環境要素。而對上下左右的有機聯系及其歷史變遷的認識和研究,因將社會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勾連起來,從而與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相比,可能會更全面、更準確地反映或揭示歷史的存在。這樣,環境史凸現的“上下左右”的原則,即是對傳統史學的英雄史觀和新史學的“自下而上”原則的繼承和發展。在這里,“繼承”可以從人及其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發展”可以從自然的角度來理解。關于環境史的敘述模式,筆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這是對環境史敘述的立體抽象。其含義是,環境史的敘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種要素,人們通過講述這些要素之間因相互影響、分合交錯而演繹的各種故事,構建了一種立體網絡狀的歷史畫面。② 至于環境史研究的具體方法,尤其是跨學科研究,已有不少學者作了論述,③ 這里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關于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我們可以從諸多方面加以把握。對于筆者個人來說,從事環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擺脫環境無意識、增強環境意識的環境啟蒙過程。這確實是實情,因為在這之前,筆者從沒考慮過自然的意義這類帶有哲思的問題,即使對自然有些認識,那也只是人人在與自然打交道時都必然會有的那種樸素的直觀的想法。現在,筆者這方面的認識多少有些升華,對自然的愛、對弱者的關懷已內化為自己的心性氣質,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較好地遵循深生態學的理念,儉樸、節制已成為一種自覺意識。這樣,筆者從事環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覺、更積極;不盲從、不懈怠。
如果筆者不研究環境史,就產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認識;換個角度說,筆者以前所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并沒有教給筆者上述那些可能更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史學智慧。此外,對于環境史研究的社會功用或現實意義,筆者曾用三句話來概括,這就是:環境史研究是認識環境問題的一條路徑,是解構有關環境問題之不當論調的一種方法,是增強環境意識的一個措施。而且,為了將這種認識運用到對現實環境問題的理解之中,筆者還于今年4月申報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百人工程”項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的兩位朋友,計劃對北京市危險生活垃圾的現狀展開調查,并從廢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們期望,通過關鍵問題和關鍵角度,從一個方面切實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和處理的狀況及存在的問題,以便對危險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置和管理提出具體的建議,并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別是分類回收體系的建設提供決策依據。這一調查計劃已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并已按計劃進行。可以說,這項調查工作的開展,正是環境問題研究者和環境教育宣傳者接觸現實、了解現實問題的一種方式,也是環境史研究的現實意義的一種體現。
[參考文獻]
[1]Hughes,J. Donald.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2006.
[2][德]卡爾?洛維特著,李秋玲、田薇譯. 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M]. 北京:三聯書店,2002.
[3][美]唐納德?沃斯特,侯深譯. 我們為什么需要環境史[J]. 世界歷史,2004,(3).
[4]周春生. 悲劇精神與歐洲思想文化史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美]羅德里克?弗雷澤?納什著,楊通進譯. 大自然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史[M]. 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
[6]郭俊. 1876年英國《河流防污法》的特征與成因探究[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2004屆碩士學位論文;張一帥. 科學知識的運用和利益博弈的結晶――1906年英國《堿業法》探究[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2005屆碩士學位論文.
[7]胡群英. 資源保護與自然保護的首度交鋒――1901-1913年美國人關于修建赫奇赫奇大壩的爭論[J]. 世界歷史,2006,(3).
[8]宋俊美. 為國民永久保護――論1895-1939年英國國民托管組織的環境保護行動[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2006屆碩士學位論文.
[9]魏杰. 英國皇家愛鳥協會的興起、發展及其意義[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專業2007屆學士學位論文.
[10]陳祥. 從日本安田町反公害運動的新模式看地域再生的內涵與意義[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2006屆碩士學位論文.
[11]梅雪芹主編. 和平之景――人類社會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12]賈B. 高技術條件下的人類、戰爭與環境[J]. 史學月刊,2006,(1);劉向陽. 環境政治史理論初探[J]. 學術研究,2006,(9);劉向陽. 從環境政治史的視野看20世紀中期英國的空氣污染治理[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2007屆碩士學位論文.
[13]毛利霞. 霍亂只是窮人的疾病嗎?――在環境史視角下對19世紀英國霍亂的再探討[A].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2006屆碩士學位論文.
[14]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著,許友民、許學征譯. 生態擴張主義:歐洲900-1900年的生態擴張[M].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篇(2)
關鍵詞:新清史;清朝;滿族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6-0037-02
一、新清史的產生和主要研究內容
新清史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最早流行于美國和日本等國家,但是以美國新清史發展為主流。上世紀70年代曾獨霸美國歷史學壇的費正清學派被新興的社會史學派所替代。研究中心從政治、外交、儒學轉移到關注普通民眾和社會的地方史。由西方中心論(以西方人的視角來看待東方的問題)到中國中心論(中國歷史研究實際出發以結合當時具體的歷史背景,解讀中國歷史)。90年代新興社會史學又被新興文化史所取代,而新興的文化史的學者多受到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強調重新解讀史料,重視在傳統史學中邊緣化的群體,如婦女和少數民族。正如歐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動了包括“認同”、“民族主義”、“帝國”等學術討論。近年,又將“想象的共同體”、“被發明的傳統”、“地緣實體”與“國族目的論”有質疑民族國家之自然性質的概念,都納入“新清史”關注的題材。
新清史起源于美國,其受到了社會史學派和新興文化學派思想的影響。所以“美國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有柯嬌燕、羅友枝、勞拉.霍斯泰勒特、歐立德等人。關于美國新清史學者的主要觀點,可以簡單概括為以下四點:
(一)對于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歷史反思
這些美國的新清史學者幾乎都強調少數民族的自身的認同和統治特點。美國歐立德《滿洲之路: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一文也涉及此言論。
(二)“去漢族中心論”
新清史的學者批駁以往清史研究中的滿洲全盤漢化理論,認為由于清朝統治者的強調和八旗制度,在清朝中后期,滿洲人保留了他們民族認同,清帝國之所以成功的控制和開拓廣大疆域,并非因為滿洲人的漢化,而是因為他們保留了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特性,并成功地將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主要有柯嬌燕的著作《孤軍:滿洲三代家族與清世界的滅亡》和其論文《滿洲氏族的來源和演變》、《佟家在兩個世界》、《清史問題》、《清朝開國神話淺論》、《明清史論叢》、《滿洲源流考與滿洲文化的程式化》、《半透明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身份”》美國周衛安《新清史》一文也指出清代疆域管理與族群多遠性契合等等。
新清史的學者強調滿文及其它少數民族文字史料對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性。研究資料采集上,強調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如:滿語、蒙語、藏語等這些非漢語寫成的文獻研究和講述歷史這種以非漢人或邊疆文化視角看清史。
(三)重新審視清朝的“帝國性”
新清史的學者們重新審視了清帝國的擴張這也使新清史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新清史學者,尤其是研究邊疆史的學者,在某些著作中重點討論了清帝國的擴張問題。他們主要討論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清軍在西北地區、西南地區和臺灣的戰爭性質,他們不關心歷史事實本身,而且還關心在這些征服戰爭結束之后,清代學者、民國的學者,以及共和國的學者是如何書寫和構建這些戰爭史,考察政治目的和民族關系對于歷史研究的重大影響。主要代表作有蓋博堅著有《乾隆晚期的學者和國家》,歐立德的《乾隆皇帝》等。
(四)重新審視清朝的“世界性”
新清史從研究空間上看,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而是主張將清朝納入到世界歷史和版圖中重新定位“中國”,在一個亞洲內陸研究空間內。新清史的學者普遍認為清帝國并非一個孤立的帝國,而是作為在16世紀之后歐亞大陸上興起的幾個大帝國: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沙皇帝國等都有許多相似之處,不應該將清帝國同這些同時期的帝國聯系起來。這類著作有柯嬌燕的《世界史:地球及其人民》《全球社會:1900年以來的世界》。
在日本,又有一些學者(包括岡田英弘、片岡一忠、中見立夫、石橋崇雄)也與美國“新清史”有類似的關注,此處不贅述。
二、中國新清史研究趨勢
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對中國清史研究產生影響,這樣中國出現了清史研究的新趨向,我們定義為中國的“新清史”研究。中國新清史研究較之美、日等國要晚,中國新清史研究興起是從何炳棣、羅友枝這兩位學者關于“滿族漢化”“滿洲化”問題討論開始的[1]。事實上,美國新清史所涉獵的問題諸如共同體的形成,民族融合與國家認同,邊疆的特殊化治理,滿族的特殊性等,一直都為中國學界所關注,只不過由于治學的路徑、研究的動因、歷史書寫等諸文化背景差異,使得所關注的相同問題沒能產生聚焦效應和實質性碰撞[2]。如果說“新清史”僅僅在上述研究視角與路徑上偏離中國學界的研究習慣,那么它給學人的應該是新的反思。
關于“滿族漢化”“滿洲化”問題。何炳棣指出羅有枝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系之前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認為強調滿族對于漢族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認同無需排斥對其他形式的認同。他通過中國歷史上個民族漢化過程的考察,指出漢化是一個漫長復雜持續的進程非漢民族的漢化擴充漢文明內肯定滿族只是創造一個多民族帝國杰出貢獻。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中說的那樣從清朝文化以沖突到融合以漢文化雙向互動過程,并卓有成效地維護了滿族個性過程。定宜莊《由美國清史研究引發的敢想》提出清王朝的儒化統治無論怎樣的成功,都沒有將其帶到東北、西北以及等少數民族地區。
關于民族認同感、大一統問題。汪利平對杭州駐防八旗由最初的征服集團演變成為城市中一個群體以及在此過程中滿漢民族關系變化的縱向考慮討論了民族以及族群的認同感。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一文中國皇帝的“中國”觀,是在“華夷之辨”的民族觀的理論批判中逐漸確立起來的。近代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概念也是在清朝統治時期才出現的。葛兆光也“區域研究”以“亞洲”或者“東亞”為研究空間單位,都是對“同一性中國歷史”的質疑。他認為,中國自從宋代以后,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就相當堅實。中國無所謂民族國家的重建。黃興濤重點討論了民族自覺與符號認同之間的關系,認為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形態,是一種全方位、多內涵的現代民族認同運動。楊念群從重新解構“大一統”歷史觀念出發,強調“大一統”模式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疆域”與“族群”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家認同問題。
將清史置于內亞地域空間的研究范式是“新清史”的主要特點之一,應該說“新清史”移置研究空間的預設目的在于強調清朝在內亞擴張的重要性,從而把清朝對周邊的戰爭看做類似于西方殖民擴張行為。劉文鵬解讀張勉治對清帝南巡的闡述,最后其對“新清史”的“內亞”觀點進行批駁。認為“滿族人建立的清朝雖有內亞因素,但是并沒有像13世紀蒙古人那樣繼續西進擴張”。
除了以上這些研究趨勢外,關于新清史中滿族性研究,中方學者也逐漸重視,杜家驥的《八旗與清代政治論稿》、劉小萌的《北京旗人社會》兩部書都是關于八旗的研究,從多層面、多角度揭示了清代八旗在形成過程中的諸多問題,也將八旗作為社會組織和政治、軍事組織來看待,探討它對有清一代政治的影響。它們的出版問世,代表了中國學術界在清史研究中重視清代滿族民族特色、滿漢關系,也暗合了從民族學角度來重新審視清代政治的學術路徑,因此也具有了更深一層的學術意義[3]。對于“滿族性”作為新清史研究關注點來看,擴寬中國學者研究視野有著積極作用其所主張的滿洲特性問題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邊緣化問題了。
三、中國新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發現并研究了中國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在歷史反戰中的主體地位,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財富和文化財富。其所主張的滿洲特性問題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邊緣化問題了。但是夸大甚至只是強調滿洲因素,清朝統治區別于歷代漢族王朝統治,以及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準則提出挑戰。對“中華民族”以國家的認同提出質疑。而這種理論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了潛在的顛覆性。
其次,新清史讓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內部的重要性。
再次,“新清史”研究資料采集上,強調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如:滿語、蒙語、藏語等這些非漢語寫成的文獻研究和講述歷史。這種運用少數民族史料方法,有利于彌補清史研究尤其是社會史中資料研究的不足,有利于從整體上了解清朝歷史。
最后,“新清史”讓我們能夠以更加宏觀的視野審視清代歷史的發展,擴寬中國學者研究視野有著積極作用。特別是發現清代中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系,發現中國歷史在當時的世界意義,有利于我們克服在研究歷史思路上的“閉關鎖國”,但是其移置研究空間的預設動因在于強調清朝在內陸亞洲擴張的重要性,從而把清朝對周邊的征服戰爭看成類似于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行為。給清代貼上了早期殖民帝國標示。
綜上所述,“新清史”在重新審視和重組古代中國歷史時,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是來自某種理論的后設觀察。否認中國認同,還來自歐美的后現代史學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既定發展框架來裁量評判中國歷史的權威傾向。但是也要看到新清史擴寬中國學者研究視野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張婷.漫談美國新清史研究[J].滿學論叢,2011(1):79-80.
篇(3)
東西方音樂的歷史記載,在其形態的表述中有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于音樂本 身的性質與敘述音樂史料的性質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上也是構成音樂史特征的重要依 據。樂譜、傳記、手稿等在歐洲的音樂史研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它們在亞 洲音樂史中卻并非如此,樂譜在音樂演奏和實踐中并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西方音樂 相比可以說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其數量也十分微少(相對來說中國和日本較多 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論書籍、美術、戲劇卻相當豐富。以中國為中心,日本、朝鮮在 一般的史書中以音樂制度、樂律理論、歷史沿革以及音樂美學等的記錄得到了充分地整 理和敘述。它與音樂家的傳記不同,音樂史敘述的整體與音樂的本身同時得到記錄。在 亞洲,除文獻史籍外,考古資料也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 竽、瑟,三號墓出土的筑等樂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遺 址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陶塤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術上的壁畫、浮雕等也 十分豐厚多量,我國新疆地區的庫車、吐魯番,甘肅的敦煌、麥積山,以及柬埔寨的吳 哥(Angkor)、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Borobudur)遺址等都記錄了豐富的音樂歷史 資料。這里值得注意的還有,現藏于日本奈良正倉院的大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絲綢之 路樂器實物,從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它們都是現在世界上 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
(一)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
在亞洲的歷史文獻中,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 了甲骨文,春秋戰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另外,從漢朝開始,在中國的史 料中,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為正統的、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 馬遷首創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為開端,形成了后來的“二十五史”, 被稱作正史。它以紀傳體編輯,體例上分為三大類:①以天子、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為 中心的“本紀”;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傳記,其身份從皇后到 奴隸兼有的“列傳”。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卷“樂志”(“音樂志”或“禮樂志”)。書 中對各王朝的音樂(主要是宮廷、國家、貴族、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從歷史沿 革、音樂制度,到律學、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但沒有樂譜。除此之外,敕撰書中還有 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樂典)、《通志》(卷49、50、64 為樂志)、《文獻通考》(卷128-148樂考)的“三通”與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 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六書,再加 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現 了集歷代政治、經濟、藝術等之大成并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北宋王溥的 《唐會要》(樂類共16個條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會要輯稿》(樂類4 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為細致 ,史料也甚豐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獻通考》(元) 、《唐會要》(五代)等與“二十五史”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其次,除上述 的正史外,春秋戰國以來還出現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著。以內容來劃分,思想、美學方 面的有公孫尼子的《樂記》、荀子的《樂論》、呂不韋所輯的《呂氏春秋》(戰國)、阮 籍的《樂論》(三國);樂律學方面有《管子·地員》、元萬頃等奉武則天之命所作的《 樂書要錄》(唐)、蔡元定的《律呂新書》(宋)、朱載@①的《樂律全書》(明)、康熙、 乾隆敕撰的《律呂正義》(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東漢)、朱長文的《琴 史》、朱熹的《琴律說》(南宋)、朱權的《神奇秘譜》(明)等;另外從斷代史來看,除 正史外,隨筆、筆記、詩詞以及小說等都是記載當時歷史現狀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如有 關唐代音樂有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南卓《羯鼓錄》、(清彭定求 等)《全唐詩》,有關宋代音樂有沈括《夢溪筆談》、陳@②《樂書》、郭茂倩《樂府詩 集》等。有關宋代音樂的除上述文獻外,還有王灼的《碧雞漫志》、陳元靚的《事林廣 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張源的《詞源》等,也 是研究唐宋時期音樂不能缺少的文獻。另有元朝的戲曲曲藝專著、明代以后的大量樂譜 等都是構成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像這樣全面系統的文獻史料在印度、西亞伊斯蘭教 地區以及在歐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這樣詳盡、系統的史料書籍 ,為中國惟有的史料資源。
唐代以后,中國的學術、歷史書籍得到了系統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現了稱之為“ 類書”的體例樣式,相當于今之百科全書。這類書籍大致有《初學記》(唐)、《玉海》 《太平御覽》(宋)、《荊州稗編》《三才圖會》(明)、《古今圖書集成》(清)等。上述 書籍不管是敕撰的還是非敕撰的,它們都是從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羅列出來,分門別 類地進行排列說明的書籍。因此,作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編輯過程中 有訛傳、誤抄的可能,使用中應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史料。
在中國的音樂理論書籍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音律、音階論占據了大量的篇幅, 這同中國儒教的學風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對古事件的解釋存在著反復論述的傾向。這 一現象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初見端倪,像從《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漢 書·律歷志》的五聲、十二律、三分損益法開始,后由西漢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錢樂 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寶年間的俗樂二十八調、南宋蔡元定的燕樂調與十八律,到明朱 載@①的新法密律,他們對三分損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還宮的理論進行了近兩千年的 求索、換算。到了16世紀下半葉,當這個千年不解的轉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時,卻又被 束之高閣、沉睡于書齋樓閣之中。這些理論幾乎都沒有真正得到實踐。
(二)樂譜
從中國的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所遺存的古老樂譜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樂 譜是中國南朝梁琴人丘明所傳(6世紀)的琴譜——《碣石調幽蘭》,該譜的抄卷原藏于 日本京都市上京區西賀茂神光院,現歸東京國立博物館,為唐人的抄本。這是一種用文 字來表述古琴演奏的樂譜。唐代以后出現了減字譜的指法譜、奏法譜(tableture),很 多琴譜都被記錄下來并用于實踐。由文字所記錄的奏法譜,約從唐代開始用于各種管、 弦樂器的樂譜。從中國傳入日本最古老的樂譜,現藏于正倉院的中倉,是一份共有三十 七帖的古文書(寫經紙納受帳),這份經卷上標明的時間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 在其背面寫有斷簡六行,即為《番假崇琵琶譜》亦稱為《天平琵琶譜》。在琵琶譜中還 有773年(寶龜四年)以前傳入日本的《五弦琴譜》(五弦琵琶譜,通稱為五弦譜),現藏 于日本京都陽明文庫。另外,20世紀初在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發現,現藏于法國巴黎國立 圖書館的《敦煌樂譜》,又名《敦煌琵琶譜》,今存三卷。該譜的抄寫年代為五代長興 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時期的重要文獻。中國的樂譜,特別是琵琶譜于平安時期在 日本得到了傳承。《南宮琵琶譜》或稱《貞保親王琵琶譜》、《伏見宮本琵琶譜》由宇 多法皇的敕令南宮貞保親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樂譜的最后附載著 藤原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從中國傳來的《琵琶諸調子品》(二十八個調,實際二十七 個調)以及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紀中葉的長寬元年(1163年)又出現了源經信所作的《 琵琶譜》;由藤原師長所作的12卷琵琶譜《三五要錄》(1138—1192完成);與《三五要 錄》同作者的藤原師長還完成了雅樂箏樂譜的集成《仁智要錄》(1138—1192完成)。日 本平安朝以后的雅樂琵琶譜、箏樂譜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創作,并較自然地傳承了下來。 但是這些樂譜由于對節奏記錄過于簡略,因此至今仍是學者們攻克的難題。
(三)朝鮮
朝鮮與中國地理相鄰,文化交流一直很頻繁,朝鮮深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在史料 的記載方式上與我國有著相似之處。《三國史記》、《三國遺志》、《高麗史》、《李 朝實錄》、《樂學軌范》、《增補文獻備考》等史料以紀傳體、編年體的形式構成主要 的官撰書。《三國史記》為記載朝鮮7世紀前的三國時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羅、百濟和 高句麗歷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其中記述了這一時期受中國音樂影響而形成的早期朝鮮樂 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該史料成書于12世紀,離記事的時期過于久遠,史料的真實性受到懷疑,應慎重使用。而15世紀成書的《高麗史》為紀傳體,其中專門論述音樂的《樂志》部分是了解12世紀初期宋徽宗將大晟雅樂贈給高麗王朝后的歷史現狀,以及當時朝鮮宮廷中的唐的俗樂、宋的雅樂以及朝鮮固有的鄉樂所構成的三樂在宮廷歷史演變的重要音樂史料。《李朝實錄》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構成的編年體巨著,記載了從李氏朝鮮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歷史。其 中15世紀中葉成書的《世宗莊憲大王實錄》是了解15世紀上半葉世宗朝宮廷雅樂的重要 文獻,其中還有大量的禮儀樂與雅樂譜。
在朝鮮的史籍中,除上述的樂器、樂種及宮廷的音樂歷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詞 也占有相當的比例。如歌詞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宮 廷的音樂史料。朝鮮的樂譜大致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傳承下來的,其獨自的文字音標譜 以及能明示其節奏的井間譜是朝鮮音樂邁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藝術歌曲得到了 復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部分古典的樂譜得到了五線譜化。《世宗實錄》、《世祖 實錄》中的樂譜雖然沒有完全被翻譯出來,但基于原來古譜的基礎,通過各種手段被大 量地譯成現代譜并付諸演奏,實現了音響化。其中,國立國樂院的“朝鮮傳統音樂出版 委員會”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說的古樂集——Anthology of KoreanTraditional Music(《朝鮮傳統音樂選集》),對了解和研究朝鮮傳統音樂具有重大意 義。玄琴及其奏法譜與現存的口授傳承樂譜所作的比較研究,以及古譜的復原研究也比 較深入。李惠求、張師勛等學者的著作對于平調、界面調等的音樂理論中經常使用的調 子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從整個考古資料來看,朝鮮與中國和日本相比,文獻與文物量雖 不多,但對于中國的雅樂以及雅樂樂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別是現在韓國留下的十分珍 貴的資料,更不容忽視。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時編撰的《六國史》(成書于720—901)為編年 體,包括《日本書紀》30卷、《續日本紀》40卷、《日本后紀》40卷、《續日本后紀》 20卷、《文德實錄》10卷、《三代實錄》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時期宮廷 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編年體例撰寫,沒有分類的“樂志”部分,關于音樂的記事一 般都散見于各個不同的章節。10世紀以后至11、12世紀出現一些實錄、日記、隨筆等, 像《御堂關白記》、《中佑記》、《小佑記》、《九歷》等都是這一時期十分重要的古 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國及朝鮮等亞洲大陸傳入的雅樂(實際上是中國的宮廷 燕樂為主體),并得到了傳承與發展。延歷十四年(795)出現了模仿中國的踏歌,9世紀 初又出現日本創作的器樂合奏曲《鳥向樂》等作品,至9世紀中葉不僅誕生了許多雅樂 的演奏名手,而且還創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樂曲《西王樂》、《長生樂》、《夏引樂》 和《夏草韋》等(注:見吉川英史《日本音樂的歷史》,創元社,1965年,72頁。)。13 世紀以后出現了關于雅樂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訓抄》(@④近真,10卷10冊,1233 )、《續教訓抄》(@④朝葛,1270—1322)、《體源抄》(1511年,豐原統秋,13卷20冊) 、《樂家錄》(安倍季尚,1690,50卷)等。關于能樂的文獻有《世阿彌十六部集》,還 有聲明理論書,箏曲、三味線等相關的理論書籍,它們構成了研究日本音樂的主要史料 。上世紀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國文學界對能文獻的解釋,由聲明學僧侶對聲明的研究, 聲明、能樂等的許多文獻史籍作為音樂史料也越發引起重視,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樂譜中有雅樂的樂器譜、聲樂譜,能的謠本與吟唱的手付本,平曲 的節付本,聲明的博士譜,箏組歌與三味線組歌的文字譜,尺八的文字譜等。這些寫本 與少數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傳了下來。作為考古資料,以正倉院的樂器為首(共1 8種75件),其中有很多古樂器得到了傳承。其次有關音樂的資料還能從日本大量的繪畫 、雕刻等美術作品中尋找其淵源。因此就古代的音樂史料而言,現存日本的古代資料無 論是質還是量都能與中國的史料相媲美。
(五)東南亞
在東南亞由于缺乏一般史書記載,現在傳承的音樂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紀前后。要了 解古代的音樂狀況大部分還必須依靠中國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東夷傳、南蠻傳等)。這 一地區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是越南。關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書 ;《大越史記全書》上中下,1479—18世紀末(編年體);《大南會典事例》(1855年)禮 部69—135卷有音樂的內容;《大南實錄》20卷,1844—1909年成書;《歷朝類志 》,1821年著;《雨中隨筆》19世紀前半葉。樂譜受中國影響很大,主要使用中國傳入 的俗字譜、工尺譜以及哼唱的打擊樂譜。考古資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吳哥遺址(9—15世紀 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遺址(建于公元800年夏連特王朝時期),以 及爪哇教時代的雕刻普蘭巴南(Prambanan)遺址(建于9—10世紀的建筑群遺址)等都是東 南亞地區的重要文化遺跡。
(六)印度
與中國等東亞國家相比,印度對音樂史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15世紀以后出現了較多 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論家的傳記、逸話等,還有一些口頭傳說的記載。在伊斯蘭文化 圈以及亞洲的音樂史中,最為注目的是眾多的理論書籍。其中現存最古老的是2—5世紀 成書的《戲劇論》(婆羅達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論述音列、音階、調式、斯魯 提<shruti>、音律),該書以舞蹈、戲劇為主,音樂也占據了相當的篇幅,其中對二十 二音律、七聲音階以及音組織等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還涉及了樂器維納琴(Vina,弦樂 器)等的演奏法。
繼婆羅達之后的音樂理論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職于 宮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樂藝淵海》是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著作。該書共七卷,分 別對樂律、調式、曲體、作曲、歌唱法、節拍與節奏、樂器與演奏、舞蹈與表演等展開 論述,是繼《戲劇論》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樂論著。
其后還有一些斷斷續續的理論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論著述則是在13世紀以后再度出 現的,這是由于伊斯蘭教進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漸走向伊斯蘭化。毫無疑問,伊斯蘭音樂的科學性對印度產生了極大的刺激。從這一時期開始,稱之為印度音樂的靈魂——拉格(Raga)理論才漸漸地發展起來。
由于宗教的關系,在印度的音樂考古資料中,古代的美術(主要是雕刻和壁畫等)與伊 斯蘭時代以后的細密畫占據了較大的比例。
(七)西亞
西亞的音樂文獻大致是從7世紀進入伊斯蘭時代后才有記錄的。關于這以前的阿拉伯音 樂以及3世紀到7世紀的薩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樂,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從伊斯蘭 文獻中得到推測。波斯的音樂資料不太多,作為考古資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遺址留下的一 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豎琴、小號、琵琶類四弦樂器(Barbat)、鼓等樂器形象。 7世紀以后西亞逐漸進入伊斯蘭時代,史籍中關于音樂生活的記錄、數量甚多的理論書 、細密畫為這一地區的重要史料。
二、歷史研究狀況
從20世紀初葉開始,歐美一些音樂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以作品樣式為主要對象的研 究逐漸轉向以“音樂活動”整體為研究對象。而音樂史學的研究則是以音樂學與歷史學 交叉融合的一個學科,因此,如果音樂史限于“歷史”這一個層面來理解的話,那么音 樂史的敘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獻與考古資料)的基礎上構成的。而史實是建立在對史料的 收集、批判、分析與綜合等的梳理基礎之上。在這個過程中,把握各個不同時代、不同 地域音樂的題材、樣式等的歷史流動,從宏觀與微觀的不同層面來洞察和分析音樂在各 個歷史時期的流動狀態,把握這種歷史流動的方式無疑是多樣的。這種認識可以是以音 樂的題材、樣式為主體,也可以從美學意識、社會現象等方面來窺察音樂的實質,揭示 歷史的文化現象。
關于音樂史的著述,除通史外還包括斷代史、音樂體裁史、樂種史等。史學著作有本 國人寫的,也有他國人寫的。對于歷史時代的劃分也有各自的見解。體例也不一,種類 、樣式上非常多樣。以下從音樂的世界史與國別史兩個方面來舉一些例子。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世界音樂通史上的話,C.薩克斯(Curt Sachs,1881—1959)撰寫 的《樂器的歷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New York,1940)是值得一提 的,他把世界樂器的歷史分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東、西方歷史發展的線索進 行平行敘述。這可以說是世界上首次出現的以樂器為主體線索撰寫的世界音樂通史。其 后是德國學者W.維奧拉(Walter 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樂史的四個時代 》(Die vier Weltalter der 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將東西方音樂現象融為一體進 行橫跨面平行敘述的世界音樂史專著。
這一時期作為一般史的世界音樂史的體系與研究方法還處于摸索階段,因此,如何撰 寫世界音樂史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筆者認為,在將視線投入世界音樂史的撰寫以前, 首先必須科學地完善東方音樂史的學科體系。田邊尚雄1930年的《東洋音樂史》,岸邊 成雄1948年的《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是其嘗試。但是,兩者在世界史和東方(亞洲)史 的體系上觀照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其實歐洲音樂史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這里民族文化 的一體化現象,東方要比歐洲復雜得多,作為一個文化圈要形成體系是很困難的。無論 是東方音樂史還是西方其他地區音樂史都難以完整地敘述各民族與國家從古代到現代的 完整的音樂歷史。在對世界音樂史的嘗試中,有奧地利音樂學家安布魯斯(AugustWilhelm Ambros)的《音樂史》(Geschichte der 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個人 約在19世紀下半葉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樂家傳記及一般的音樂書志學》 (1835—1844)的音樂史那樣,將東方音樂與古代歐洲音樂以橫向的歷史線索進行平行論 述的專著。C.薩克斯《樂器的歷史》和他的《音樂的起源》(The Rise of Music inthe Ancient World:East and West,New York,1943)其時代觀顯得比較暖昧。田邊尚雄 的《東洋音樂史》是以“中亞音樂的擴散”、“西亞音樂的東流”、“回教及蒙古勃興 的影響”、“國民音樂的確立”、“歐洲音樂的侵入與東洋音樂的世界化”五個章節分 別進行論述的。岸邊成雄的《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也同樣把東方音樂史以“古代前期 固有的音樂時代”、“古代后期國際音樂時代”、“中世紀民族音樂時代”、“近現代 世界音樂時代”的四個時期來論述。上述的田邊與岸邊的著作都以亞洲為地域整體來敘 說,但時代的劃分以及某些歷史觀上有些分歧,不過像這樣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幾乎很少 。W.維奧拉《世界音樂史的四個時代》設定為“史前與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東 方音樂”、“西洋音樂的特殊地位”、“技術世界產業文化的時代”四個時期,其中在 東方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紀與近代的斷代劃分上很不明確,這里存在著較 明顯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敘述世界音樂史中,較重要的是對歷史發展的評價。比方說中國的京劇、日本的能 、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亞的甘美蘭等,這些音樂體裁、樣式在世界音樂史中應該置于 什么樣的地位?像這樣的比較與評價如何避免主觀意識來建立起音樂史觀是十分艱難的 。僅僅展示一張詳細的年表是不能成為史學的研究成果。以客觀史實、全面橫向類比的 評價來建立起音樂史各時期的發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對音樂的歷史評價,體裁樣式史 與社會史不能分離敘述,因為音樂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及環境文化中產生的。
地域、國別的音樂通史是分別以民族、地域及歷史斷代、體裁分類來敘述的。除西方 音樂史以外,中國、日本和朝鮮在國別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 —1867)末期就已經出現了對江戶時期的音樂進行總體記述,尤其是特定種類的歌曲和 凈琉璃(一種說唱音樂)的專門論述著作——《聲曲類篡》(注:《聲曲類篡補遺》、《 聲曲類篡增補》都被收入《巖波文庫》,1941年。)(齋藤月岑,1847)。該著作以凈琉 璃為中心,收集了江戶時代的律調、詞章,演奏者的傳記、曲目、年表等。在這一領域 內,它的資料詳細,分析透徹,很具權威性。到了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日本音樂史中最 初的通史專著——《歌舞音樂略史》(注:《歌舞音樂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 常清佐校訂《巖波文庫》1928年版。)(上下兩冊)是一部編年體著作,但其整體以詳實 的資料為基礎,其歷史的真實性受到高度評價,是一本對雅樂制度進行論述的最早專著 。1932年田邊尚雄的《日本音樂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樂的歷史》等可稱為 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邊尚雄的《日本音樂史》是一部從文化史的角度,攝取民族 學的方法論進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為歷史學的方法論略顯陳舊。而吉川英史的《日本 音樂的歷史》則是總結、歸納了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提煉出歷史事實并以時代的順序 所完成的一部簡練明了、忠實于史實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沒有用樂譜來闡述音樂現 象和理論問題,留下了一些遺憾。
中國現代出版的音樂通史大多出現在民國之后,均采用編年體的敘述方式。整體上來 看大致有1929年鄭覲文的《中國音樂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1935年朱 謙之的《音樂的文學小史》、1953年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紀 的80年代以后出現了大批的中國音樂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樂史方面,雖然其中不乏有 獨到見解之作,但是在一個國家中出現了如此之多大同小異的音樂史學專著,這種現象 在其他國家中是少見的。關于中國音樂史還必須提到的是法國的東方音樂學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寫的《中國音樂史論》(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編撰的《音樂百科辭典》(第一部、第一卷),該 書比較詳細客觀地論述了中國音樂的發展狀況,同時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國音樂通史。
關于朝鮮音樂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有了飛速的發展。1964年由李惠求、張 師勛、成慶麟共著的《國樂史》,1967年李惠求的《韓國音樂序說》,從體例到形式都 非常完整,歷史考證也深入細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證、文獻的解釋及李朝以 來的樂譜分析等,在各領域多層面進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關韓國音樂史學的研究, 近年來除了本國外,歐美學者對其進行的研究,尤其是對唐宋以來中國流入朝鮮的宮廷 音樂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較強的勢力(注:參見宮宏宇《韓國及歐美學者對流傳在韓國 的古代中國音樂的研究》,《中國音樂學》2002年第3期。)。
東南亞和印度的通史還沒有完全形成系統。有關越南的傳統音樂,陳文溪于1962年在 巴黎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越南傳統音樂》(注:La Musique 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樂的歷史、傳統器樂、樂律樂調、宮廷樂種 、儀式音樂等的理論專著。關于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和巴厘的音樂可參閱麥克非(McPhee) 的著作。但是這些都是概論性的著作,作為通史還缺乏一定的文獻史料上的梳理和積累 。印度本國人寫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樂史》(HistoricalDevelopment of Indian Music,1960),以及《印度音樂的歷史研究》(A HistoricalStudy of Indian Music,1965)。此外,同時代的還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樂史 》(History of Indian Music,1960)。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實性以及音樂史現象 的解析、演繹上都還沒有真正達到深入、詳盡的研究地步,作為通史來說還只是一個初 級階段。古代印度音樂以史學的角度來考證的有邦達喀爾勞(Rao Bhandarkar)、考馬拉 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等以各種不同體裁、樣式等進行的出色研究,因此產生 一些優秀的綜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較關心和注重音樂的演奏,而 對歷史的研究重視不夠。在研究印度音樂史中歐美人對印度關心的人很多,但作為歷史 性考察的著作卻不多見,1941年法國學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樂器》(LesInstruments de Musique de I’gnde 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較突出的著作。
關于西亞的音樂史學,很少見到由本國人撰寫的,幾乎成了歐美人獨占的天地。很多 理論書的原始史料被運往歐洲,成為歐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礎。1842年凱薩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樂》(Die Musik der Araber,Leipzig)為起端,很多學者 對伊斯蘭教音樂開始進行歷史性的考察。關于阿拉伯音樂史的研究必須提到的人物是英 國學者H.G.伐瑪(Henry Geory 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樂通史——《13世 紀前阿拉伯音樂的歷史》(A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 to the 13 Century)是一本以 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等的文獻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專著,時間上一直寫到阿拉 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紀)滅亡為止的一段音樂歷史,該著作出版后幾 乎半個世紀一直成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權威性阿拉伯音樂史的專著。翌年, 他的一本題為《受阿拉伯音樂影響的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 for the ArabianMusical 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實的事例證實了西方音樂中受 阿拉伯音樂影響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證實阿拉伯音樂通過伊比利亞半島進入歐洲的 歷史事實。接著,他的一本《阿拉伯音樂的史料》(The Sources of Arabian Music,1 940年,1965年修訂版)是對8—17世紀阿拉伯音樂的理論、演奏以及歷史相關的原始史 料進行論述的解說集,對理解早期阿拉伯音樂是極其重要的研究手冊。關于阿拉伯音樂 ,這里還要提及的是黛嵐捷R.D’Erlanger編撰的巨著《阿拉伯音樂》(La 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編撰,全六冊),這是一套歷時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 第二卷上半部分為阿爾·法拉比的《音樂的大著》法譯本,第三卷是薩菲·阿迪恩的《 旋律的寫法》全譯,第四卷為奧斯曼帝國時期獻給穆罕穆德二世的《音樂通論》,第五 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樂的理論與實踐相關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階、旋法和一些文獻 ,第六卷為阿拉伯音樂的節奏組織與曲式分析。全書還包含著許多五線譜的譜例。該書 是一部十分系統又全面論述阿拉伯音樂史的重要著作。
關于阿拉伯音樂的研究,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德國、法國都有過一些深入的研究 ,如1970年出版蘇普勒(Spuler)編撰的《東方學手冊》(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c) 的第一部別卷4《東方音樂》(Orientalische Musik)所輯錄的論著《阿拉伯—伊斯蘭文 化圈的音樂》(Die Musik des Arabisch—islamischen Bereichs),是對20世紀70年代 以前有關阿拉伯音樂研究的歷史總括。對阿拉伯音樂技術理論的研究還有賴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樂的調式與體系》(The Modal System of Arab andPersian Music,1978年)等(注:參見《音樂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 5頁。)。伊斯蘭音樂在東方的研究較早的有日本的學者飯田忠純1936年的《中世紀阿拉 伯人的音樂觀》(注:日本《東洋音樂研究》第一集,1936年。)。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是 岸邊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樂的西流》(東京《音樂之友社》),1983年被譯成中文, 改名為《伊斯蘭音樂》(上海文藝出版社,郎櫻譯),這是一本八萬字左右的小冊子,但 它卻對我們了解伊斯蘭音樂幾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專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論著簡 明扼要地闡述了伊斯蘭音樂的形成、發展的過程,以比較音樂學的研究方法論述了阿拉 伯音樂與希臘、波斯及印度音樂間的關系,并進一步以實例闡述了伊斯蘭音樂對歐洲和 東方的影響,對前人的研究總結也十分客觀翔實,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蘭音樂專 著。
另外,亞洲地區尚有許多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區,原因是文獻資料的缺乏,研究者 一般只能從民族學、民俗學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確地把握亞洲古代音樂歷史狀 況還存在一定的困難。
以上主要對亞洲地區的音樂史料及音樂研究狀況,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個歸納和綜 述,限于自己的外語水平及有限的資料只能做一個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國的音樂文化與 亞洲各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互動關系,相互間的交叉、滲透都交織著千絲萬縷的文化流 動關系,因此筆者在執筆此文時的一個主導思考是:我們在研究中國音樂史的時候不能 忽視關注周邊地區相互間的文化滲透和交叉現象,對周邊地區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對 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坊去方換育
@②原字湯去氵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