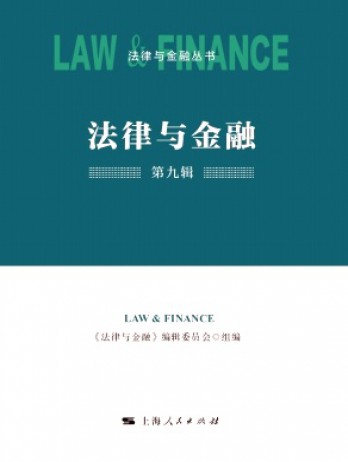對法理學的看法精品(七篇)
時間:2024-02-24 15:23:36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對法理學的看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隨著我國法制化進程的加快,法律在社會中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因而,我國法學教育的質量也受到了多方面的關注。其中法理學在法學課程設置中的位置就是其中爭議聲音比較大的一部分,之前大多數人關心的都是開設法理學課程對學生法學知識學習的意義上了,很少有人關注法理學在課程設置中的位置,但是,本文主要是對位置方面內容的研究。
一、從法理學的研究對象上看法理學位置
我們要從分析法理學的研究對象來看法理學是否適合放在大一的法學課程中。“法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法律現象的共同規律和共同性問題”,但是,目前對其中的“共同規律”“共同性”的解釋還是眾說紛紜的,這就導致了法理學外延不清晰,也出現了法理學定位不準確的現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法理學呢?這就要追溯到它的前身法哲學,在西方的法學著作中層提到過法哲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是定義與分析問題,其二是法律推論問題,其三是法律批判問題。要想學好法理學知識就必須要進行這三方收集整理面的研究,但是,這些知識對于法學基礎非常薄弱的大一新生來說無疑會存在理解上的難度,無論是法律推論問題還是法律批判問題,都要求其實施者要具有一定的法律思維和法律知識,但是,這種思維和知識是需要長時間積累的。對于法學初學者來說,要他們掌握法律中的基本概念都是需要時間去消化理解的,更別說要學生具有法律思維和法律知識了。正因為分析所需要的前提條件不存在或者匱乏,就導致學生在學習法理學知識時多是死記硬背,而且學到的知識比較單一,都是一家之言,學生自身理解力上的收獲比較少,因此,從這方面來看將法理學的學習放在大一是不太合適的。
二、從學習法理學的目的上分析法理學位置
目前,“在大一設置法理學課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在理論上掌握一些法理學的基本知識,為學習部門法做一個良好的鋪墊。”是很多人眼里學習法理學的目的,正因如此,目前很多的高效在進行法學課程設置時都將法理學放在了大一,但是我們并不能完全的肯定這種觀點。首先我們要明確什么是理論,理論就是“通過對特定事物的大量觀察、經驗和陳述進行系統地收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般性的命題,人們就把它稱之為理論。”但是,由于觀察對象的流動性和復雜性以及觀察主體的主觀性,這也導致了理論的不周延性和主觀性,法學理論也是如此,這也導致了法理學這個概念本身就是要經過思維、觀察以及驗證的一個主觀認識。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是以法學理論為基礎的,在我國,法理學對法律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反思功能。首先,在法治社會建設中法學理論的反思功能。我國法律制度的復雜性是隨著法治進程而變化的,因為,法律是要對社會中重要的利益沖突和生活現象進行調整的,如果社會基礎復雜,那么就需要一種復雜的法律制度來調整。隨著我國法治社會發展程度的加深,對法律制度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是,精密的法律制度并不是一朝完成的,它需要一個不斷自我改正的過程,因此,就需要法理學對舊解決方案的存在基礎進行不斷地反思。其次,在社會轉型中法學理論的反思功能。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社會結構轉型,而社會結構轉型也必然會帶來社會領域中各種新生的利益沖突,這是就需要法律對這些沖突進行調整,但是由于社會結構不斷的變動,法律調整也是需要不斷進行改變的,但是到底該如何的改變就是需要法理學進行反思了。最后,在價值觀念改變中法理學的反思功能。生活關系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而生活關系的變化又會給人們尊崇了上千年的價值觀念受到嚴重挑戰,而且這種價值觀念會逐漸的被新生的價值觀念所代替,正如前人總結出來的“法律共同體中的價值觀的內容和活力則比有關法律提高問的變化更加迅速”,因此,也就導致了現有的法律規范與公民普遍的價值觀念之間總是出現脫節的現象,那么,此時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比如,是否需要調整國家法律制度來適應公民價值觀念的變化、怎樣調整才能夠適應公民價值觀念的變化、什么時候調整、調整的頻率等都是需要法理學理性反思來輔助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的。
通過對以上內容的論述,我們不難總結出,法理學的重要性主要還是取決于學習者的主觀態度,法理學知識學習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為了學習部門法做準備。其實,為學習部門法知識做準備并不是光靠學習法理學知識就能夠實現的,因為,法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其內容已經不再涵蓋部門法知識的介紹了。而我們現代人學習法理學知識的真正意義是培養法學知識學習者的反思思維以及反思意識,這是需要相關部門法作為基礎的,所以說把法理學課程安排在大一第一學期還是存在著一定的不合理之處的,應該在了解了部門法之后再進行法理學知識的深入學習。
三、結束語
篇(2)
關鍵詞:法律理論;法律的本質;概念分析
中圖分類號:D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2)02-0079-10
在從事法律理論或法哲學工作之前,首要的任務便是澄清圍繞在法律理論四周的種種誤解并厘定恰當的研究方法。這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對法律理論本身進行認真反思,來探究如何才算得上是一種成功的法理論。否則,我們的結論無論看似多么合理,都將建立在極其不穩固的基礎之上,隨時都會坍塌。近十多年來,當代法理學對法律理論之方法和性質的集中討論已經逐漸成為理論關注的一個焦點,“法律理論家已經開始——人們今天或許會認為有些遲了——嚴肅地揭示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和他們提出的主張之性質” 。①這個理論發展趨勢無疑也迫使我們有必要加入到這場方法論層面的論辯中。
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這里需要表明,本文所指的法律理論是在分析法理學的語境下使用的。因此,在文章一開始有必要對分析法理學作一個初步界定,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予以說明:一方面,分析法理學所使用的方法被廣泛地稱為“概念分析”;另一方面,分析法理學作為一種法律理論,其目標是提供一種對法律本質的說明。綜合而言,分析法理學作為一種法律理論是要通過概念分析的方法來提供一種對法律本質的說明。這就表達了一個方法論的基本論題,即法律的概念分析就是對法律之本質的探究。不過對這樣一個粗略的看法,我們顯然還是會存在不少疑問——概念分析等同于語義分析嗎?如何正確理解法律的本質問題?一種對法律本質的說明能夠是價值無涉的嗎?分析法理學如何是普遍的?對上面四個問題的嘗試性回答將構成本文的主要內容。
一、概念分析和語義分析
我們不妨先從對“概念分析不是什么”這個消極論題入手。值得注意的是,探究事物的本質和探究語詞的意義之間的區別經常在法哲學家那里遺失了。這里想要著重表明的就是,概念分析絕不能等同于語義分析,法律理論試圖說明的是法律的本質屬性而不是任何語詞的意義。
語義分析這種方法最系統地體現在奧斯丁的《法理學的范圍》中。對奧斯丁來說,其所面對的壓倒性問題是“law”這個語詞在復雜多樣的非法律語境中的使用,例如自然法、萬民法、國家法、禮儀法、尊嚴法等等。奧斯丁無法容忍這種語詞混亂的狀況,他試圖通過考察“law”的準確用法和非準確用法的界限來精確地界定“法律”這個語詞的意義。因此,限定法理學范圍這項任務,指的就是“清理這門科學中語言修辭活動滋養的病灶”。②
然而,描述“law”這個詞在所有情形下的使用對法哲學家來說有什么意義呢?這樣的理論進路無異于使法哲學變成了詞典編纂學。奧斯丁當然不想使其法理學事業淪為詞典編纂的工作,他也想提供一種對法律本質的哲學說明。因此,對奧斯丁來說,這種語義分析的必要性建立在一個基本預設的基礎之上,即對“law”的其他多種使用方式是基于“法律”這個語詞的類比式修辭活動,其寄生于準確意義上的“法律”語詞之中。因此,通過語義分析所剝離出的“法律”之核心意思就成為法哲學家理論探究的中心。
不幸的是,奧斯丁的這一理論預設是錯誤的。拉茲尖銳地指出,且不論奧斯丁法律命令理論本身之缺陷,奧斯丁對法律分析的失敗在于如下雙重錯誤:“第一,沒有理由把關于純粹理論法則(theoretical laws)的話語(例如自然法則)視為關于純粹實踐法則(practical laws)話語(例如法律規則)的寄生性拓展;第二,當考量純粹實踐法則的時候,似乎沒有理由給予法律規則及其具體特征相較于道德法則的優先性地位。”③
我們或許不應提及奧斯丁這種笨拙的語義分析方法,而來重點關注現代語言哲學。在這方面,哈特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把20世紀中期的語言哲學應用到法哲學領域的卓越范本。哈特受到了其同時代語言哲學家奧斯汀(J.L.Austin)言說活動(speech acts)理論的極大影響,他相信運用此理論可以幫助解決“法律”、“權利”、“義務”、“公司”等一直困擾法哲學家的法律語詞的本體論問題。哈特從奧斯汀對“施事話語”與“敘事話語”的區分中得到了很多啟示。他認為,語言的施事效用不同于我們通過或真或假的陳述去描述世界時對語言的使用;而離開了語言的施事效用這一觀念,就無法理解法律現象的一般特征。
然而,哈特所受到的以奧斯汀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學派之影響主要限于其學術生涯的早期。④拉茲指出,在《法律的概念》這部成熟作品里,哈特對語言哲學的很多期待都消散了。⑤就《法律的概念》來說,哈特從言說活動理論那里獲得的最為重要的教益是對基于內在觀點的法律陳述之理解。具體來說,哈特的這個思想主要受到斯蒂文森(P·F·Stevenson)和黑爾(R·M·Hare)對道德話語之語言分析的影響。斯蒂文森和黑爾在分析語言哲學框架內提出的倫理學理論分別被稱為情感主義和規定主義,而哈特的基于內在觀點的法律陳述正是應用了此種理論。
這里不是具體討論哈特內在觀點理論的地方,讓我們回到概念分析與語義分析(乃至更廣義的語言哲學)的關系上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主要觀點是,無論是奧斯丁式的語義分析還是哈特式的現代語義分析,都不能等同于對法律的概念分析。因為,對法律這個“語詞”的使用及其意義的分析對于我們理解法律的本質幾乎沒有什么實質的意義。用拉茲的話來說,“大體上,只要一個人在對法律本質及其核心制度的思考中沒有錯誤的使用語言,那語言哲學對促進其理解所能做的就微乎其微。”⑥
不過,不難設想這樣一種反駁意見,即畢竟哈特對內在觀點及法律內在陳述的闡發是他對現代法理學作出的最具標志性的貢獻,不管哈特的觀點是否正確,他都是在積極運用語言哲學的成果。而且,在《法律的概念》之“前言”部分,哈特明確地把“深化對語詞的認識,來加深我們對現象的認識”作為他的方法論綱領。哈特還說到,“在許多地方,我提出了可說是關于語詞意義的問題。我考慮了被強制與負義務如何區別;一項有效的法律規則與對于官員行為的預測有何區別;說一個社會團體遵守一項規則意味著什么,這與聲稱該團體之成員習慣性地做某些事有何不同和相似處。”⑦
這個反駁意見并非沒有合理之處。我們必須承認哈特的理論確實依賴于日常語言學派的語言分析工具,但是我們更要清楚:哈特只是把這種方法作為一個工具來比較與法律相類似的制度和實踐,從而使得我們充分理解法律本身的獨特屬性。因此,語義分析只是從事概念分析工具的一個技術策略,不能把它等同于對法律本質的探究。法律的概念分析可以包括語義分析這種技術策略,也可以包括其他的技術策略。語義分析只是一個概念分析的下位范疇。
概念分析真正關注的不是語詞本身而是言說背后的制度和實踐。哈特之所以在從事概念分析這一事業,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使用了語言哲學的方法,而在于他是在進行關于法律本質的探究。這就是說,一個不采用語言哲學方法的法哲學家也有可能是在從事分析法理學的事業。所以,下面讓我們回到“法律的概念分析就是對法律之本質的探究”這個方法論的基本論題上來。
二、概念分析和法律的本質
作為分析法理學的經典之作,《法律的概念》這個書名可能會給我們以這樣的印象,哈特所要分析的對象是概念。但是,這個看法是誤導性的。如果把概念誤認為是分析的對象,我們就將處于危險之中,就像把指向月亮的手指誤認為是月亮本身一樣。因此,《法律的概念》的真正分析對象其實是落在概念之下的實在,法律的概念分析是對法律這一社會實在的本質之分析。
把握事物的本質顯然是一項比正確使用其概念更為困難的事情。當我們有一個概念的時候,很可能并沒有對其本質的透徹知識,換言之,具有一個概念相容于對其本質特征的粗淺或有缺陷的理解。因此,一種哲學解釋的目的就在于提高人們對概念背后的世界的理解;法哲學的目的就是促進人們對法律之本質的理解。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法律之本質”的問題呢?當對法律本質加以探究時,我們究竟想知道些什么?結合一些重要法哲學家的討論,筆者試圖通過以下相關方面的鋪陳,來漸次推進和深化我們對法律本質問題的理解。
第一, 法律的本質指的是法律的必然屬性。
拉茲明確指出,一個法律理論的成功要滿足兩個標準:“首先,它由其為必然真的有關法律的命題組成;其次,這些命題解釋了法律是什么。”⑧可見,法律的本質問題指向法律所必然擁有的屬性,這也構成了分析法理學對“法律是什么”這一根本法哲學問題的處理方式。要注意的是,對“必然性”的強調表明概念分析是一種哲學工作而不是經驗研究,雖然概念分析與經驗觀察有一定關聯,但從根本上說這是兩種不同的理論方法。“一些擁有房間那么大的計算機和巨額預算的社會學家,通過分析像珠穆朗瑪峰那么龐大的數據,可能不是希望去發現法律的本質或性質,而僅僅是希望在一大堆故事中發現模式或反復出現的東西”。⑨
在更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還要排除這個看法,即法律之必然屬性等同于“自然種類”理論中討論的必然性類型。以米歇爾·摩爾(Michael Moore)和尼克斯·斯塔羅普洛斯(Nicos Stavropoulos)等為代表的學者在法律理論領域引入自然種類的概念分析方法。“自然種類”理論來源于克里普克—普特南的語義指稱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意義和指稱是由世界本來的方式決定的,不是由我們的信念決定的。自然種類理論認為,一個自然種類的語詞指稱一類對象,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這一類對象具有獨立于人類心靈的本質。例如,“黃金”作為一個自然種類的語詞,無論何時,其本質屬性都是“原子序數為79 的物質”。
然而,把對自然種類的分析卷入法哲學領域是令人懷疑的,因為這完全忽略了自然世界和人造世界的基本區分。法律不是自然種類,我們不能否認法律如同其他社會實在一樣都是意向性人類行動和實踐的產物。因此,自然種類理論不可能解決法律之本質這個屬于完全不同領域的問題。比克斯(Brain Bix)就此告誡我們,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觀點試圖說服我們的是,“我們實際使用語言的方式植根于我們的實踐和意愿并且足以滿足我們的需要” 。⑩
第二,法律的本質指示一種特定制度性實踐的本質。
探究法律之本質意在對“法律是什么”這個問題提供一種哲學說明。但是,如沃爾德倫(Jeremy Waldron)所說,“法律是什么”這個短句是模糊不清的,它可能意味著是對法律這個制度是什么的總體說明(wholesale account);或者可能意味著是對具體法律是什么的細節說明(retail account)。B11不可否認,法律理論會對確認具體法律是什么感興趣,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更主要的是通過援引這一制度具有的本質屬性來建立一種制度的類型。例如,我們常常認為,法律通常聲稱有權利使用強力來實施它的規則。在這個例子中,法律沒有指涉具體的法律規范,而毋寧是指涉一個創造、適用和實施這些規范的制度或組織。按照這個設想,我們似乎可以說,法律體系具有被設計用來獲得某種政治目標的獨特制度性結構。
在這個問題上,哈特的《法律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分析范例:以承認規則為代表的第二性規則的出現彌補了前法律社會之規則的缺陷,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類型;最小自然法的內容則表明了這一新的制度類型所針對的社會和政治之特定需求。拉茲的立場無疑更為鮮明,在他看來,法律理論試圖對法律之本質屬性的說明就是在探究一種社會制度的類型學(typology)。B12拉茲更是把這種解題思路稱為對法律本質加以探究的制度性進路(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B13他贊成制度性進路而貶抑基于“法律人視角”的研究進路。拉茲強調,我們并非要完全不顧法律人視角,但是這種關注必須置入到社會的背景下,即從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的更寬廣視角來檢討法律人和法庭的定位。
第三,對法律本質探究的根本目標是詮釋屬于我們自己的法律概念。
當我們把法律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制度來加以研究時,這種分類學的理論方法不免會被認為是某些抽象的理論考量決定了對社會制度的歸類,這些理論考量可能包括理論的豐富性和一致性,理論表達的簡約、理論的預測性力量等等。因此,理論的解釋力量在于這個理論本身是否符合上述的元理論標準。哈特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這個看法,在《法律的概念》里,他指出:“如果我們要在這些概念之間作個理性的選擇,那應該是因為其中某個概念有助于我們的理論探究、促進或澄清我們的道德推理,或兩者皆是。”B14
這句引文似乎部分地承認,一個概念或類型的形成是為了促進理論研究或其結果的表達之目的而被學術團體引介進來的。然而,此看法是根本錯誤的。盡管在一般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可能沒有人否認那會是一種極佳的概念之形成方式。但是,法律理論并不追求純粹的理論智識價值。拉茲指出,“法律的概念作為對一種社會制度的類型之標示,其并非是任何學術性學科之科學工具的一部分”。B15這就是說,法律的概念并不是一個被學術界引介進來幫助解釋法律這種社會現象的概念,相反,法律的概念是一個扎根于我們社會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概念,是我們的文化以及傳統的一部分。它是一個在我們社會中的共同概念,而不是對任何具體學科的維護。質言之,法律的概念從根本上反映了我們對法律制度的自我意識或自我理解。概念分析不創造理論,而只是詮釋我們自己的概念。
因此,當我們探究法律之本質時,“自我理解”就構成了我們所研究的根本內容。不過,由拉茲所主要闡發的這個“自我理解”論題卻遭到了來自德沃金的質疑,德沃金不無諷刺地說:“如果我們想研究我們自己的意識,那么轉向小說、政治學、生物學、精神分析學和社會科學,我們會做得更好。”B16面對德沃金的這個質疑,這里有必要對“自我理解”論題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可以注意到,在新近出版的《權威與解釋之間》這本著作的“序言”里,拉茲再次強調,“法律理論的一個特征是它們處理活動、態度、制度以及相關現象,后者本身由一些盡管并不完美的自我理解所告知。”B17拉茲的這個主張實際上意味著,這些“不完美的自我理解”作為一種常識或顯明之理(truisms)是法律理論的分析質料,揭示法律本質的過程就是一種對有關法律之常識的理性重構。換言之,法律的概念分析之關鍵是對我們所擁有的相關常識之收集和反思。這里,不妨以第24屆IVR大會上拉茲所作的“世界秩序中的個體權利”之主題發言為例。在對“權利”的這個杰出分析中,拉茲所做的首要工作就是細致地列出了如下若干有關權利的常識:“1)擁有權利意味著擁有對權利主體而言具有價值之物;2)擁有權利本身對于權利主體是有價值的,權利構成了課予他人以義務的根據;3)他人對權利主體負有不得侵犯或妨礙其權利之享有或實現的義務;4)權利主體可依其選擇免除或終止此義務。”B18無疑,這四點都是我們對“權利”概念的重要常識。
當然,列出有關法律的常識并不意味著其就構成了對法律本質的認知。這些常識只是被作為暫時的固定點而隨時可以被修正甚或放棄。我們的理論工作雖然始于常識性的判斷,但卻并非終于常識性的理論。如果法律的本質對任何人都非常清楚,那么我們就沒有必要致力于概念分析這項事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概念分析是一種類似羅爾斯意義上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之方法。
總之,就一種成功的法理論而言,我們必須盡可能地提出這類常識,并盡可能地予以說明和反思;相反,如果我們罔顧它們,那么我們的法律理論工作就會出現問題。在這方面,德沃金自己的法律理論并非背道而馳,反而忠實地遵循了此項要求。眾所皆知,為德沃金所關注的“常識”是法庭辯論中的“理論爭議”,由此,德沃金的概念分析重心在于對法律這種“論證性實踐”的理性重構,他說:“我們希望能夠更具有反思性,并且希望提出一個比大多數律師有時間或有意愿去構想的答案更深刻、更具有一般性的答案。”B19
三、法律理論: 評價性vs.描述性
如何判定“法律理論之性質”這個問題必然要把我們帶到法律理論的描述性和評價性之爭的領域。現在立場應該很清楚,當我們主張“對法律本質的探究是要促進我們理解我們自己”這個命題時,已透露出法律理論的詮釋性特點,即法律的概念分析是我們對法律這種制度性實踐的詮釋。因此,法律的概念分析其實是一項詮釋性工作,它具有評價性或證立性的維度。這正如德沃金所言,“法律的諸一般理論其目標在于詮釋法律實踐的主要本旨和結構……”B20值得指出的是,就德沃金和拉茲而言,無論各自在有關法律理論之性質問題上的其他方面存有多大分歧,他們其實都承認自己的理論是詮釋性的,因而也是評價性的。
法律理論的評價性和描述性之爭也可以轉換為法律理論的兩種不同視角之爭,即評價性法理論代表著法律理論的內在視角,而描述性法理論則代表著法律理論的外在視角。在《法律帝國》里,德沃金就明確提出,他所采用的理論出發點是法律實踐參與者的“內在視角”,而不是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的“外在視角”。B21德沃金的這個看法致使哈特在《后記》里,進一步明確主張他自己的法理論是描述性的,而不以任何證立為目標。在哈特看來,法律理論并非一定要納入法體系之參與者的內在觀點中,一種描述性的法理學是完全可能的。“在描述性法理學的計劃中,并沒有任何東西阻止非參與者的外在觀察者,去描述參與者從此種內在觀點看待法律的方式”。B22哈特對“內在觀點”所給出的基本描述和分析就是:“事實上,他們對體系的忠誠可能基于許多不同的考量:長期利益的計算;對他人無私的關懷;不經反省的習慣或傳統的態度;或者只是想要跟著別人走。”B23
哈特的這個進路可以稱為一種外在的概念分析(external conceptual analysis),佩里進一步稱其為方法論實證主義(methodological positivism)。B24方法論實證主義的基本命題就是,法律理論和價值沒有必然關聯。在方法論實證主義看來,如果要展開對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法律之評價,那么在邏輯上就必須首先對現實存在的這種制度進行價值中立的描述和分析。因此,對法律的概念分析嚴格地限定在“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應該是什么”的問題上。這個看法無異于把概念分析與規范性評價分成了兩個先后承繼的獨立階段,從而在實質上把“規范法理學”逐出了“分析法理學”的范圍之外。
然而,我們對法律本質的探尋離不開對法律之于我們之重要性的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必須從法律實踐參與者的視角來作出。把參與者信念納入到描述中并使其可理解盡管并非不可行,但這卻不是以理論家自己的聲音來提出這些信念和態度的。沃爾德倫指出,這里存在一種重要的不對稱:1)法律學者把握有關服從一條規則的內在觀點之角色,與2)法律學者把握有關一個法律體系的本旨或功能的內在觀點之角色。哈特顯然接受了1)而拒絕了2)。但是,沃爾德倫提醒我們,重要的是,不僅法律是規范性的,而且法律的概念也是規范性的,一個人不可能脫離于對一種生活形式的參與而使用或理解這個概念,這種生活形式以不同的方式對政治實踐作了分類。B25
顯然,方法論實證主義違背了這個重要觀點,即我們對法律實踐的詮釋和理解形塑了屬于我們的法律概念。概念的生命在于實踐和生活形式。對“法律是什么”的回答內在地蘊涵著對“法律應該是什么”的價值判斷,這兩者無法斷然分離。一種“阿基米德式”的方法進路是行不通的。B26菲尼斯(John Finnis)早就指出:“現代法理學的發展顯示,并且對任何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之反思證實,除非理論家本身也參與了對什么是對人類真正好的東西以及什么是為實踐合理性所真正需要的東西之評價和理解的工作,否則他不可能對社會事實進行理論描述和分析。”B27要言之,法律理論必須從內在視角出發并且必須通過訴諸道德判斷來加以證立。
對法理論內在視角的辯護促使我們必須深入思考法哲學與政治哲學以及道德哲學的關系。 由于一種基于內在視角的法理論含有規范性的證立維度,其必然會迫使我們把目光投向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領域。在這方面,德沃金是毫不遲疑的堅定行動者;拉茲和菲尼斯則徑直把法哲學看成是實踐哲學的分支。這就是說,法律理論并非一個自足的論域,道德或政治考量在法律的概念分析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我們不需要為此而自尋煩惱,認為這種學科之間的隸屬關系取消了法哲學的獨特地位和貢獻。沃爾德倫就此指出,當法律理論家確認了他們需要回答的重要的非法理學問題時,法律理論有時候可以幫助政治理論建立起有待討論的事項。在這方面,他們可能加強了政治哲學業已從事研究的重要性,或是促成了新的工作,這要求政治哲學聚焦于其所忽視但卻被法律學者洞察到的政治現象之特征。B28
對法律理論內外視角的簡要說明可以幫助我們澄清對分析法理學的兩個普遍誤解:一是把德沃金的詮釋性法理學看作是不同于概念分析的事業;二是把法律實證主義等同于一種外在視角的法理論。這兩個認識都是誤導性的。
第一個誤解的問題已經很清楚,德沃金以及其他自然法理論(例如菲尼斯)仍是在探究法律的本質問題,他們所采取的內在視角與概念分析的工作不僅不矛盾而且相互契合。對德沃金來說,法律理論僅僅在規范性的、詮釋性的意義上是概念的。B29斯蒂芬·佩里一語道破,對概念分析的一種正確理解使其在所有重要方面都等同于德沃金的詮釋主義,雙方不過采用了不同的名稱。B30因而,我們不要陷入“分析法理學”和“詮釋法理學”的語詞稱謂之爭,對法律理論如何命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重要的是清楚“如何才算是一種成功的法律理論”。
第二個誤解更值得我們注意。在《法律帝國》中,德沃金曾把法律實證主義重構為慣例主義,他認為慣例主義法律概念觀的吸引力在于,慣例主義認為之所以過去的政治對當前的權利具有決定性在于“被保護之期待”的理想。B31法律實證主義者當然不同意德沃金對實證主義的這種漫畫式的素描,但這卻顯示了德沃金的一個重要洞見,即德沃金從根本上否定了方法論實證主義與他自己的整全法理論相競爭的資格。質言之,德沃金認為所有的法理論必須是規范性的,法律實證主義也是如此。就我們所關心的這個誤解來說,重要的是,方法論實證主義雖然是一種基于外在視角的法理論,但法律實證主義卻有一個更為豐富的規范性傳統,這就是由霍布斯所開啟的規范實證主義(Normative Legal Positivism)。
規范性實證主義不同于方法論實證主義的理論進路,它是一種基于內在視角的實證主義法理論。以霍布斯為代表的早期實證主義者,對實證主義法律觀念的辯護完全來自于一種規范性的政治立場,他們對法律本質的探究也都伴有對法律實踐之本旨或功能的反思。然而,這個理論典范在奧斯丁那里被中斷了,分析法理學被奧斯丁抽掉了其規范性維度。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十多年來,法哲學家們一直關注法律實證主義如何被重鑄為一種規范性論題。我們在此無法細致地對規范實證主義展開論述。如果要提煉出其基本命題,那么可以說,規范實證主義認同如下這個主張,即如果法律體系的一般運行不要求人們實施道德判斷來確認法律,那么就可以最佳地獲得合法性的價值或者法治。作為一種內在視角的法理論,規范實證主義的傳統以及理論趨向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四、法律理論:普遍性vs.地方性
法律的概念分析就是對法律本質(法律所具有的必然屬性)的探究,因此,概念分析的方法也被稱為一種普遍法理學的方法。現在遇到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理解法律理論的普遍性?顯然,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困難在于概念分析既然是對法律這個屬于我們自己之概念的詮釋或理解,那么就完全有理由把法律理論看作是地方性的,而且也只能是地方性的。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使得法律理論普遍化的唯一路徑似乎就是把不同文化的法律實踐加以抽象化,從而獲得一個共同的抽象基礎來確立法律理論的普遍性。
表面看起來,上述做法似乎是建立普遍法理學的可行方法;但這滿足的毋寧是一種經院式的學究癖好,按照此種方式所得到的法律概念因而是一個瑣碎無意義的空泛觀念,法律的概念分析絕非是從所有的法文化和所有歷史時期里找尋一個相似的法律概念,這種做法無異于把所有地方歷史聯結起來的詞典編纂。抽象固然可以使得理論高度普遍化,但概念的核心意義很可能被完全忽略,從而喪失了真正把握概念的機會。因此,如果要保持對屬于我們自己的法律概念的充分理解,即在保持地方性特色的基礎上推進普遍性,那么普遍法理學的建立就必須另辟蹊徑。在這方面,菲尼斯給我們帶來了非常重要的見解和啟發。
菲尼斯發掘了亞里士多德在有關人類事務的哲學里所討論和使用的焦點意義(focal meaning)之確認的方法。事態的焦點意義被菲尼斯稱為核心情形(central cases)。在菲尼斯看來,普遍化的哲學機制是通過概念所指的事態之核心情形和邊緣情形(peripheral cases)這對范疇展開的。B32事態的核心情形具有概念的豐富性和完整性,而邊緣情形通過與核心情形之間形成的張力有效地納入到了我們對概念所指事態的理解中。例如,商業友愛構成了友愛的邊緣情形,納粹德國則構成了立憲國家的邊緣情形。可以說,菲尼斯所倡導的這種普遍化機制毋寧是通過類推而不是歸納和演繹的方法機制實現的。
一個質疑可能隨之浮上水面。如果普遍化的出發點是我們對自己所處文化中的法律概念之理解,那么,當我們把這個理解類推到其他文化時,我們可能真正理解異域文化嗎?這難道不會是一種文化霸權嗎?筆者認為,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能夠理解其他文化的法律概念,而在于我們不得不借助于自己文化的概念范疇來解釋其他社會的法律制度,這么做并不存在錯誤。正如拉茲所言,“這是理解其他文化的任何智識嘗試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B33
重溫一下哈特與德沃金之爭對于我們恰當理解法律理論的普遍性是有幫助的。在“后記”中,哈特極力強調他與德沃金的法理論設想是完全不同的理論事業,從而否認這兩個法理論之間存在任何重大而有意義的沖突。哈特的理由除了強調他所做的是一種不同于評價性法理學的描述性法理學之外,他還意在表明德沃金的理論是地方性的,其“指向特定的法文化” ,B34即德沃金作為理論家自己所處的英美法的法文化。哈特聲稱自己的理論是普遍性的,他對此作出了特別說明:“這個理論在以下的意義上是一般性的,即它并不關聯于任何特定的法體系或法文化,而是要對法律,作為一種復雜的,包含著以規則來進行規制且在此意義上是規范之面向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作出闡釋和厘清。”B35
哈特和德沃金的理論事業是否形成了如哈特所言的巨大差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我們更細致地辨明哈特所從事的這項理論工作的性質。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在《后記》中,哈特接著上段引文提到,“此項厘清工作的出發點,就是我在本書第四頁中所提到的,任何受過教育之人都普遍擁有的,關于現代國內法體系之顯著特征的常識”。B36在《法律的概念》開篇,哈特對這些有關國內法體系之顯著特征進行了概括性描述:
“一、在刑罰之下,禁止或責令某些方式加以損害之人的規則;二、要求人們賠償那些他們以某些方式加以損害之人的規則;三、規定作成遺囑、契約或其它賦予權利和創設義務所需之必要要件的規則;四、決定規則為何、它們是何時被違反的,以及確定刑罰與賠償的法院;五、制定新規則和廢止舊規則的立法機構。”B37
我們之所以大段摘錄這段文字,無非是想表明哈特的法律理論起始點,這個起始點就是現代國內法體系及其所具有的顯著特征。哈特所描述的現代國內法體系是一個相對具體的制度類型,對我們來說,現代國內法體系是我們的法律概念之核心情形。這樣,當哈特從事于闡明法律這個概念的任務時,他聚焦于這種類型的制度;這項任務一旦完成了,我們就可以更滿意地掌握我們的法律概念,并且處于更好的位置上來看其他文化的社會實踐(如原始法律、國際法或與我們自己的實踐極其不同的外國法律實踐等等)是否是法律的個例。這就是法律概念和法律理論的普遍性意義所在。所以,非常清楚的是,哈特理論事業的起點是“地方性”的。要言之,哈特的概念厘清工作把法律這個概念的地方性闡釋作為了起點。
當然,這里要再次強調的是,哈特對法律概念的回答不是簡單地重復受教育之人對現代國內法體系這些顯著特征的描述,哈特明確反對以這種武斷方式來結束“什么是法律”這個惱人不休的問題。因此,更準確地說,概念分析的普遍性在于尋求概念的必然屬性,即我們要從現代國內法體系的常識中厘清法律的本質。否則,憑借現代國內法體系的偶然屬性來闡釋其他法文化就可能不得要領。
一旦我們看到哈特法律理論的起點是地方性的,他的法理學方法和德沃金的就沒有那么大的鴻溝了。在《法律帝國》中,德沃金表明了他的理論起點是,“集體地確認出自己文化中算是法律實踐的實踐。我們有著立法機構、法院、以及行政機構與機關,而這些機構所做成的決定,都以規范的方式被加以報導”。B38德沃金的這個說明與哈特所謂受教育之人的常識非常貼近。這也恰如德沃金所指出的,“法哲學家擁有著對法律領域相當無爭議的前詮釋確認” 。B39
我們現在關注的是法律理論從哪里開始的以及它是如何普遍的。大致而言,哈特和德沃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根本的分歧,他們的理論工作都是從對屬于我們的法律文化的理解入手的。質言之,這兩個理論都從地方性開始,并且認為我們能夠利用從這個起點而來的法律理論來把握完全不同于我們自己的法律實踐。法律固然總是地方性的制度,但是法律理論可以追求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所以,哈特與德沃金都是在從事普遍法理學的事業,他們的主題是相同的,他們的理論論爭在同一個平臺上展開而非互不搭界。
當然,在法律理論之普遍性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發現哈特與德沃金的兩點不同。首先,相比于哈特,德沃金更好地揭示了法律理論的普遍化機制。在內在精神上,德沃金的詮釋性法理學與菲尼斯式的法理論之普遍化機制保持了基本一致。德沃金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困難,“任何追求合法性一般觀念的嘗試都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它必須力求充實的內容,以避免空洞,它也必須力求足夠的抽象,以避免地方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言,德沃金在《法律帝國》中嘗試開辟了一條能夠避開這兩種危險的路線,即“通過循著上述兩個維度的線索進行的并對之作出回應的建構性解釋過程,合法性可以得到最好的闡釋”。B40其次,哈特和德沃金各自理論的出發點存在些許差別,后者從普通法體系開始,前者則從一個現代國內法體系這個更廣義的看法出發。此外,拉茲在對來源命題的論證中也著重指出,該論證所主要依賴的是我們對現代國內法體系基本特征的理解。B41
第一點不同其實展現了德沃金對法律理論性質的深刻洞見;第二點不同雖然確實存在,但卻不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差別。就這個出發點的差別來說,佩里曾指出其在方法論意義上并不重要。B42或許,我們認為,哈特所依賴的現代國內法體系不加區分地把普通法文化和民法法系法文化都包容在內,因而德沃金從其所處的英美普通法文化出發的理論事業似乎更為可取。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如下事實:這兩種法文化其實都出自一個更大的歷史傳統,而且在今天正在相互影響和融合。所以,哈特的理論起點也同樣可靠。
結 論
在分析法理論的語境下,圍繞著如何進行法概念研究的問題,我們對法律理論的方法及其性質進行了若干討論。簡要總結這個討論,可以列出如下四個論題:
(1)法律的概念分析不是對法律概念的語義分析;
(2)概念分析是對法律之本質(必然屬性)的探究,是對法律這種特定制度性類型的探究,從根本上講,這是對屬于我們的法律概念之自我理解;
(3)一種合格的法律理論只能是評價性或證立性的;
(4)法律理論的普遍性不僅不排斥地方性,而且要以地方性為出發點。
上述四個論題實可歸結為同一個論題,即我們可以用第二項論題來概括本章的全部觀點。首先,在這四項論題中,第一項論題只是一個否定性主張。當然,就概念分析的否定論題而言,我們還提到:法律的概念分析既不適用經驗科學的方法也不能被呈現為科學對自然種類的那種研究方式。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發現,第三項論題和第四項論題都來源于對第二項論題特定方面的進一步闡釋。后兩項論題對第二項論題的強化主要體現在:一種關于法律本質的理論既然是對屬于我們的法律概念的自我理解,那么研究者就不能在一種脫離語境的情形下,以觀察者的視角來從事描述性工作;相反,他必須從特定的語境(例如,哈特所說的“現代國內法體系”)出發,以參與者的姿態來從事評價性工作。
我們已經強調了這樣的一種評價性工作與法律理論所蘊含的如下問題意識緊密聯系在一起,即法律對我們為什么重要?法律這一制度類型反映了我們怎樣的實踐興趣?必須承認,如果沒有對賦予法律概念之用途的人類興趣和價值的反思,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為什么一系列特定的經驗屬性就一定以其本來的方式歸結為法律這一概念。除非我們在某個意義上抓住了法律的本旨,否則這一概念似乎會是古怪和無定形的(shapeless)。B43無論如何,“法律”這一概念絕非是用來簡單地對一種獨特的實踐類型加以描述,毋寧說,它在法律實踐之內扮演著重大角色,其本身是規范性的。因此,法律理論的任務是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自己的法律實踐,法律理論的焦點在于詮釋我們在運用法律這一概念時所追尋的獨特目標。質言之,我們必須對法律這一制度性實踐的本旨、目的或功能作出說明,這構成了一個成功的法律理論之不可或缺的前提。
On Methodology and Nature of Theory of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ZHANG Chao
Abstract: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misunderstandings as to theory of law before undertaking detailed studies so as to establish proper methodology and explore nature of theory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of law equals that of nature of law. This methodology is grounded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of law is not semantic analysis. Secondly, conceptual analysis is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feature of law and to study the typology of law with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nd in essence a self-understanding of legal concept. Thirdly, a qualified theory of law can only be evaluative or justifiable. Fourthly, with regard to theory of law, the universality should be based on rather than incompatible with the locality.
Key words:theory of law; nature of law; conceptual analysis
注
① Brain Bix, Raz on Necessity, Law and Philosophy 22, 2003, p.555.
② [英]約翰·奧斯丁:《法理學的范圍》(譯者序),劉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③ 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6.
④ 在這方面,哈特的兩篇代表性文章是“責任和權利的歸屬”以及“法理學中的定義與理論”,參見H. L. A. Hart, The 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49 (1948-9), Reprinted in Logic and Language, 1st series (A. Flew,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pp. 145—66; H.L.A. Hart,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0—48.
⑤ Jules Coleman, ed. ,Hart’s Postscript: Essays on the Postscript to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
⑥ 前引⑤, p.6.
⑦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⑧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
⑨ [美]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義》,周林剛、翟志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頁。
⑩ [美]布萊恩·比克斯:《法律、語言與法律的確定性》,邱昭繼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頁。
B11 前引⑤, p.415.
B12 前引⑧, p.29.
B13 前引③, p.203.
B14 前引⑦,第193頁。
B15 前引⑧, p.31.
B16 前引⑨,第163—164、254頁。
B17 前引⑧, p.15.
B18 鄭永流、張超等:《在全球和諧中商談法治——第24屆國際法哲學與社會哲學大會學術綜述》,載《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2期。
B19 前引⑨,第9頁。
B20 [美]德沃金:《法律帝國》,李冠宜譯,時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頁。
B21 前引B20,第13頁。
B22 前引⑦,第223頁。
B23 前引⑦,第187頁。
B24 前引⑤, p.311.
B25 前引⑤, p.426.
B26 “阿基米德式”的哲學分析是德沃金對描述性哲學話語的形象比喻。德沃金指出,哈特的立場就是標準的阿基米德觀念的一個特殊個案。阿基米德觀念的方法論特征是:研究家認為自己雖然研究某一類別的社會實踐,但自身卻并不參與其中。這個方法論共同預設了同一個區分,即區分了所研究之實踐的初階話語(the first-order discourse)與研究者自己的“元”話語的二階平臺(second-order platform )。參見前引⑨,第163—164、187—188頁。
B27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
B28 See Coleman, Jules and Scott Shapir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 Philosophy of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26.
B29 在《哈特的后記與政治哲學的要義》這篇文章里,德沃金明確對政治性概念(法律屬于政治性概念)的哲學分析方法提出如下主張:“我們不能合理地宣稱,對價值的哲學分析是概念性的、中立性的和非參與性的。但我們能合理地主張,它是規范性的、參與性的和概念性的。”參見前引⑨,第178頁。
B30 前引⑤, p.313.
B31 參見前引B20,第127頁。
B32 前引B27, pp.9—11.
B33 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0.
B34 前引⑦,第221頁。
B35 前引⑦,第220頁。
B36 前引⑦,第220頁。
B37 前引⑦,第3頁。
B38 前引B20,第99頁。
B39 前引B20,第101頁。
B40 前引⑨,第208頁。
B41 前引B33。
篇(3)
我們目前正處于民法法典化的過程之中,而民法法典化必須對民法的要素有完整準確的理解和恰當科學的把握。唯其如此,才能從抽象而宏觀的層面上保證民法法典化的質量。那么,構成民法的要素都有哪些呢?這需要從法理學的理論出發來作答。法律要素乃與法律體系相對而言。借用體系和要素這樣的系統論范疇來說明法律現象,不僅有著理論上的解析作用,而且能夠使得我們對法律的認識更清晰、更具體、更豐富。在西方法學史上,分析法學派曾把法律要素歸結為單一的“命令”。這種“命令”模式對法律體系的解釋很不恰當。針對此錯誤,有法學家將法律要素多元化,而分別提出了“律令-技術-理想”模式和“規則-原則-政策”模式。①借鑒這些研究成果,并結合國內外的法律實踐,我國法理學界一般認為,法律要素包括法律規范、法律原則和法律概念,并且法律規范占絕大多數。據此,民法的要素就包括民法規范、民法原則和民法概念。在民法的這三大要素中,民法原則乃民法的靈魂,民法概念乃民法的基石,而民法規范乃民法的主體。既然民法規范乃民法的主體,那么,在目前民法法典化這個大背景之下,探討民法規范的界定問題,分析民法規范的邏輯結構問題,對于提高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科學性,無疑是有著積極意義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為突出法理學原理對于部門法學的指導作用,本文的論述始終遵循從法理學的一般原理到民法學的具體問題這一思維路徑。
二、民法規范的界定
界定民法規范的基礎和前提乃在于對其功能和作用以及它與相近概念的關系的深入思考。分析法學巨匠凱爾森教授有言:“我們對自己智力工作中那些擬用作工具的術語可以隨意地界定,問題只在于它們是否符合我們意欲達到的理論目的。”②因此,確定法律規范的科學涵義,就將引發這樣的思考:作為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規范乃是根據需要“建構”而成,而此處所謂“需要”,即指我們確立一個概念的目的。顯而易見,這與我們對“既定”概念的通常處理方式有著截然的不同。這里需要克服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即突破對概念的實體論理解,而代之以功能論。對概念的實體論理解實質上是一種反映論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雖有其用武之地,但并不適于法律規范這類概念的界定。概念的本質問題乃是貫穿于哲學史古今的一個大課題,其突出表現當推中世紀唯實論和唯名論的爭執。唯實論認為,“在人類思想的世界和外部現實的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嚴格的對應。”③而唯名論則認為,“概念只是一種名稱,也即稱謂,而這些稱謂在客觀自然界并沒有直接的、忠實的復本和對應物”。①
概念的實體論理解與唯實論的思想相互一致,而唯實論的傳統則構成了西方哲學史上的主線,由古希臘的柏拉圖至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而登峰造極。按照該派的觀點,概念是本原和實體,有固定的所指和確定的涵義。概念的功能論理解則與唯名論的根本主張一致,認為概念并非抽象的實體,其確切涵義只有在使用的過程中在具體的語境中才能確定。可以看出,概念的功能論理解比實體論理解更為靈活。維特根斯坦曾明言:“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②這一思想在新分析法學的倡導者哈特那里得到了重視。在指出通常的定義模式并不適合于法律領域之后,哈特闡發了源自邊沁的思想:“我們絕不能把這些詞拆開而孤立地去看,而應將它們放回到它們在其中扮演獨特角色的句子中去,從而進行整體的衡量。”③這一思想自19世紀中葉實證主義興起,特別是自20世紀分析哲學成為西方哲學的主導特征以來,已獲普遍認同。法律術語的意義取決于這些術語被使用的語境、使用這些術語的人以及使用這些術語的目的。因此,在研究法律概念時,不應問該概念的本質是什么,而應問該概念的功能是什么。④以概念的功能論理解為基礎,我們才能對法律規范這個概念進行建構。據此,本文對民法規范作如此界定:所謂民法規范,系指作為民法基本要素、具有嚴密邏輯結構并且能夠發揮民法調整功能的最小單元。
關于這個界定,需要作三點說明。其一,民法規范在整個民法中占有最大比重,是構成民法的主要要素,這可從絕大多數法律均以權利義務性規定為其主要內容這一點而得到證明,因為“是否授予權利或設定義務是檢驗一個法條是不是法律規范的標準。”⑤其二,民法的根本功能在于調整市民社會,而民法規范作為民法的主要構成要素當仁不讓地承擔著這一功能。其三,民法規范之所以必須是“最小單元”,原因在于確立概念的目的就是用它方便地建構或有效地解釋整個知識或文本體系。因此,研究者就必然要尋求各種意義上的“最小單元”,這正如生物學將“細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將“商品”作為其相關研究的“最小單元”一樣。綜合此處的三點,我們可以說,民法規范就是關于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最小的獨立完整的表述。
我國法理學界對法律規范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規范作為構成法律的主要要素乃是規定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責任的準則和標準,⑥或者是賦予某種事實狀態以法律意義的指示和規定。⑦孫笑俠教授將法律規范界定為通過法律條文表達的、由條件假設和后果歸結兩項要素構成的具有嚴密邏輯結構的行為規則。⑧劉星教授則將法律規范表述為“規定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職責的準則,或者賦予某種事實狀態以法律意義的指示”。⑨這些就是目前國內有代表性的幾部法理學教材對法律規范的界定。它們的共同點在于都強調法律規范是關于法律上權利和義務的規定,都強調法律規范有著嚴密的邏輯結構,盡管具體表述不盡相同。不過,這些界定均忽視了法律規范的“最小單元”性質,而正是這種忽視造成了目前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的普遍誤差。本文認為,從功能要求上說,法律規范乃是構成法律的細胞,故而“最小單元”就是其題中應有之意。
三、民法規范的邏輯結構
關于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目前法理學界有三種觀點。第一種是傳統三要素說,認為法律規范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組成;10第二種是兩要素說,認為法律規范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構成;11第三種是新興三要素說,認為法律規范由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構成。12本文認為,這三種關于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觀點都存在著缺陷。為敘述簡潔,有必要明了這三種觀點相互之間的關系。一方面,第三種觀點實際上包括了第一種觀點,因為前者的“條件”就是后者的“假定”,前者的“行為模式”就是后者的“處理”,而前者的“法律后果”則不僅包括了后者的“制裁”,而且還多出了“肯定性法律后果”這一內容;另一方面,第二種觀點實際上與第三種觀點相同,因為前者的“行為模式”本身就包含了后者的“條件”和“行為模式”。①這樣一來,目前法理學界關于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這三種觀點,盡管其外表有些許差異,但其本質卻實屬相同。簡而言之,它們都認為“法律規范=條件(即假定)+行為模式(即處理)+法律后果(包含制裁和肯定性法律后果)”。那么,這個公式所代表的觀點都有哪些不科學之處呢?
首先,并不是每一個法律規范都有“法律后果”這一部分。法律規范可以分為授權性法律規范和義務性法律規范。義務性法律規范可能需要法律后果,但授權性法律規范絕對不需要法律后果。“授權性規范是指示人們可以自己作為、不作為或可以要求別人作為、不作為的規則。……授權性規范的特點是為權利主體提供一定的選擇自由,對權利主體來說不具有強制性,它既不強令權利人作為,也不強令權利人不作為,相反,它為行為人的作為、不作為提供了一個自由選擇的空間。”②由此可見,授權性規范既不包含制裁這種否定性后果,也不包含獎勵這種肯定性后果。例如《婚姻法》第11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據此授權性規范,因脅迫而結婚的人可以申請撤銷該婚姻,也可以不申請撤銷該婚姻,而不管該人如何行為,法律都既不會獎勵該人,也不會制裁該人。
其次,即使對于那些具有法律后果的法律規范,將“法律后果”和“行為模式”并列起來也違反了形式邏輯。法律后果包括了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包括了肯定性法律后果。不管是哪一種法律后果,都會導致法律權利義務的產生,因而都是行為模式。也就是說,“法律后果”和“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同一個東西,都是有關法律權利義務的規定。既然兩者規定的內容相同,那么,對它們兩者賦予不同的名稱并將它們并列起來合適嗎?有必要指出,這種將“法律后果”和“行為模式”并列起來的做法,實質上就是要求法律規范必須具有對責任的規定,而這正是奧斯丁法律“命令說”的翻版。奧斯丁認為,“不完善的法律,例如沒有制裁規定的法律,是有缺陷的,是不具有命令特點的法律。”③奧斯丁分析法學的“命令說”對法律的理解不僅為自然法傳統所不能接受,也為奧斯丁之后的法律實證主義所批判,足見強調責任性規定為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必要組成部分的觀點非常片面。
最后,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不等于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屬于事物自身的結構問題,而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則屬于事物之間的關系問題。上述關于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公式可以這樣來表達:如果A(即條件或稱假定),那么B(即行為模式或稱處理);而如果非A,那么C(即制裁)。在這里,作為制裁的C,其實也是一種處理,只不過是否定意義的處理罷了,因為制裁的結果必然會產生義務,即第二性義務。④這樣一來,我們本欲分析“一個”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但卻在實際上談論著“兩個”法律規范,從而揭示出了目前法理學界關于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那些觀點的本質缺陷:它們原來是在談論“兩個”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問題,而并不是在談論某“一個”法律規范本身的邏輯結構問題。
試舉例說明。《公司法》第172條規定:“公司除法定的會計賬簿外,不得另立會計賬簿。對公司資產,不得以任何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同法第202條規定:“公司違反本法規定,在法定的會計賬簿以外另立會計賬簿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責令改正,處以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這里,兩個法條代表了兩個各自獨立的法律規范,因為每個法條都是一個關于法律權利義務關系的最小的獨立完整的表述。但是,上述公式所代表的觀點卻認為前條(第172條)包含了“條件(即假定)”和“行為模式(即處理)”,而后條(第202條)就是“法律后果(即制裁這種否定性法律后果)”,從而認為這兩個法條合起來才構成一個法律規范。這表明,傳統的三要素說本質上不是在談論“一個”法律規范本身的邏輯結構,而是在談論“兩個”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
造成這種誤差的根源在于忽視了法律規范的“最小單元”性質,從而錯誤地把相互關聯的兩個法律規范當成了一個法律規范。忽視了法律規范的“最小單元”性質,我們對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的分析就可能無限制地擴展下去,進入法律規范間關系的分析領域,而有關聯關系的法律規范不僅可能存在于同一個規范性法律文件中,而且還可能存在于多個不同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中,以致于這種分析完全可能“跨文本”。
在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這個問題上,學界混淆了整個法律體系和作為整個法律體系的元素的部門法這兩者之間的科學區分,同時對民法刑法和私法公法不加分別,并且從義務本位出發觀察問題,從而把一個本來簡單的問題人為地復雜化了。綜上關于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見解,在民法規范的邏輯結構這個問題上,本文的觀點是:民法規范就是一個關于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最小的獨立完整的表述,它只包含“假定”和“處理”兩個部分。在這里,“假定”就是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產生條件的預設,它與上述學界觀點中的“條件”等同;“處理”就是對特定預設情況下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具體規定,它不但涵蓋了上述學界觀點中的“行為模式”,而且也涵蓋了上述學界觀點中的“法律后果”,從而包括了上述學界觀點中的“制裁”。
對民法規范的邏輯結構作這種理解,不僅在法理學上有如上根據,而且在作為部門法學的民法學上也有根據。將此邏輯結構和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相比照,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假定”就是對民事法律事實的概括,而“處理”就是民事法律關系本身。這里的“處理”既包括調整性法律關系,如人格權法律關系和所有權法律關系,也包括保護性法律關系,如侵權責任發生時,責任人和權利受侵人之間的法律關系。顯而易見,按照對民法規范邏輯結構的這種理解,在我國未來民法典中,侵權法無法獨立于債法。①
四、代結論:民法規范與民法條文的關系
篇(4)
自從法律的理論產生以來,法律理論就顯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法律理論發展到今天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法律理論的三元鼎立和多元共存。這正如我國著名的法哲學、法理學家張文顯教授在《當代西方法哲學》一書中,對西方法哲學的多元性和三足鼎立所總結的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法哲學的多元化表現為以某種學說或學派占主導的多元化。戰后這種一家占主導地位,同時存在其他學派的局面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先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然法學和社會法學三大學派鼎足而立,七十年代以來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然法學,社會法學和經濟分析法學派旗鼓相當,同時存在若干小學派。”[1](P14)而另一位重要的西方法哲學研究者北京大學教授沈宗靈也認為現代西方法理學的特征中:1.派別繁多,2.自然法學在戰后的復興,3.三大派鼎立,4.三大派相互靠攏,5.非法學思潮的影響的前四個特征都與三足鼎立和法學理論多元有關。而沈宗靈教授更明確指出:“現代西方法理學雖然派別繁多,但主要是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2](P27)西方當代的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構成西方理論法學的研究特色。但我們知道,所謂的法律理論是以法律這一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如果某一理論不以法律這一社會現象為對象就不能稱其為法律的理論。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難道現實中有三種法律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三個學派只能研究法律這一總體現象的某一方面,指向法律的某一個視域。對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的發展過程進行研究可知,西方法律理論的形成恰恰指向法律的某一視域,這一視域的形成恰恰是當時社會法律生活的反映。因為法律哲學作為法律生活的自我意識,它是通過法律哲學家思維著的頭腦所建構的,規范人們如何理解和怎樣變革人與法律世界相互關系的理論。任何一種法哲學理論,都凝聚著法哲學家所捕捉到的該時代人類對人與法律世界相互關系的自我意識,都貫穿著法哲學家用以說明人與法律世界相互關系的獨特的解釋原則和概念框架。因此,任何一種真正的法哲學理論,都應是黑格爾所說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都應是馬克思所說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具有二千多年歷史的自然法學的研究都指向法律的理想的價值視界;而分析實證法學的研究都指向了法律的規則視界,并堅持以實在法為自己的研究指向;社會法學的產生歷史較晚,但這一研究指向是法律實際作用的視界。這樣在法律理論的研究中就形成了法律研究的三個視角和法律研究的三個視界。法學研究的三個視角是思考法律問題的基本方法:一個是自然法學的價值研究方法,一個是分析法學的實證分析方法和法社會學的社會分析方法。
而特定的方法指向法律的不同視域,從而體現了法律研究的視角同法律的視界的統一。法律思維的三個視界的形成來源于社會現實的情況和法律價值,法律規則,法律現實之間的矛盾性。我們知道在前現代社會中,由于宗教、道德、法律的相互融合,國家的立法,即政治權力的立法在當時的社會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在某些社會中政治權力的立法處于次要地位,如前現代社會中的印度社會中的法律,伊斯蘭社會中的法律,中世紀的歐洲社會中的法律都處于對宗教的補充的法律地位。即使在政治權力的立法相對比較重要的古代中國社會和古代的羅馬社會中,中國的古代國家的法律深受禮的影響,禮法之中可能禮顯得更加重要。而羅馬法更深受自然法的影響。因此,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作為研究法律理論的法律哲學,當然這種法律哲學并沒有同其它理論明顯分離開來,就必然把法律的理想、法律的價值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這種研究體現于古希臘的政治法律哲學以及羅馬的律法理論之中,體現于十六———十九世紀的自然法,自然權利和人權之中,體現于當代的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之中。這種理論更扎根于人性之中。當十六世紀以后,隨著國家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政治力量,國家的法律越來越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特別是隨著國家立法越來越形成獨立的體系,那么對法律自身的規范分析就越來越成為法律研究的主要任務。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了一個反對前幾個世紀中自然法的強大運動。法律分析成為法律研究的主要方法,從而形成法律的規則研究的視角。
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認為,只有實在法才是法,而所謂的實在法就是國家確立的法律規范。這種法律理論實質上重視產生法律的權力因素。隨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國家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之后,由于國家從社會的守業人而逐漸成為社會的管理者,國家的社會職能不斷增加,開始進入法律的社會化階段而形成國家不斷調整經濟并興起福利性立法,而越加注重法律的實際作用。與之相連出現了法律研究新的社會轉向,從而形成對法律實際作用,考察法律的社會效果的法律社會的研究視角。縱觀法律三個視界研究的視角的形成,法律的三個視界即法律的價值視界,法律的形式視界,法律的現實視界,是形成法律研究的價值視角,法律研究的規則視角,法律研究的社會視角的根本,而與此相關的研究視角都可劃入這三個視角之中。法律三個研究視角的形成也來源于法律的價值視界,法律規則視界和法律的歷史現實視界之間的矛盾性。法律的價值,規則和現實之間存在著矛盾性,一方面表現為法律價值,法律規則,法律現實的一致性,即三者的同一,也就是法律價值轉化為法律規則。法律規則轉化為法律現實,而法律現實又與法律的價值相一致。這也表現在人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法定的權利和義務,現實的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在現實中法律的價值,法律的規則和法律現實的不一致,不同一。
它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1.法律價值與法律規則的矛盾,它表現為法律規則不體現法律價值,即立法沒有體現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價值沒有轉化為法律規則,即某種價值精神沒有轉化為法律。2.法律規則與法律現實的矛盾。它一方面表現為法律規則沒有轉化為法律現實,即法律規則的無效性。另一方面是法律現實中的事實沒有相應的法律規則,它表現為立法的滯后性。3.法律現實與法律價值的矛盾。它一方面表現為法律的現實不體現法律的價值,即法律價值的未能轉化性。另一方面是法律現實中的合理性沒有轉化成法律的價值和觀念,這樣存在于法律的理念落后于法律現實。正由于法律的價值視界,法律的規則視界,法律現實視界之間存在的矛盾使法律研究的三個視角可以互相指責各自理論的弱點。法律的分析理論和社會理論指責法律價值理論的無用性和意識形態的性質,法律社會理論指責法律的規則主義是一種“書本上的法律”“規則的無效性”等等。正由于法律的價值視界,法律的規則視界,法律的歷史現實視界的矛盾。那么解決這三個視界的矛盾就成為法律理論,法律規則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真正能解決法律這三個視界的理論矛盾的可能就是法律的綜合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同意杰羅姆•霍爾的觀點:他從相似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前提出發,發出強烈的呼吁“要求當今的學者努力創建一個‘統一的法理學’。#p#分頁標題#e#
他嚴厲地批判了法理學中的‘以單一因素去闡明復雜現象的謬誤’,尤其是那種試圖將法理學理論中的價值因素,事實因素和形式因素孤立起來的企圖。霍爾認為,今天所需要的是分析法學,對社會和文化事實的現實主義解釋以及自然法學說中有價值的因素的統一”。[3](P199)因此,法律理論發展到今天已顯示出明顯的法律綜合的趨向,這不但表現在一批綜合法學派的領軍人物,杰羅姆•霍爾、E•博登海默、J•斯通、哈羅德、L•伯爾曼等主張使用法律研究的綜合方法,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更表現在當代西方的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個主流法學派的相互靠攏上,他們已明顯看出采用一種法學的研究方法,研究法律的單一視角,考察法律的某一視界是不可能完成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偉大使命。他們在堅持自己的研究特色的同時,更吸取其他學派的成熟觀念。所以,不論從法律的理論研究的成果上,法律自身的規則發展上,還是從社會的進化上,今天都可能成為一個法律理論綜合的時代,那么,采取何種方法,運用何種步驟,對法律理論進行綜合確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的問題。當談及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時,它的顯著特點是用一種多維的,全方位的視角來考察我們現有社會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調整器———法律。而任何只用一種視角來考察法律的理論在某些方面可能很深入,很徹底,其結果將證明這種單一的視角是片面的,但這種方法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應將具有重要價值。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對法律的考察則應采用一種多維的、多視角的方法,這是面對復雜的法律現實采取的唯一的正確方法,這正如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認為的:“法律是一個帶有許多大廳、房間、凹角、捌角的大廈,在同一時間里想用一盞探照燈照亮每一個房間,凹角、和捌角是極為困難的,尤其是由于技術知識和經驗的局限,照明系統不適當或至少不完備時,情形就更是如此了。[3](P199)因此,我們不能象分析主義法學那樣,認為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歷史上的大多數法律哲學都是非科學的“胡說”。
相反,我們可以更為恰當地說,這些學說最為重要的是它們組成了整個法學大廈的可貴的建筑之石,盡管這些理論中的每一種理論,只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但隨著我們知識范圍的擴大和事務發展的成熟,我們必將進行一種更偉大的事業,即在利用人們過去所做的一切貢獻的基礎上,建立一門綜合的法理學。而建立統一綜合法學至少有三方面的意義。首先,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我們知道某種重大的理論都是面對社會現實并對之提出某種解決的方案。而法律本身從人類社會的早期,即公元二千年前發展到今天,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法律規范體系,它幾乎調整著人類的整個生活,使人們的生活規范化。正因為如此,在一些偉大的思想家那里都對“生活的法律化感到擔擾”,特別是現代化社會發展到今天,韋伯提出,現代化的主要后果是“自由的喪失”,而當今最偉大的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將韋伯所說的“自由的喪失”解釋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實質上就是生活世界的“法律化”(Juridification)。因此,我們今天如何看待生活世界的“法律化”顯然就不能用簡單、片面的認識方法,而應對法律世界的擴張進行全面的宏觀分析,這是建立統一綜合法學的原因之所在。其次,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也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同法律的實踐相比,法律的理論的發展相對較晚,但它致少也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在這樣歷史的長河中,無數的法律哲學家都對法律理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法律理論發展到今天,明顯出現三大相互對立的法學傳統。這正如我國著多法理學家沈宗靈教授認為:“現代西方法理學雖然派別繁多,但主要是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4](P27)他也正是依據這三個學派的分立而建立他現代西方法理學體系的。
單就一個法律問題為什么出現三種相互對立的學派,顯然在法律的理論上需要統一。這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法律實踐的問題。這正如美國法理學家霍爾指出“法律是形式價值和事實的特殊結合”。而霍爾的法律概念中的這三種因素,正是分析法學、自然法學和社會法學所分別測重研究的問題,因此,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就在于看到了法律的形式因素、事實因素和價值因素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最后,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也是法學方法論統一的需要,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必須實現方法論的統一。而這種統一絕不是法學方法論的簡單相加,而是有機的綜合,也就是說只有采取綜合性的方法才能實現這一偉大任務,這種方法顯然應是邏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的方法。邏輯的方法是把法律看成是辯證的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應找到它統一的基礎。具體在后面我還要談及這一問題。美國著名法學家哈羅德•J•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一書中的序言中指出:“我們需要克服下列現象:將法律歸結為一套處理事務的技術性手段;使法律脫離于歷史;把一國的法律等同于我們的全部法律,把一國的法律史等同于我們全部的法律史。也需要清除以下謬見:排他的政治的和分析的法學(‘法律實證主義’)或孤傲的哲理的和道德的法學(‘自然法理論’),唯我獨尊的歷史的和社會經濟的法學(‘歷史法學派’,‘法的社會理論’)。我們需要一種能夠綜合這三個傳統學派并超越它們的法學。”[5](P227)他提出要建立一種能夠綜合三個傳統學派并超越于它們的法學,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的后三十年中,美國的法理學家霍爾,博登海默,澳大利亞的丁•斯通等很多一流的法理學家都主張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這么多一流的法學家為什么都主張建立綜合法學并為此而進行了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形成西方現代法學的一支獨具特色的力量。
這里就涉及到綜合法學產生的基礎性問題。我認為建立統一的綜合法學應有三方面的基礎。
其一是產生統一綜合法學的理論基礎,任何理論的產生都有其自己的理論根源。而上一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產生的統一綜合性法學的理論體系可以說是十分豐富的。因為在它產生之前,在西方的法學理論界早以形成三個重要的法學流派,他們就是自然或價值論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當然這些學派產生的時期和歷史條件各不相同,而自然法學派有著最久遠的歷史,它在歷史上雖然有過缺時間的衰敗,但它不久又加以復興。說明它具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而這一派聚集了歷史上最優秀的大思想家,也是理論系統最豐富、最有影響力的一派,他們的思想影響整個學界并直接作用于社會。這一學派形成西方思想史上的三次高峰期。那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基者霍布斯、洛克、康德、密爾等一大批一流的政治法律哲學家創造了西方政治理論的第二次高峰。他們的思想至今還影響著我們的政治生活。而以1971年羅爾斯出版了他的名著《正義論》,并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正義問題的大辯論。成為西方政治法律哲學的第三次學術高峰。他們的理論系統是我們探討法律價值的重要財富。而重在研究法律自身的分析實證法學的一批法學家奧斯丁、凱爾森、哈特、拉茲等為規范法律哲學的創立建立了深厚的理論系統。而在本世紀一大批的法律社會學家,特別是以龐德為的社會法學是法律實證分析的重要代表。因此,只有吸收這樣一大批理論家的成果才能建立一個堅實的統一綜合法學。#p#分頁標題#e#
其二,建立統一綜合法學的法律基礎。法學研究的直接對象顯然是調整人們行為的法律制度,而法律制度在杰羅姆•霍爾看來“法律乃是形式、價值和事實的一種特殊結合”[3](P187)這說明只有把法律看成是法律的價值一種制度理想同法律條文本身及它作用于社會形成的一種動態的法律秩序結合,才能全面地考察社會中最復雜的法律現象,而任何把法律簡單化的看法都不可能正確認識法律。這也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人類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可能根據任何單一的、絕對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釋法律制度。若干社會的、經濟的、心理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若干價值判斷影響著和決定著立法和司法。雖然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某種社會力量或正義理想會對法律制度產生特別強烈的影響,但是根據唯一的社會因素(如權力、民族傳統、經濟、心理或種族)或根據唯一的法律理想(如自由、平等、安全或人類的幸福)都不可能對法律控制作出普通的分析和解釋。法律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網絡,而法理學的任務就是要把組成這個網絡的各個頭緒編織在一起”。我們的法學理論雖然探討了很多問題,但缺乏一種把各種基本理論聯系為一體的具體認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欠。因此,法律的形式、價值、事實的統一是建立統一綜合法學的必然基礎。
其三,建立統一綜合法學的社會基礎。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逐步形成了統一的認識,盡管人們對社會發展采用的思維角度不同,但較為統一的是社會三形態論。如果用最新的學術術語就是社會發展經歷了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用阿道夫•托夫勒的話來說就是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用丹尼爾•貝爾的話來說就是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而按照馬克思的宏觀歷史劃分就是:“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了條件。”[3]第4卷上(P104)因此,按照馬克思的劃分,人類存在的三大歷史形態是: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以個人全面發展為基礎的自由個性。這三種形態集中體現為“自然經濟”、“市場經濟”和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為基礎的“產品經濟”。與這種社會形態相對的法律就以刑罰為主的古代法,以民商為主的近代法和以福利立法為特征的現代法,而這種法律的社會發展顯然是一種辯證的發展過程,而現代法律的綜合顯然體現古代法律、近代法律、現代法律的統一。
三個價值秩序、自由、福利的統一。這種統一是法律發展的最高階段,這正是建立統一綜合法學的社會基礎。建立統一綜合法學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實現法學方法論的統一。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自然法學,分析實證法學和社會法學都有其獨特的方法論,自然法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總認為:“有某些關于權利和正義的特定原則,它們憑著自身內在的優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顧及那些支配共同體物質資源的人們的態度。這些原則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實際上,如果說它們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話,那么它們仍然表達了神的本性并以此來約束和控制神。它們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與理性本身卻互相浸透融通。它們是永恒不變的,相對于這些原則而言,當人消除某些不相關的情況而有資格受到普遍遵行時,它只不過是這些原則的記錄或摹本。而且制定這些人法不是體現意志和權力的行為,而是發現和宣布這些原則的行為。”[6](P5-6)顯然,自然法學派的學者大多都認為在人定法之上有一種更高的法或價值,而人定法必須遵循這些更高的法或價值。因此,他們的法學理論大多同他們的哲學聯系在一起,正因為如此,他們不但是偉大的法學家,更是偉大的哲學家,他們的法律思維更具哲學的思辨色彩。如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塞涅卡、烏爾比安、圣托馬斯阿奎那、柯克、格勞秀斯、洛克、康德、羅爾斯等等都主張人類生活所遵循的法律能夠,而且應當“體現根本的、永恒不變的正義”。當分析法學產生以后的某些分析法學家認為“自然法”是一種無用的“胡說”,但希特勒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了自然法的價值。就連新分析法學的主要代表哈特也承認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而分析實證法學則把法律直接同國家權力聯系起來,只考慮法律的政治因素而排除其它之后。轉而對法律規范進行分析。
從而對完善法律自身作出了貢獻。而社會法學則主要考慮法律的實際作用后果以及對社會和人的影響。因此,他們才能得出“法律官員就爭論所做的事,就是法律本身。”“法律是對一個未來判決的預測”等等。由于社會是發展的,而發展過的東西很快就成為歷史,因此社會法學在本質上是運用了歷史考察的方法來考察社會中的法律,因此通過上述分析、哲學的、分析的、社會歷史的方法都是建立統一綜合法學的必備方法,那么如何實現方法論的統一呢?我認為,人們在對法律進行考察時,明顯地存在著對法律考察的三重視角,也就是法律存在三重視界,即法律的價值視界,法律的規范視界和法律的現實視界。而這三重視界正是西方三大法學派考察法律時所定在法律的不同角度。也就是說自然法學派主要思考的是法律的價值視界。分析法學派主要考察的是法律的規范視界,而社會歷史法學派則主要考察的是法律的社會歷史視界。那么法律理論的統一就是對法律考察的價值視界、規范視界和歷史現實視界的統一。它們是如何統一的呢?我們在此對法律三個視界進行簡要的分析。
篇(5)
內容提要: 法律方法論是法學的綜合性學科,即各個分支學科都要涉及方法論的問題。由于法律方法論中的方法也是借助其他學科的方法,因而這一學科與哲學、邏輯學、修辭學、語言學、解釋學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法律方法論近年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但還是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不注意讀者及“市場”需求、不注意研究的背景、沒有問題意識以及不注意經驗與技術的結合研究,這些弊端已經顯現出來。法律方法論不是純粹的理論,我們應該結合中國的問題意識展開研究。
法律方法論是對法律如何被運用的一系列解釋、論證和推理的技術、技巧、規則、程序、原則的系統思考。從法學家的愿望以及研究所展現的成果來看,一般都認為法律方法論的專業性很強,似乎描述的都是職業法律人才能看懂的東西。但實際上因為法律的運用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太緊了,從而使法律方法論成了人人都可能做出貢獻的學科。不管對該學科有沒有研究,都可以憑著感覺說這一學科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似乎對法律方法的評說無須論證。論說許多的批評是學科發展的動力,但零星的說狠話式的批評多少傷害了研究者的“自尊心”。一些憤青怒吼的無用論、廢話論肯定是建立在沒有仔細研究的基礎上的。因為,如果仔細研究的話,會指出法律方法論的研究存在著什么樣的問題,而不會是沒有任何鋪墊的全面否定。在很多法律方法的研究者看來,這一學科也許是法學各學科中最細膩的學科,如果沒有經過專門系統細致的研究,很難對學科是否完善評頭論足,雖然這并不影響在諸多判斷上發表“高見”。長期以來,其他學科的發展似乎很少能干擾法律方法論學科的孤寂性,學者們基本都是在圍繞著法律規則展開自己的言說。然而最近有一些學者看到,近百年來法學的發展已經沖出傳統法學的封閉狀態,進入了和其他學科相互交融發展的時代。
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中,有些人特別是一些所謂的專業法律人士更愿意把法律應用技術化,這就走向了極端;還有一些學者更愿意把相當狹窄且技術性的法律問題當成廣泛社會問題的縮影。如從反壟斷案件中提出政治自由問題;在合同法中提出人的自主性問題,即在技術性的法律方法中融進了很多的政治理論和社會學理論。有些人甚至提出“形式服從效果”的口號,搞所謂的結果決定論。實際上,這種觀察問題的方法屬于本質決定論,有違法治的基本原則。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形成專斷的理論基礎。對此實用主義法學者波斯納說:“這種廣義理解反映出興趣的拓展,而這恰恰是法律學術的特點。”[1]我們注意到法律方法論有兩個方面的進路:一是根據規范的邏輯分析;二是在邏輯分析中的修辭論證。法律的邏輯運用一直支撐著法治在部分領域的實現,起碼使人們的理解活動逐步接近法治。但由于西方近代的法治實踐,出現過度依賴邏輯的問題,誤導很多人的思想,他們把法律直接當成邏輯,因而霍姆斯提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的命題。自此以后,法學之術在于論辯的主張甚囂塵上。傳統的修學理論雖然沒有得到發展,但實踐和理論中卻出現了修辭的濫用。人們注意到論辯少不了修辭,但修辭卻具有兩面性。對同一個行為既可以說成是謙虛,也可以說成是虛偽(還有魯莽與勇敢、老實與窩囊、粗魯與豪爽、傲慢與自信、聰明與狡猾、慷慨與揮霍等等) 。修辭的不確定性及其變幻使得修辭方法聲名狼藉,因而借用修辭進行論證的法律方法論在其不成熟的時候就呈現出危機。人們討厭法律人的善辯,認為沒有他們世界可能更太平一些。這就提醒我們必須防止過度修辭。修辭論證實際上應該有道德因素、政治因素、審美因素,但更應該看到它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工具。法律中的修辭應該與法律方法論的使用結合起來,過多的修辭可能會使人無所適從。我們必須注意到,法律論證的方法如果離開邏輯的約束就可能是隨心所欲的。在堅持邏輯規則及其相應法律規范的同時,修辭學中強調的“修辭修其誠”還是值得提倡的,雖然在完全的意義上這是做不到的,因為情緒與價值、利益與情景、前見與當下都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方法論在很多情況下只是人們思維的路徑,而不是思維的全部(對修辭的一些認識得益于高萬云教授在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瑪珈山法律方法論壇(第64期)上的演講。高萬云教授認為,人們不可能完全誠實修辭,但我認為這恰恰是倡導“修辭立其誠”的原因之所在。如果都誠實地進行修辭,講究這一原則的意義就會失去。)。法律方法論與邏輯學是血緣關系,而與修辭學(語言學)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親緣關系。雖然法律方法論離不開這兩個方面,但是這兩個方面對法律方法論的影響卻都不是系統的,只是以一些零散的觀點影響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法律方法的研習不僅要修煉善于言辭,更主要的是要長于邏輯,提升簡化復雜事物與行為的思維能力。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如下問題:
一、法律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市場”問題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似乎不用關注市場需求的問題。這倒不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屬于暢銷品,而是說這些研究成果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市場”。一部分學者除了迎合政黨、政府的宣傳要求外,還關心研究成果是否被政府采納。當然還有一些學者的研究似乎是為學術而學術,把研究成果當成小圈子里自我欣賞、陶醉和完善自我的過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買家”的單一性,以及研究方式的自言自語使得研究者很少關心市場需求以及讀者的忍受力問題。現在,多數的研究者也許最為關心的是發表刊物的級別,轉載率、引用率,以及在評職稱評獎項的時候能否用得上。而這些東西有都與個人的待遇、學校和研究機構的評價緊密聯系,思想的創新與文化的發展被丟到了一邊。于是,社會科學的所謂科研成果竟成了自我完善、同行欣賞或批判的對象。人文學科如果是這種情況還是有情可原的,畢竟他們擔負的是文化積淀與傳承的任務。但是像法學這樣的實用性學科也都成了這個樣子,就不能不讓人感覺到悲哀。法學研究尤其是法律方法論的研究,不能為迎合某種宣傳的需要或者把寶押在被領導采納上,如果是那樣的話研究的成功概率太小。我們不能僅僅把研究的定位放到領導關心的視野,而應該與司法實踐的需求結合起來,在司法實踐中發現問題,用理論解決問題。法學研究的課題,從開始到結項都應該考慮市場的需求問題。看對什么樣問題的研究是有出路的,什么樣的表述能贏得讀者,最好是能夠使成果研有所用,對實踐有啟發意義上的指導或至少是有某些參考價值。美國學者埃里克森說:“盡管法學研究成果的市場很難完美,但是我認為它可以運行優良,至少比Edwards法官和其他一些批評家們所想象的更好。這個市場的分析人士們不能僅僅將眼光局限在供給方,而供給方確實包括難以盡述的情愿自我沉迷的教授。在需求方來說,這些供給者所面臨的有經驗的人并不樂意遭到欺騙。盡管一些法學院的教職人員可能偶爾屈從于一些無價值的潮流,但是市場的趨勢最終會懲罰他們。從長遠來看,最為可靠的學術成果的監控方法是那些消費法律服務的顧客們的需求,以及大學對于那些贏得同行贊譽的教職人員的需求。”[2]用市場的觀點來看我國的法律方法論研究,我們會發現大家都在忙著引進西方成果,這一方面凸顯了西方法學研究的“前衛性”;另一方面也為我國法律方法論的研究趕上西方提供知識儲備。這可以說贏得了中國的學術進步的需求,但是問題在于,這種研究缺乏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關注,從較為普遍的角度看司法界對此不甚領情。原本西方的法學研究就不是針對中國司法實踐的,缺乏中國問題的針對性和對策性研究。我們把它拿過來除了增加知識量以外,對中國實踐的影響似乎微不足道。
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應該是圍繞著法律文本的應用而展開的,理論研究成果一方面要接受司法實踐的檢驗,看司法實踐中是不是真的有市場需求。另一方面還要接受理論的檢驗,看研究成果是否經得起邏輯的檢驗。任何想從法律文本中獲取意義的都應該經過方法的拷問。這種拷問是一種理性的、運用邏輯的反思。“法學只有在具備了反思意識與反思能力以后,才會產生法學方法論。”[3]可以說,法律方法論文章的影響力并不完全取決于同行的引證率,而是對司法決策者思維的影響程度;它的水平還取決于法學家對法律解釋結果與過程的反思能力與水平。當學術都是在用引證率、轉載率等來說明自身價值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還要做點別的什么?布萊恩·辛普森的話對法學研究者也許是有震撼意義的。他說:“文學往往是鼓勵法律進行改革的推動力,公眾對法律秩序的不滿,往往只反映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才能上達當局。當狄更斯著力描繪當時司法部的不公和拖拉作風時,他的聲音簡直使當局不得不聽。他對司法界、訴訟程序、衡平法庭、債權法和監獄所做的尖銳批判,有助于形成公眾的改革呼聲。”[4]司法部之所以不敢不聽,是因為他的作品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法學研究要想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需要學習文學的表述方式,應該打動聽眾,在邏輯基礎上做好修辭,給讀者提供簡明扼要的、有問題意識的對策性研究成果。辛普森的話是在告訴我們,研究成果應該面向讀者,作品一旦有了較大的讀者面,就會產生社會影響,甚至會影響決策者。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文學作品中的簡單修辭也許比長篇大論的理論文章更能影響社會。這提示我們的研究者,我們不僅需要邏輯嚴密、層次分明、詳細論證的成果,也需要簡明的修辭來表明我們的立場,有時還得需要借助文學的手法來表達我們的思想。也許對法律方法的論證應該是細膩的,但結論一定是簡單的。法諺早云:“簡潔乃法律之友。”[5]簡潔而明快的法律結論很可能形成法律人的信條,影響法律思維和決斷。
除了研究表述方法的改進外,我們還需要有一種學術獨立與自由的立場。我們看到,由于法學家沒有政治上的權力,因而只能盡力用其學問對當權者施加影響。這就使得法學家們很容易心甘情愿地為當權者服務,成為當權者的奴仆和工具。當然,有時也會出現相反的情況,有很多學者忠于自己的良心,執著于對學術的追求,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使得學術傳承沒有斷流。我們需要把市場看得寬泛一些,不能走極端。這種極端包括,要么把心思全用在迎合權力者的想法,要么完全割裂與社會的聯系,孤立地搞純粹的學術研究等等。我們要看到“法學家雖然有時候不可或缺,但并不真正地受寵于統治者,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在賣弄學問、艱澀難懂以及鉆牛角尖的書卷中,將做出什么樣的結論。他們一般也不受公眾的歡迎,因為他們的言談高高在上,并喜歡把簡單的事情弄復雜”[6]。這個警告雖然不一定是現實狀況,但具有警示意義。在許多場景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學家被鄙視,一些材料顯示英國人特別不喜歡法學專家,認為有些“喜歡賣弄學識的法律博士們,他們只懂得把那些被奉為名言警句的東西引來引去,這些引言或者來自千年歷史之久的書籍,或是來自其他同樣把法律知識埋葬在沉重墳墓中的博士們,他們的理論充滿了矛盾,并只會把普通人引向歧途”[7]。一位歷史學家曾說過:法律人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任何法律問題上,他們總會站成意見相左的兩隊[8],總是喜歡把簡單問題復雜化。
在法律方法論的研究中,我們需要用行動和全新的成果改變對法學家的這些看法。一要面向讀者,找好市場(消費市場在哪里)之所在、社會的需求之何在,讀者群在哪里。二要找市場需求的問題在哪里,對那些純粹理論沒有使用價值的命題,要在研究中予以淘汰,而對那些有現實意義的對策性研究應下大功夫進行。三是我們需要用什么手法予以表述,不要把理論總搞成灰色的,理在事中,我們完全可以在對事實的描述中展開理論,而沒有必要都搞成是從思想到思想的印證。“問題和方法是任何一項研究的兩個基本元素。沒有真問題便沒有文章,沒有適合一定問題的科學方法便沒有好文章。而問題和方法又可以從各種角度進行劃分,形成各種可能的‘問題———方法’組合。”[9]法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實證主義的分析方法和價值分析方法。“法律實證分析的方法元素可以歸結為經驗的研究方法,與這種研究方法有關,法律實證主義的元素又必然以一定本土實際為選題資源,當然,關注實際并非尾隨實際、復制實際、更不是粉飾實際,而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發現、描述和解讀實際。”[10]由于在國外法律實證主義的研究是一種風尚,所以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是用世界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問題。一般來說,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實證主義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與研究的目的有關系;二是與研究的案件是否具有共性有關系。
二、法律方法論研究的學術背景
在中國進行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應該注意到自身的學術背景。這個背景從大的方面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傳統中國文化沉淀到今天的影響;二是西方文化不斷地在中國的傳播,并且還將繼續擴大范圍和深度的趨勢;三是中西方文化的結合在中國所形成的新傳統。在充分挖掘國學精粹的口號下,西方文化也出現中國化的趨勢。這都是研究法律方法論必須注意的大背景。在歷史上我們有律學的解釋傳統,但近百年來已經在形式上丟失了,活著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語。在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以后,中國文化的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起碼在形式上我們在追隨著西方。法律和法學的形式基本上已經西化,只是還用漢字表達。雖然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學者說,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流淌著龍的血液,中國文化的精髓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近百年來中國學科的變化對中國人思維的影響,雖然我們不能把什么問題都集中在文化上,讓其承擔社會進步緩慢的擋箭牌,但是也不能忽略文化的變異對中國社會變革發展的影響。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
近年,我們開始意識到了國學的重要性。于是很多學者開始關注國學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試圖用國粹來解決一些現代性文化解決不了的問題。這多少有些復興傳統文化的意味,是對近一百多年文化斷裂的憤滿。我們看到了很多學者對傳統文化丟失的吶喊,認為傳統已經逝去了意義,但是傳統自有進入當今的途徑。現在,我們已經不再閱讀四書五經,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完全消失。即使我們研究手段、對象以及問題意識等已經發生了大的變化,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傳統與今天的關系。法學研究近百年來實際上有很多是重復的問題,這很可能是沒有歷史地總結經驗,只注意眼前的問題與資料造成的。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否則會招致歷史的懲罰而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一般來說,問題意識的觀念是基于哲學角度的考慮,但在不同的學科和文化背景中,問題的內涵以及面向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在德國討論很多的硫酸是不是武器的問題,竊電是不是盜竊的問題,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中國人思維的整體性缺少細膩的分類要求。因而只要有簡單的歸類,就不會對過于細致的問題提出質疑。所以,我們很容易接受硫酸就是武器,盜電就是盜竊的邏輯。還有在美國被廣泛探討的愛默爾繼承案,在中國也不是問題,這不僅是因為我國繼承法對被繼承人有謀財害命行為喪失繼承權的規定,而且在我國的道德中對此早都有明確的要求。這都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對問題的不同篩選。問題雖然是共同的,但對問題的理解是有文化背景的。我們不僅要注意我們的現在,還要熟悉自己的過去。比如,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優先以及價值判斷正確就不需要方法的觀念。如果不對此類判斷進行反思就會使一些正確理論發揮不出效用。當我們引進了很多現論以后,如果不注意與傳統的銜接就會使它的作用大打折扣。傳統對現代的消解使得我們很難搞成像樣的法制建設,不顧及傳統使得現論成了純粹的呼喊。我們不能排斥各種優良的價值,但應該為價值的實現提供理性的工具。這種思維工具并不像有的人說的是普遍性的。思維規律雖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具有相當的地方性和時代性。在傳統思維中,對方法的忽視已經使中國的哲學顯得不那么完整,在本體論、認識論之外缺乏方法論。方法論的缺失使得我們的科學研究長期停滯不前,特別使得我們的研究深入不下去。這既是歷史傳統鑄成的,也是我們今天必須注意克服的。我們注意到,近年從西方引進的自然科學以及思維方式,多少打破了中國人不講邏輯的思維,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以及對大的問題的看法上,或者說在意識的深層里對方法論的漠視仍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并沒有在現代化的呼聲中消失,在法律方法論研究中我們時刻應該注意到它的存在。這對建設適合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法律方法有積極意義。
(二)新的文化傳統的影響
這種所謂新文化傳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百年來基于革命思想傳播所形成的新傳統;二是對西方法學的盲目追捧。關于革命的思想對中國現代的影響是深刻的,對我們今天研究法律方法論也是不容忽視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當代法治建設的阻力。法治實際上是對現有秩序的守護,是對現存社會的點滴改良,但我們不時能夠發現,很多學者在談論法治的時候依然堅持的是革命思想。革命思想與法律思維很不合拍。滿懷革命熱情很難搞好法律方法的研究和法治建設。法治要求我們應該在理性的基礎上注意要以克制、保守、權衡、寬容與冷靜的態度對法律的意義以及法律方法論的研究,但革命要求我們對秩序進行徹底的改變。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新的傳統。哈佛大學的曼斯菲爾德在總結了西方現代史后認為,在激進的革命思潮結束以后,現在人們似乎普遍地缺乏男子漢的氣概。這并非是男性不爭氣,而是與現代法治社會對人的要求相關:講究理性控制,每個人都很職業,不輕易發怒。因而騎士的時代已經結束,接下來是詭辯家(包括法律人) 、經濟學家、算計者的時代到來了。商界缺乏男子漢氣概是因為商業是物質主義的,滿足于獲取而非獲勝,滿足于權衡而非正義。商業活動拒絕犧牲,立足于算計收益,當今的體育運動員也是如此。他們更關心掙錢,很難與古代的角斗士相提并論。如今什么都講究方法與技藝,充滿男子漢的氣概的那種勇敢的又是帶有莽撞的正義,已經被智慧與理性所代替,我們這個時代對方法與技能的渴求超越了革命時代的激情。這正是法治建設所需要的研究環境,也是實施法治所帶來的人格變化。法學研究與法治建設需要這種背景。法治的實現需要多種因素促成,制度的完善、對法律的信賴、市場經濟的需求、權力分離的政治體系,獨立的職業法律群體以及法律方法論的支撐等都是條件。然而就法律方法來說,“頗有意味的是, 20世紀以前的法學家們很少懷疑自己是否擁有適當的方法,他們相信,以法學的基本要求為準,他們確信的方法較之于其他學問的方法毫不遜色。尤其是古羅馬的法學家們,他們從不談論‘方法’問題,因為他們明白,如果一門法律科學不得不談自身的方法論問題,那么必定出了什么問題”[11]。到了20世紀初年,法學家們開始在反思法律的疑難問題中對所謂概念法學的弊端,開始為法學的健康考慮,開始系統考慮法律方法論問題。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在早期的時候就把關注方法問題稱之為病態。我國的很多學者競相引用,信其為真。但我們認為,對這種修辭性比喻的盲目追捧是有問題的。因為方法論的問題并不是所謂與學科“健康”必然相聯系的問題,而是一個與各個學科相伴而生的元問題。在方法論較為單一的時候,關于方法論的爭論較少,人們似乎感覺不到各種方法論之間的爭寵。但這并不意味著學科的發展就是健康的,法學不是生物學,法律也不是生物有機體,拉德布魯赫的比喻并不恰當。當法治本身沒有出現難題時,人們感受不到方法論的重要性,或者換句話說對方法論的需求不是很高。就像現代中國的簡陋法治,不需要精深法律方法理論。精深的法律方法論研究對初級階段的法制來說是一種奢侈品。但未雨綢繆,我們的理論必須為未來的細膩法治做好準備。
謝暉在其《法律哲學》一書中談到了我國法學研究中方法長期缺席的問題,認為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沒有自身獨立的方法,都是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二是能夠代表獨特法律方法的規范分析方法的缺席[12]。其實,法律方法有沒有獨立的方法問題,似乎不是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而僅僅是一個邏輯性的理論問題。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幾乎很少有所謂符合學科專業屬性的獨立的方法,在很多領域人文社會科學是互相聯系的。“法學思考的公式化可能是個陷阱,它在特定的情形下會表現為可怕的司法擅斷甚至司法專制。”[13]當今社會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學科及其方法滲入其中,并沒有改變社會思維的混沌狀態。各種學科的劃分僅僅使人們的思維邏輯更清楚了。因為各種學科及其方法都是根據不同的邏輯標準所進行的人為的劃分。這其中雖然有發現的成分,但基本都帶有人工秩序的成分。幾乎沒有一個學科不是交叉研究的結果,孤立的學科是不存在的。或者說除了滿足認識論劃分的需求外,社會中原本就不存在獨立的學科與方法,能夠存在的也許只有獨特的方法或者相對獨立的方法。雖然歷史上存在過所謂封閉的法學與法律體系,但那多少也有些夸張的成分,畢竟封閉的法律也必須向社會開放,否則它就不能調整發生在立法之后的案件;即使封閉的法律也必須向解釋者開放,否則就不能獲得與時俱進的生命。所謂封閉也僅僅是一種姿態而已,什么樣的學科都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封閉。當今的法律方法論不屬于傳統的規范法學,而是一種以規范法學為主的綜合性學科,因為它不僅要把規范性的法律作為判案的依據或者說法律思維的根據,而且要把應然的價值變為具體的判斷標準,把現實生活的事物的本質、規律以及人們思維的理性融入對法律判斷的思維中去。在以規范分析為主的法律思維中不能割裂與人類價值追求的聯系,也不能把社會獨立于法律之外,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律。在我國,不是規范法學的缺席問題,最主要的是缺少守望規則法律職業群體。謝暉說:“規范實證,其本質是權利與義務分析方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法律中的權利義務問題,可以視為規范分析方法中的技術之維。”[14]這種方法實際上是法理學和民法學里面的通說。幾乎所有的法科學生都要受這種學說的訓練。我們存在的問題是這種觀念貫徹不到對實際問題的分析中,反而出現了權力、權利絕對化趨勢,即有些人只講權利不講義務、只講權力不講職責。這是規范法學引進中國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法治不可能健康發展。
(三)西方法律文化繼續滲透的現實
當受西方法學的影響中國法學也出現流派化趨勢的時候,各種具體研究與應用所固守的方法成了劃分流派的標準,這一方面加劇了對法律認識的相互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各自方法論的缺陷與優點也就顯示了出來。傳統的自然法學、分析法學仍然在新形勢下固守自己的信念,但自從法律社會學出現以后,理論法學與實用法學出現了分野。法律社會學更多的是對法律現象的描述,分析法學與自然法學的規范作用在社會法學的敘述方式中弱化了。法學似乎更加科學化了。早先關于法學是一門實用學科的概念被法學是科學的概念所取代。雖然我們還能看到:法律人像醫生一樣,是靠對法律嫻熟的運用和其他人所掌握不了的技藝來從事職業活動的。在運用法律時的邏輯與論辯能力是法律人贏得市場的主要手段。但我們也能看到,現代的法學家也像科學家一樣用理性的方式,冷漠地像對待物質世界一樣在研究著法律。價值熱情被科學精神所取代。我們發現法律社會學出現以后,對事實的關注與研究,擴展了法律研究的視野,成了法學研究的主流,有關法律方法和法律的解釋技術反而退居次要地位。現在,西方法學的大量作品都是圍繞著法律規范的基礎而展開的,法律規范的運用與解釋的方法反而沒有受到法學研究者的重視。在西方法學界幾乎要出現傳統法律方法論研究的危機,幾乎所有的理論都在攻擊傳統的法律解釋方法,如對司法三段論的批判、對法律意義確定性懷疑、對法律解釋客觀性丟棄等。在西方,這種理論上的危機多少會波及法治建設,但并沒有改變法律運行的整體情況。然而在中國,由于我們對當代西方的法學理論與制度極力推崇,這就出現了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危機。一方面中國的法制建設才剛剛起步,法治所需要的思維基礎和職業群體還不成熟,法律人還不能熟練地運用法律方法,基本上是在一種被稱之為跟著感覺走的思維進行著判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在跟著西方法學在痛批傳統的法治建設初期所需要的法律方法論。這是很危險的。原本我們的文化中就沒有堅固的法治理念,尤其是缺乏嚴格法治的精神。在每一個規則之外都有一千個理由不服從規則,幾乎所有的高尚道德和時興的政治大詞都可以成為改變法律含義的理由,如社會效果、和諧社會建設、人民的意志等都是法律需要讓步而不需論證的理由。在缺乏中國問題意識的情況下,我們的理論卻跟著西方法學的主流徑直進入了后現代,開始了對法治以及法律方法論的批判性研究。西方傳統法學的悲劇在于:他們過度講究用形式邏輯的方法解釋法律,以至于使法律的運用出現了僵化;而中國法學的悲劇在于我們文化的骨子里看不起方法,而過度迷戀于自己的整體性理解、對價值優先的固執和對政治影響力的偏愛。方法沒有成為阻止專制與任意的工具,在處理問題的關鍵時刻法治的嚴格多少被淡忘了。
法律方法論研究還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基礎理論研究與部門法研究的分裂問題。實際上現在的部門法研究多半可以歸類到知識論的范疇,通過對法律規范的分析與解釋來解決案件時,部門法學更像法律解釋學,無論是教材還是專著都大體如此。雖然我們的文化是整體性的,但部門法的研究幾乎是在缺失宏觀理論指導下的研究,因為多數部門法幾乎是完整地從西方搬來的學科。中國的學者雖然能從零星觀點中談出自己的看法,但還沒有能力建構自己的體系。部門法學和法理學之間的相互指責與誤解隨處可見。西方法學所講的法學是一種封閉的學科大多指的是對法律的這種部門化的專業性研究。無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生多大的變化,這一學科的基本教義都不發生大的變化,研究者采取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姿態。所以法學的發展與進步是緩慢的,知識量的增長也是被動的。沒有其他學科的逼迫,規范法學幾乎不會自己發展。我國有些部門法學者不僅拒絕來自其他學科的影響,而且也拒絕來自法學基礎理論的反思。很多人公開以不看法哲學、法理學的文章為榮,一些人的口頭禪是“法理學那玩意我們看不懂,也沒有什么用,無非是把簡單的問題搞得越來越復雜”。這種拒絕思維啟迪的做法,強化了法學的封閉性。他們只知道從西方販賣所謂前衛的理論,而對本土學者的反思持蔑視的姿態。法理學確實存在一些故弄玄虛的作品,但也不都是這樣,所以我們沒有必要一概否定,況且即使否定的話也存在鑒別力的問題。實際上一些口出狂言的人士并不見得有多少真才實學,只是充當著口無遮攔的憤青角色。在中國法學中,理論法學與部門法學的分裂還表現在,法理學隊伍中對規范法學研究進行持之以恒研究者較少,政治法理學、法律社會學、價值法學的研究者較多。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有可能與規范法學封閉性和專業性有關系。規范法學的研究需要較強的專業基礎,弄不好在部門法學者面前會說外行話,被扣上法盲的帽子,而規范法學以外的研究則無需像規范法學那樣謹慎,他們可以盡情地不顧現行法律的規定,而進行忘法、枉法的演說。尤其是一些所謂的法哲學,只要你拿著哲學的話語隨便套到法學上幾乎很難找出毛病。我們現在很多研究者奉行的“敢嘲笑法律者,方為真法學家”的觀念是有問題的。這表現出有些學者對法律權威的蔑視,也暴露出法理學、法哲學的研究也像法律語言學一樣存在著兩張皮的現象。懂語言學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語言學,結果搞出來的法律語言學研究使法學家和語言學家都覺得有問題,難以發揮學科交叉的優勢。現在法學研究似乎也是這樣,理論法學越來越哲學化,部門法學越來越專業化。基礎學科的人認為部門法學的研究沒有品位,部門法學的人認為法理學者多是法盲。現在看來,不僅是外部交叉,即使法學內部的交叉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更應該注意學科的交叉,而不能一味地偏向哲學和邏輯學。
三、技術與經驗層面的研究
魏德士在其著作《法理學》德文版“前言”中講到,本世紀法學和法學者的歷史表明:純粹的法律技術對法律和社會是危險的。只有那些對法的基礎和作用方式以及對可能法適用的原因和適用方法后果有所了解并對其思考的人,才能在法律職業的領域內盡到職責的要求。行為人必須知道他們的行為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對此他們必須認識到其行為應遵守法律,此外還必須認識到歷史和社會的聯系。波斯納也談到過此類問題,他說:“自蘇格拉底以來,一直就有些有影響的思想家懷疑,法律推理能否提出某些有理由稱之為‘真理’的東西。”[15]波斯納提到了一本由耶魯大學法學院弗雷德·羅德爾寫的一本書《該你們受罰了,律師們》,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所有從事法律的人都應該定罪,應該用技術專家委員會代替法院。“分析哲學和法律推理在方法上的主要方面是一致的,都主張細致區分和界定,要構建并考察設想的個案決定在邏輯上是否一致,就要把深藏的假定提到表層,要把問題分解成容易駕馭的許多小問題,要精細地發掘對手論點中的隱含義等等。實用主義者認為,分析哲學家和法律推理家都太容易夸大邏輯的領地,太容易把分歧等同于錯誤。并因此過于急切地反駁對立觀點;與此相聯系,分析哲學家和法律推理家就支持這些觀點的經驗性證據興趣不足。實用主義特別懷疑的是,能否用分析哲學的方法及其孿生姊妹法律推理來確立道德責任和法定權利。”[16]
我們相信魏德士所講的是有道理的,因為他說的是純粹的法律技術對法律和社會是危險的。這并不是否定技術與方法的意義。而只是告誡我們在法律運作和解釋的過程中,不能將純粹的技術,而應該把技術,文化經驗、道德價值、歷史與現實和現行法律一起作為理解法律的前見因素,全面地、歷史地、文化地和有價值考量因素來理解和運用法律。結合當前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法律思維水平的現狀,我們認為起碼有一部分人應該集中精力研究法律的技術以及隱含在經驗中的技術。因為方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缺乏的,也是我們現在法制建設所需要的。然而很多學者對此并不以為然。黃宗智對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做過如下評述:“有的人因不滿意識形態而摒棄理論,把自己限定在純經驗與技術性的研究,但是我們相信,理論是任何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世界上沒有能夠壟斷真理的理論,追求絕對真理只能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沼。”[17]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恰恰是黃宗智所說的經驗與技術研究。但這是不是就不牽涉理論或者意識形態了呢? 我看問題沒有那么簡單。社會的焦點和現實問題是躲不掉的,純粹的技術性研究也是堅持不下去的,關鍵是我們該如何在研究中處理這一問題。
第一,研究司法的經驗與技術是法治建設的需要。“當下中國法律理論界與實務界之間的隔膜仍然相當明顯,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之間也往往鑿枘不投,冰火兩重天。”[18]理論聯系實際,實踐聯系理論,基本上都是一廂情愿的呼吁。很多法學家們熱衷于立法活動,至少是從立法的視角觀察問題,對司法實踐理論不是十分關心。“這種雙向的漠然既妨礙了通過具體個案進行試驗從而糾正社會政策錯誤的可能,也導致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無法形成。”[19]理論與社會的隔離,導致了法學家的想法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想法差距越來越大。這雖然成就了法律的專業化研究向深度發展,但也阻礙了法律向公眾意識的滲透,導致了法學家與社會之間的隔膜。雖然有些理論家反對在法律適用和解釋過程中講究純粹的方法與技術,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法治的實現需要方法與技術。法治最基本的含義是對專斷的限制,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程序和規則這些形式化的規定,對規則和程序既不能死板地遵守,但也絕不能丟棄,而應該在尊重其權威的前提下積極使用,使其成為限制專權柵欄。然而在我們新近形成的辯證法影響下,把科學的任務界定成透過現象看本質,本質似乎成了最重要的,形式性的東西都被視為形式主義。從法治的角度看,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我們必須看到,法治幾乎都是通過形式來實現的。沒有形式性法律規范、程序以及運用技術與方法,就不可能有法治的實質性功能的發揮。“依據明確的法律(大前提) ,事實(小前提) ,法官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法律決定(結論、判決) 。這一理論基本是18 ~19 世紀歐洲理性主義的產物。典型代表是罪刑法定。就刑法而言,這一理論的實踐追求盡管有后面分析的不現實,卻很有意義。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權力的濫用和無理擴張,維護了公民的權利,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20]在此法治理念下,圍繞著三段論展開的方法成了各種法律方法的主流。法律方法還只是理論,不是法律的現實,但很多人忽視這一點,因而引發了很多人把邏輯世界的法治當成了現實的法治,造成了一部分人對法律的誤解。如果把邏輯世界當成法律的現實,實際上忽視了法律作為經驗的存在。法律經驗是人們能夠全面理解法律的前見。僅僅看到形式主義的方法論,而沒有理解者對經驗的把握,就會被理性主義的方法所蒙蔽,就會相信法律方法就是法律。“隨著人們從概念分析日益轉向經驗材料,更多地觀察司法行為,積累了大量的數據,還迷信這些觀點,理由就不充分了。看似為了守護法治理念,實際是拒絕現實地理解司法和法官,拒絕那些有助于深入理解司法和法官的新信息和知識。也正因為此,我概括地稱其為法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司法觀。”[21]在波斯納看來,對法條主義之外融入法律的因素是為了超越法律,但我們認為對經驗的把握更主要的是為了更正確地理解法律,法官應該奉行法條主義,但實際上他們卻抵擋不住自己的價值偏好、政治立場的偏見。但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他們也不可能我行我素,職業群體的思維也會限制他們對法律的理解。司法能動主義是一種幾乎本能的思維,而司法克制主義則需要理性的謹慎與謙抑。
第二,研究法律方法的經驗與技術是發展與完善學科的需要。對法學學科來說,如果沒有自身的研究方法,就不可能哪怕是相對獨立的存在;如果沒有應對糾紛的解決方法與技術就會失去實用學科的屬性。賀衛方在一次講座上談到,我國的法學內部的知識與方法還處在一個比較脆弱的狀態,現在又不斷地引進其他學科的方法來拓展本學科的視野,這是件好事情但也存在著一定風險,因為這可能危及法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地位,這是應注意的問題[22]。我們過去的法學教材以及研究傾向重在知識的介紹,對法律的運作方法研究很少,以至于出現了雖然學習掌握很多知識,但實踐動手能力不行的情況,或者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的現象。對歷史敏感的人會意識到,離開歷史、傳統、經驗去研究裁判方法的學者,無論在技術層面論述得多么精巧都無濟于事,法治落后與司法粗糙往往是并發癥。所以我們應該把對經驗與方法的細節研究結合起來[23]。一個學科不應該僅僅是純粹形式化的,還應該是把理性、經驗與歷史結合起來才能比較完善。對經驗的重視實際上就是要把對形式主義方法的過度關注,轉向到對人及其經驗的關注,以彌補法律方法研究主體性的缺失。法律確實不完全是邏輯,法律是社會生活中的法律,是由人的思維和行動構成的活生生的法律。只有在對法律邏輯與經驗的把握中,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和解釋法律。法律方法論與本體論的法學不一樣,應該是以服務司法實踐為中心的理論體系,所以不能僅僅關注理論體系的完善,更主要的是要研究如何幫助法律人在具體的審案中正確地理解和運用法律。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很多成熟或不成熟的經驗,但我們現在的法學作品對此的關注與研究卻很缺乏。蘇力發問:“太多的法學研究脫離了或正在脫離司法實踐,只講正確的原則甚至是法律常識,完全不理解法院和法官的問題,或司法上無法操作。這樣的法學還是法學嗎?”[24]
第三,對經驗與技術的研究是形成良好法治文化、積淀法律智慧的需要。形式主義法學敵視經驗,而實用主義法學則敵視理論。這兩種極端的思維都不利于理論與實踐的融合,不利于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波斯納說:“實用主義者們希望法律更具經驗性,更現實,更符合真實的人們的真實需要。但是如果從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說法律科學者都應該拋棄理論,那也是一個錯誤。事實和理論并不相互對立;科學,包括好的社會科學,都是事實和理論的統一。”[25]正像波斯納所講的,法學研究者應該拋棄糟糕的理論,也應該拋棄糟糕的經驗性研究。但什么是糟糕的理論和糟糕的經驗性研究呢? 近百年來,我們不斷引進西方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但這些都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而產生的,比如,在普通法系“律師會館制度與陪審團制度的精巧結合,習得技藝與生活經驗相得益彰,普通法的發展融合了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專業智慧。”[26]然而,如果我們僅僅從西方學習他們的理論與經驗,就會使中國法學像水上漂浮的浮萍一樣缺少根基。無論我們怎么研究都難以逃脫西方人所設計的框架,只能跟著他們的步伐爬行。因為我們一些人文化先進的標準都是西方人制定的,然而法律甚或是法學都是地方性知識,只有和地方的文化結合起來研究才能找到我們自己的法律文化根基和適應于自身土壤的法律方法。所以這里的經驗主要是指本土的經驗與智慧。外國的經驗與智慧已經通過理論的形式傳輸給我們了。我們要做的是把他們所謂普遍性的東西作為啟示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導向,把我們自己的法律文化和法律思維方法建構好。
第四,對經驗與技術的研究是提升法律方法論回應實踐能力的需要。純粹的邏輯理論可以鍛煉思維能力,但動手能力的提升則需要經驗成分的加入,這里的所謂經驗主要是指法律人的經驗,通過對判例的研究可以獲得更多的司法經驗;通過對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經驗,而這些都使理解能力獲得更大提升。“要善于總結中國的經驗,而不僅是拿外來做法來批評中國。要把那些還不完善的、過于粗陋的甚至有錯的中國經驗提升、概括到理論層面,使之成為具有指導意義的中國司法經驗,進入中國法學理論。這需要開闊的理論視野,求實的態度,更需要法學人對中國法律人的智慧和實踐的根本自信。”[27]我們所學的法律方法不是固定不移的方法, 明白這一點才能解悟方法的真意[28]。面對多種多樣的方法,實際上在運用的時候始終存在著選擇問題,怎樣才能進行恰當地選擇?這不是理論所能決定的,很多法律人遵循的是經驗法則。我們看到,法學院向學生灌輸法律知識、法律技能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判斷力,從而在追求正義中服務公眾。但是,“現在的法學畢業生能夠熟練地掌握后現代文學理論,卻不會起草一份文件。他們學會了像律師那樣思考問題,卻不知道如何依靠它來謀生”[29]。在我看來,出現這種情況與對法律經驗的掌握不夠有聯系。因為關于法律的經驗在大學里面不可能全面展開,這主要是因為在短期內更主要的是學習理論知識。其實理論也都是加工提煉了的經驗,但其中的經驗一般性太多,而個性太少。所以,為提高理解法律的水平,法律的研習者應該有意識地把一般理論與具體經驗結合起來。
注釋:
[1][15][16][25][美]理查德1A1波斯納. 超越法律[M]. 蘇力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原文序) 1, 2, 10, 23.
[2][美]羅伯特1C. 埃里克森.“法律交叉”研究成果的市場[A]. 馮玉軍. 美國法律思想經典[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246.
[3]薩維尼. 薩維尼法學方法論講義與格林筆記[M]. 楊代雄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譯者序言) 1.
[4][英]布萊恩辛普森. 法學的邀請[M]. 范雙飛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219.
[5]鄭玉波. 法諺(二)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81.
[6][7][8][比]R. C. 范1卡內岡. 法官、法學家與法學教授[M]. 薛張敏敏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153, 148, 151.
[9][10]白建軍. 法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導論) 14, 14 - 15.
[11]雷小政. 刑事訴訟法學方法論導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2.
[12]謝暉. 法律哲學[M].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2 - 4.
[13][23]熊靜波. 為法律思維設路標———評《裁判的進路與方法》[EB /OL]. http: / / chinale2galtheory. com /Article _ Show. asp? Article ID =1803. 2009 - 08 - 16.
[14]謝暉. 法律哲學[M].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9.
[17]黃宗智. 為什么要建立一個歷史與社會高等研究所[EB /OL]. http: / / lishiyushehui. cn /.2009 - 08 - 16.
[18][19][26]汪慶華. 迷失的法律職業共同體[J]. 文化縱橫, 2009. (4) : 74, 74, 76.
[20][21][24]蘇力. 經驗地理解法官的思維和行為[A]. [美]波斯納. 法官如何思考[C].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譯序) 1, 3, 14.
[22]賀衛方. 法學方法論的困惑[EB /OL]. http: / / 360doc. com. cn / content/090121 /22 /69630_2379935. html. 2009 - 08 - 16.
[27]蘇力. 法條主義、民意與難辦案件[J]. 中外法學, 2009, (1) : 109.
篇(6)
[關鍵詞]語言游戲;語境規則;法律的內、外在陳述;反科學主義
一、哈特與維特根斯坦:一個思想外史的考察
20世紀的西方哲學發生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就是出現了所謂的哲學的“語言轉向”,語言成為哲學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和概念分析也成為哲學尤其是英美哲學的主要方法,分析哲學在英美哲學界幾乎是一統天下,成為哲學的主流。一般認為,分析哲學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數理邏輯創立后興起的運用現代邏輯方法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以澄清語言意義的哲學活動;第二個階段主要是在二戰后興起的由對日常語言的關注而引發的對日常語言的使用進行描述和概念分析的潮流;第三個階段則是在現代邏輯有了新的發展(如出現了模態邏輯、時態邏輯和道義邏輯等非經典邏輯)以及美國實用主義的復興影響下而出現的哲學研究方法和觀點。其中,第二個階段分析哲學的重心幾乎完全就在英國,并且主要就是在劍橋和牛津兩所著名的大學。在劍橋,主要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為代表;而在牛津,則是以奧斯汀、賴爾和斯特勞森等人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學派,又稱牛津學派。而哈特當時就在牛津大學教授哲學。他敏銳地注意到這股新的哲流,積極主動地融入其中,并成為日常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哈特接替古德哈特任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便將這種新的哲學方法引入到法學研究當中,把先前枯燥乏味的英國法理學改造成為一門真正的法哲學,創立了新分析法學。
而哈特真正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的時間正是后期維特根斯坦思想產生并逐漸成熟的時期,哈特是否與維特根斯坦本人有過接觸,目前并沒有相關記載佐證,但在萊西關于哈特的傳記中,我們可以鉤稽出一些維特根斯坦對哈特影響的證據。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維特根斯坦對于整個牛津學派的影響,如萊西在傳記中提到,雖然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一書直到1953年才出版,但維特根斯坦的課堂筆記《藍皮書》和《棕皮書》的復印本在1940年代中期就已經通過非正式渠道流傳開來,而牛津學派著名的周六晨會就曾對維特根斯坦的這些后期思想進行過多次討論。另外,不少牛津學派的成員都對維特根斯坦極為欽佩,如漢普舍爾記得大部分牛津哲學家都承認維特根斯坦是“這門學科中爆發的一個天才”,斯特勞森也對《哲學研究》贊賞不已,并承認當他第一次讀到《藍皮書》時,“我覺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了思想,盡管它是裸的”。甚至代表牛津這股日常語言哲流的口號“不問意義,只看用法”也是來自維特根斯坦。其次,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對哈特本人也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如哈特在日記中記載了他閱讀《藍皮書》的感受,認為這本書促使他放棄了對某些知識問題復雜性的極端認識,并讓他設法尋找某種更為簡單精致的分析。而后來,他甚至說《哲學研究》是“我們的圣經”。1988年,哈特的忘年交薩默斯到牛津拜訪他時發現,暮年的哈特仍沉迷于維特根斯坦且剛剛讀完麥吉尼斯的維特根斯坦傳并心有戚戚。另外,哈特在1970年代出版了兩本書《邊沁研究文集》和《法理學與哲學論文集》,這兩本書的封面分別是藍色和棕色,其意圖在于響應維特根斯坦的《藍皮書》和《棕皮書》;哈特曾受教于魏斯曼,后者是維也納學派中除石里克外與維特根斯坦關系最為密切的學者,而哈特的得意門生P.M.s.哈克則是著名的維特根斯坦研究專家。
然而,雖然我們鉤稽出了這些維特根斯坦對哈特影響的證據,但總體來說,關于維特根斯坦對哈特直接影響的材料還是比較單薄,尤其是,哈特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確提到維特根斯坦的地方很少。不過,對于本文來說,這并不構成大的問題。英籍匈牙利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提出,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側重于研究思想發展中那種通過客觀觀察可以得見的外部關系,主要是影響一位學者思想的人生經歷和社會事件等,譬如某某思想家讀了某某思想家的著作、某某思想家與某某思想家之間有相互的師承關系,等等,稱之為思想外史;一種側重于研究思想發展中那種不易得見的內部邏輯關系,稱之為思想內史。與外史不同,內史不是從外部觀察得見的,而是需要研究者根據自己的解釋和理解進行理性重構而成的。因此,用這種分類方法來說,本文主要想考察的是思想的內史而不是外史,或者用英國哲學家達米特的話來說,是思想的歷史而不是思想家的歷史。前述對于哈特與維特根斯坦之間的思想外史的考察僅僅是為我們進入思想內史提供一個感性的認識,而后者才是我們下面所要討論的主題所在。本文接下來所要做的,就是從后期維特根斯坦哲學中最具代表性的“語言游戲”說的視角,對哈特法哲學理論中頗具特色的關于法律陳述(尤其是關于內在陳述和外在陳述的區分)的論說作一番解讀,并揭示其中所蘊涵的反科學主義的哲學取向。
二、“語境原則”與法律陳述的語言學方法
“語言游戲”是維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概念,人們甚至有時就把后期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徑直稱為“語言游戲論”,以與作為前期維特根斯坦思想之總結的“語言圖像論”相對應。“語言游戲”這個概念最初是在《藍皮書》中提出來的,意指“孩子剛開始使用語詞時的語言方式”、“語言的原始形式”,后來維特根斯坦對這一概念作了進一步的擴展,即“通過逐步增加新的形式,我們可以從諸種原始形式構造起諸種復雜的形式”,這些復雜的形式也可以稱為“語言游戲”。到后來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賦予了“語言游戲”更為廣泛的意義:“我還將把語言和活動——那些和語言編織成一片的活動——所組成的整體稱作‘語言游戲”’(第一部分,7節)。可見,“語言游戲”主要地是指語言的使用方式。當然,“語言游戲”這個概念作為后期維特根斯坦思想的核心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許多主要論題如意義即使用、遵守規則、生活形式等等都是由“語言游戲”所生發出來的。在筆者看來,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這一思想的核心觀點主要體現為兩點:一是我們不能孤立地理解一個語詞、一個句子,而應當把它們置入它們所賴以存在的語言環境,比如說,我們只有在整個象棋游戲中才能理解什么叫做一個“卒”,一個“兵”,什么叫做“跳馬”,什么叫做“將軍”,在語言哲學中,這樣的一種觀點被稱為“語境原則”(context princi-ple)。二是在于,它讓我們意識到,語言并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符號表征用來描述世界的,它還有很多用途,語言的不同用法就形成了不同種類的語言游戲,在語言哲學中,這可以被稱之為語言游戲多樣性論題(diversity thesis of languagegame)。我們下面的討論就將緊緊圍繞這“語言游戲”的這兩個思想內涵展開。在這一部分,我們主要討論語境原則在哈特法哲學理論中的運用,而在下面兩部分,將重點討論語言游戲多樣性在哈特法哲學理論中的體現及其所蘊含的哲學傾向。
“語言游戲”這一概念意味著我們要理解一個句子,必須將其放在其所在的語言游戲當中。這涉及如何確定意義的基本單位的問題。在近代,洛克、休謨、密爾等人大多把詞看做意義的基本單位,但邊沁已開始把句子看做意義的基本單位。到了現代,弗雷格提出了著名的“語境原則”,主張語詞只有在句子中才能確定其意義,這也就意味著意義的基本單位是句子而不是詞。早期維特根斯坦接受了弗雷格的這一原則,認為“只有命題才有意義;只有在命題的聯系關系中名稱才有指謂。”而到了后期,維特根斯坦更進一步把語言游戲看做意義的基本單位,“在他看來,無論詞或語句都沒有獨立的意義,它們只有在語言游戲中才能獲得意義,詞和語句的意義都是在語言游戲中確定的。”維特根斯坦舉例說:
設想一個語言游戲:B根據A的提問向他報告一堆板石或方石的數目,或堆放在某處的石料的顏色和形狀。——某個報告可能是“五塊板石”。那么,“五塊板石”的報告或斷言和“五塊板石!”的命令之間的區別是什么呢?區別在于說這些話在語言游戲里所扮演的角色。(第一部分,21節)
也就是說,同樣一個表達式,在不同的語言游戲中就具有不同的意義,在命令的語言游戲當中,“五塊板石”意味著“給我拿五塊板石來”,而在報告的語言游戲當中,“五塊板石”則意味著“這兒有五塊板石”。而我們要弄清表達式到底說的是什么意思,首先就必須知道我們正在玩的是什么語言游戲。
哈特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他的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就職論文《法理學中的定義與理論》中,他批評了那種孤立地考察法律語詞和法律語句的做法,強調要從整體語境出發來理解法律語詞和法律語句。當然,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確地說自己的這種觀點是來自于邊沁:
很久以前,邊沁就發表了他的告誡,指出法律語言需要一種獨特的闡釋方法……他說,我們一定不能把這些詞匯拆開了、孤立地去看,而應把它們放回到它們的扮演獨特角色的句子中去,從而進行一個整體的考量。我們切勿僅僅去考慮詞匯“權利(right)”,而應考慮的是句子“你擁有一項權利”;也切勿僅僅去考慮詞匯“國家”而應考慮的是“他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成員或一名官員”。
而在該文其后的論述中,哈特對于這一語境原則的運用有明顯擴大的趨向,即他不僅認為法律詞匯必須放在一個句子中來進行考察,而且還認為包含這些法律詞匯的句子也必須在整個法律制度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他在探討法人概念的時候引用了梅特蘭曾經舉過的一個例子:假設有一個國家叫做納斯夸米亞(Nusquamia),和許多國家一樣,它也負債累累,你正好也是它的債主之一,它欠你1000英鎊。那么,當納斯夸米亞欠你1000英鎊的時候,到底是誰欠你1000英鎊?哈特認為這種問法本身就是成問題的,因為唯一的答案就是再次重申:納斯夸米亞。而這等于什么都沒說。正確的方法則是把“納斯夸米亞欠你1000英鎊”這個陳述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并且可能要用如下方式來描述它:
1.這里,在納斯夸米亞的版圖范圍內有一套正在起作用的法律體制;根據這個體制的法律的規定,遵循特定條件的特定人,可以為某種目的而被授權去接受一筆款項,以及為其他行為。這類似于那些按照要求在私人個體之間簽訂借款合同的人們的行為。
2.當這些人去為這些行為時,特定的后果就會接踵而至,這些后果與那些由私人間類似行為所具有的后果非常相像。它們包括法律所規定的人從法律所規定的那些資金中償還所欠款項的責任。
3.“納斯夸米亞人欠你1000英鎊”的表述并不能說明存在這些規則,也不能說明存在這些情況;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當這些規則存在時,這個表述就是正確的,并且會被用于在特殊個案中根據這些規則推出一個法律結論來。
簡單地說,就是一個法律陳述必須從其所在的法律體制中獲得它的意義。而這樣一套法律體制也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種語言游戲,借用維特根斯坦的話來說,就是由法律語言和法律活動所編織成的一個整體,任何一個法律陳述都只有在這樣一種語言游戲中才能夠被人們所理解。
三、“語言游戲”的多樣性與法律的內、外在陳述的關聯
如前所說,維特根斯坦提出“語言游戲”這個概念是為說明語言活動的多樣性,以批評那種試圖以一種語言游戲來說明其他語言游戲的簡單化、單一化的傾向。從多樣中把握統一自古希臘以來就是哲學的一個重要主題,也是哲學探究的一個重要目的。維特根斯坦在其早期哲學思想中也秉持這樣一種單一主義的觀點,并得出了“語言圖像論”的結論,即把語言看做對于現實世界的摹寫,語言的功能就在于反映世界、描畫現實,用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觀點來看,這也就意味著,任何語言活動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種唯一的“語言游戲”。而后期維特根斯坦對于前期維特根斯坦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對這種單一語言游戲觀的否定開始的。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語言游戲的多樣性。例如:
下達命令,以及服從命令——
按照一個對象的外觀來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來描述它——
根據描述(繪圖)構造一個對象——報道一個事件——
對這個事件的經過作出推測——
提出及檢驗一種假設——
用圖表表示一個實驗的結果——
編故事;讀故事——
演戲——
唱歌——
猜謎——
編笑話;講笑話——
解一道應用算術題——
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
請求、感謝、謾罵、問候、祈禱。(第一部分,23節)
在這些例子的結尾,維特根斯坦特意說道:“把多種多樣的語言工具及對語言工具的多種多樣的用法,把語詞和句子的多種多樣的種類同邏輯學家們對語言結構所說的比較一下,那是很有意思的(包括《邏輯哲學論》的作者在內)。”這也就是說,后期維特根斯坦對于包括他(前期)在內的“邏輯學家們”對于語言的簡單化認識予以了否定,而這種否定的目的在于揭示人類思維中存在的這樣一個問題,即“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我們對語言形式本身的誤解,最常見的是把不同的語言游戲混淆起來,或者認為某種語言游戲是唯一合法的。”
在哈特《法律的概念》一書中,我們也能常常碰到與維特根斯坦關于語言游戲多樣性的論述極為相似的觀點。在本文中,筆者主要從法律陳述的角度來對此作一比較,這也就是哈特非常著名的關于法律的“內在陳述”和“外在陳述”之分。
哈特是從“義務”這一觀念出發運用他嫻熟的語言分析技巧逐步得出這一著名區分的。哈特認為,說某人被迫去做某事(be obliged to……)與說某人有義務做某事(have an obligationto……)這兩種陳述是不同的。前者通常是關于行為由已作出的確信和動機的心理學陳述,后者則不是。因為前者所說的“確信”和“動機”并不一定是后者作出陳述所必需的,并且,我們說某人“被迫”做某事通常是他實際上已這樣做了,而說某人“有義務”做某事與他是否實際上了做了并沒什么關聯。把二者等同將導致以心理學的感情術語誤釋規則的重要的內在方面。也就是說,法律作為一種語言游戲不同于其他種類的語言游戲,為了強求表達一致而把它與其他語言游戲相混淆不僅會產生理解上的混亂,而且會使我們對法律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征視而不見。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規則的“內在方面”。規則的“內在方面”是哈特在分析社會規則與習慣之間的區別的時候所提出的一個概念。他認為,從外觀上看,社會規則與習慣都是觀察者能夠記錄下來的有規律的統一行為,但顯而易見,社會規則與習慣是不同的,兩者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如果一個社會的規則要存在的話,至少有某些人必須將有關行為看做該群體作為整體應遵循的一般標準”,這就是規則的“內在方面”,而習慣的存在則無須這樣一個內在方面。正是因為規則有這樣的一個“內在方面”,這就產生了一些關于規則的特殊表達,就像維特根斯坦慣常所做的那樣,哈特以國際象棋為例對此進行說明:
國際象棋棋手們不僅有以同樣方式移動王后的類似的習慣,……而且……他們將此行為方式看做所有參賽者的一個標準。每個棋手不僅本人以一定方式移動王后,而且對所有以那種方式移動王后的行為的適當性“有看法”。這些看法在偏離行為現實存在或出現預兆時,體現為對他人的批評和對他人提出服從要求;在接受別人的批評和要求時,體現為接受這種批評和要求的正當性。為了表達這種批評、要求和承認,一系列“規范性”語言被人們所采用。如“我(你)不應該那樣移動王后”。“我(你)必須那樣移動”,“那樣是對的”.“那樣是錯的”。
而在此類表達上常常發生的錯誤就在于:規則的內在方面經常被曲解為與外部可見的身體行動相對照的純粹“感情”問題。哈特對此論述道:
毫無疑問,在規則被社會群體普遍接受,并一般受到社會批評和要求遵守的壓力所支持的地方,個人可能經常有類似于受限制或被強制那種心理上的體驗。當他們說他們“感到受約束”而以某種方式行為時,他們可能實際上指的就是這些體驗。但對于“有約束力的”規則的存在來說,這種感受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充足的。說人們接受某些規則但從未有過受強制的感受,這種說法是不矛盾的。所必需的是,對作為共同行為標準的某些行為模式應存在著審慎的、沉思的態度,而且這種態度本身應表現在批評(包括自我批評)、要求服從以及對這種批評、要求之正當性的承認之中。所有的批評、要求和接受都在“應當”、“必須”、“應該”、“正確的”、“錯誤的”等規范性語詞中發現它們特有的表達。
而“義務”觀念作為這樣一種“特有的表達”,正是從規則的“內在方面”看待自己和他人行為的觀念,哈特稱這樣一種站在“接受規則并以此作為指導的一個群體成員”立場上所具有的觀點為“內在觀點”,與之相對應的是“僅僅作為一個本人并不接受這些規則的觀察者”所具有的觀點,即“外在觀點”。而從內在觀點出發所作的陳述他就稱之為“內在陳述”,從外在觀點出發所作的陳述就稱之為“外在陳述”。顯而易見,“內在陳述”是法律這種“語言游戲”所特有的表達,也是我們理解法律這種社會現象的關鍵所在。否則,我們將無法區分規則與單純習慣甚至是偶然的行為一致性,也無法獲得規則的觀念。
哈特似乎對自己提出的這兩種陳述的區分頗為自得,緊接著就運用這一理論在法理學中爭論不休的法律的“效力”與“實效”問題上小試牛刀。他認為,只要清楚地認識到內在陳述與外在陳述的區分,那么有關法律“效力”觀念的許多模糊不清之處就可迎刃而解。在他看來,與“效力”有關的陳述屬于內在陳述,因為“某一個特定規則是有效力的這種陳述意味著它符合承認規則所提供的一切標準。”而與“實效”有關的陳述屬于外在陳述,它“意指一個要求某種行為的法律規則多半被遵守的事實”。這也就是說,關于“效力”的陳述和關于“實效”的陳述是處于兩種不同的語言游戲之中,“效力”和“實效”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更不能把兩者相混同或企圖用其中的一個來涵蓋另一個。而哈特運用內在陳述和外在陳述的理論來區分“效力”和“實效”的一個重要目的,就在于批駁法律現實主義的預測論:即斷言一個規則的效力就是預言它將由法院或某一其他官方的行為強制實施。他認為,預測論表面上的合理性在于:對旁觀者可能記錄下來的事實——這一制度一般地是有實效的并可能繼續有效——所作的外在陳述的真實性,通常是接受規則并對義務或效力作出內在陳述的任何人的前提。但它卻忽視了內在陳述的特殊性,把它作為關于官員行為的外在陳述。這也就混淆了兩種不同的語言游戲,從而導致法律理解上的謬誤。譬如,很明顯的是,當官員在司法判決中作出關于法律規則的效力的陳述時,他顯然不是在預言他自己或其他官員的行為,而是表明他作出這個判決的理由。
四、法哲學中的反科學主義意蘊
根據前一部分的分析,法律現實主義的預測論犯了用外在陳述抹殺內在陳述的毛病。那么究竟是什么動機驅使他們這樣做的呢?我們前面已經提到,“語言游戲”這個理論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治療人類思維中單一主義這種理性疾患。而這種理性疾患自近代至現代以來最突出地表現為一種科學主義的思維模式,即在近現代科學迅猛發展、科學觀念深入人心以后,人們往往傾向于用科學的語言尤其是用描述經驗事實的那種所謂的“客觀中立”的語言來解釋一切現象——無論是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從而希望對一切現象都做出所謂的“客觀的”因而也是“科學的”說明。這也就導致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出現了一股十分強大的科學主義傾向,希望將自然科學中的成功也搬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來,從而使人文社會科學也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客觀。法學領域自不例外。實證法學可以說是這種法學科學化的典型代表。邊沁、奧斯丁區分立法學與法理學,其目的就是為了把法律作為一個客觀對象來進行研究,他們開創的分析法學因而也被他們視為一種關于法律的科學。甚至法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哲學中脫離出來也正是始自奧斯丁。凱爾森也明確聲稱自己的純粹法學是一門法律科學而非法律政治學,他的法學之所以是純粹的就是因為他要把法律科學從其他不相干的因素(諸如心理學的、社會學的、倫理學的以及政治學的因素)中解放出來,他并且認為這是他的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他們的這種科學傾向就在他們具體的法學概念和法學觀點中體現出來了。無論是奧斯丁的(以威脅為后盾的)“命令說”還是凱爾森把真正的法律僅僅看成是“下達給官員的實施制裁的有條件的命令”,都是一種用描述經驗事實的術語來闡釋法律現象的企圖。對于這一企圖,哈特一針見血地評論道:
認為法律就是命令這一著名的理論只是一個更為寬泛也更富野心的主張的一部分。奧斯丁說命令是“理解法理學科學與道德規范的關鍵,”當代一些以“強制性”或“規定性”的術語去闡述道德評判的努力就是這種極富野心的主張的遙遠回響。
然而,豈止是實證法學有這樣的“野心”,社會學法學——包括通常被歸于其中的法律現實主義——同樣也具有這樣的“野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畢克斯有頗為精到的論述:
要將法律研究立基于“科學的”——客觀的,不合偏見而純粹的——基礎之上的努力,促使許多早期的法律實證主義者,嘗試去創建一種理解法律行為與法律概念的嚴格的經驗主義方法,由此將其理解為過去的、當前的以及將來種種因素的應變量。法律理論中的這類探討,可以在那些要為社會科學研究探索一種“科學”方法的更為廣博的研究中見到,這些方法當能與“硬科學”(例如物理學與化學)所運用的方法相提并論,由此,理論就將只以對事件的“客觀”觀察作為基礎,這些事件則可以輕易復制或者得到其他理論家的確認(用稍稍技術一點的話說,就是法律的“規范性內涵”被化約成了“經驗性內容”)。因此,法律規則也就根據公民過去遵守法律的傾向、立法者對于特定種類語言的運用、將來施加制裁的可能性、對法官將會如何判案所作的預期等等因素來進行分析了。
可見,以“預測論”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正是——相比實證法學——“研究探索一種‘科學’方法的更為廣博的研究”。從預測論的表述我們就能很明顯地看出這一點:說法律實際上就意味著當某人違反一個規則時,我們可以預期法院會做出何種處理。這種說法和我們平常說“天空烏云密布,估計快下雨了”并無二致,因為我們只是對經驗事實有所陳說,這也正是外部陳述的特征所在。而導致采納這種言說方式的,正是那種科學主義的理論傾向和思維模式,用哈特對阿爾夫-羅斯的評論來說就是:在法律現實主義者看來,“能夠表征法律并且使之適合現性法律科學的特征的唯一適宜的方法,就是一個具有經驗科學之諸種陳述的結構與邏輯的方法。”
篇(7)
上述現象充斥在中國人文社科的各個領域,法學研究也不例外,并且表現得更為突出。在被稱為法學骨干學科的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商法學、國際法學甚至刑法學中,如果我們檢索其主要概念和原理,幾乎很少有詞匯不是來自歐美、日本等國。即使是被稱為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學科,也基本上是用現代西方法學的術語在闡釋古代的制度和先人的思想。可以說,中國法學近百年來無可挽回地已經西化了。這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所以,當我國的許多法學家出訪他國,在介紹中國法學研究現狀的時候感覺到十分茫然,因為,代表我國法學研究先進水平的許多“成果”原本就是西方的東西。這其中,令外國人理解不了的也許是被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法學那一部分。從解釋學的角度看,西方法學傳入中國不會原汁原味,中國人在理解西方文化時肯定會帶有十分鮮明的中國印記。當然,這樣敘說中國法學研究史也許并不可取,因為這很容易使讀者誤以為我們在為失落的中國文化唱挽歌。其實,在這里我們僅想揭示一下這樣的現實,目前關于中國法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立足于中國,近百年的法學研究是在追趕西方的背景下定位的。當然,這種敘說并不包含對以西方法學為參照系進行研究的贊美或批評。我們承認中國法學的進步與西方的法學的涌入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大學法學院課堂上所傳授的知識基本上都是用漢字表述的西方法學。目前關于中國法學的研究不這樣做也許不行,因為近百年來我國的法律制度從形式到內容基本上都西方化了。現在高素質法律人已基本上習慣于用西方人的法學原理分析、解釋發生在中國的案件。雖然我們也常聽說,封建的法律意識還禁錮許多人的頭腦,但我們看到,在西方文化“話語霸權”的影響中,這些人的思想很難成為研究的主流,甚至根本無法進入學術研究者的行列。
評介學習西方法律學術無疑會縮短中國法學與西方法學的距離,會增進中西文化交流,也會增強中國文化的自生能力。但像任何事物都可能有其副面作用一樣,后進學人對法學研究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定位也可能會影響中國法學的進展。有學者甚至提出這樣的疑問,究竟有沒有“中國法學”?因為他們感覺到,目前被稱為中國法學的東西實際上是“西方法學在中國”。關于“中國法學”的沉思給提出了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法學界首先應解決什么是“中國法學”的問題。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是不是西方法學的概念、原理由中國人加以傳播就是“中國法學”呢?是不是西方法學的漢字化就是中國法學呢?這是值得法學學人沉思的問題。我認為解決“中國法學”的問題,首先應對中國的法學研究進行定位,而這一定位涉及到我們對西方法學的態度,涉及到我們的研究立場、內容、方法及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法律的問題。
對西方法學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不僅是中西方法律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中國法學進步所必須經歷的階段。我們認為對西方法學的評介及其研究只能提升我國法學研究者的視域,甚或提高我們用西方法學知識、原理理解我國法律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應該說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問題在于,著眼于西方立場而進行研究的“中國法學”,缺乏解決中國問題的能力,難以真正地融入中國社會。所以,我們認為在西方法學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以后,起碼應有部分學者專注于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我們應把研究的視野定位于中國。只有這樣才能使有關“中國法學”的研究有所進步,中國法學的研究者不僅僅是西方法學的傳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