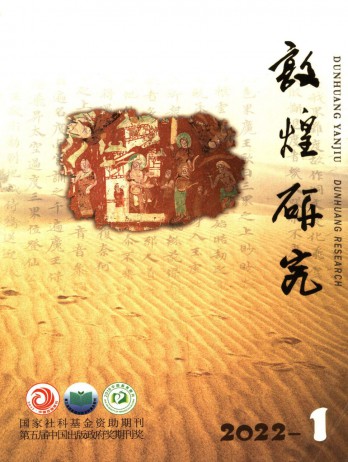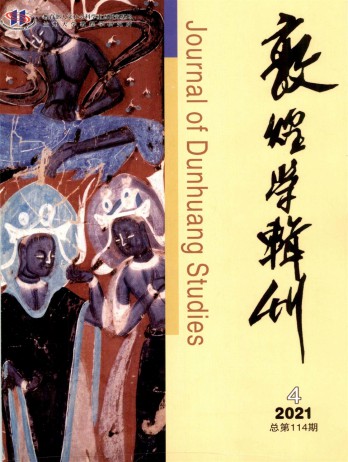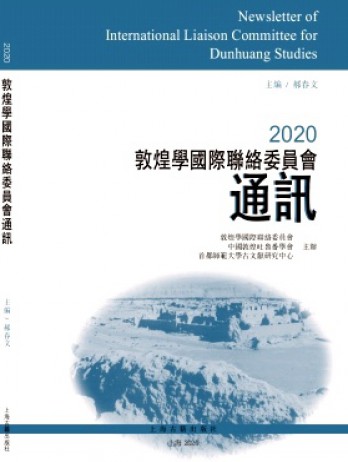敦煌文化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02-28 07:55:36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敦煌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在當今敦煌學研究欣欣向榮、深入發展之際,《敦煌研究》期刊迎來了三十周年生日。古人云“三十而立”,我們希望《敦煌研究》這份學術期刊在廣大讀者和作者的關心愛護下,永遠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回顧《敦煌研究》醞釀創辦之時,正是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寬松環境逐漸形成,中國學者振奮精神,決心奮起直追,把敦煌學研究搞上去。當時,地處西北沙漠、長年守護著敦煌石窟的研究者們深感重任在身。隨著全國敦煌學研究逐漸恢復發展,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紛紛撰寫論文,把多年來對敦煌石窟及文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整理出來。這些成果先后刊登在一些書刊上,如日本平凡社和文物出版社合出的《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就匯集了本所大部分研究人員的成果,此外本所的研究人員還編輯了論文集《敦煌研究文集》。為了盡快地刊布這些成果,并強有力地推動國內敦煌學的發展,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段文杰先生敏銳地看到敦煌學發展的契機,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始籌備創辦《敦煌研究》期刊,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試刊第一期和第二期,頓時,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作為主編的段文杰先生在發刊詞中回顧了七十年來敦煌學發展的歷程,認為必須改變我國敦煌學在國際學術進程中的落后狀況,提出以《敦煌研究》作為敦煌學研究的學術園地,促進敦煌學發展的辦刊宗旨,體現了在國際領域展開敦煌學術研究的遠見卓識。《敦煌研究》從創辦之初,就立足敦煌,放眼世界。一方面集中本所的研究力量,發表新成果和高質量的論文;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征集國內外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的成果,使本刊發表的成果保持在較高的學術水準,成為敦煌學界及相關學科的重要參考。
在試辦《敦煌研究》期刊階段,主要交由甘肅人民出版社作為圖書出版,以書代刊,編輯人員也不固定。李永寧、施萍亭、馬德、林家平等先生均為《敦煌研究》的編輯出版做出了貢獻。隨著《敦煌研究》編輯出版的需要,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編輯室。1983年《敦煌研究》正式獲得甘肅省期刊登記證,并出版了創刊號。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原編輯室也改為編輯部,梁尉英先生先被任命為副主任,1991年為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為止,梁尉英先生一直負責編輯部的工作,為《敦煌研究》期刊的編輯出版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1986年《敦煌研究》定期發行以后,在編輯方面逐漸走向正規化。1988年以后,根據敦煌學研究的特點,設立了一些欄目,如“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石窟保護”、“河西史地”、“敦煌遺書”、“敦煌語言文學”等欄目逐漸成為了本刊的特色欄目。而在其后的十多年中,又根據來稿情況,不時增加一些欄目,如“敦煌民俗”、“敦煌樂舞”、“回鶻問題研究”、“敦煌體育”、“敦煌科技”等新欄目。期刊欄目的分類,并不是嚴格意義的圖書資料的分類,主要是從來稿和研究主題特色出發,通過這樣的歸類給讀者提供一個便捷的路徑,為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提供可以查詢的通道。同時也樹立本刊的一種形象特色。多年來,“石窟考古”與“石窟藝術”欄目中不僅發表了有關敦煌石窟的重要成果,而且還涵蓋了全國各地石窟及佛教藝術研究的成果,成為中國石窟考古與佛教藝術研究的重要參考。而“石窟保護”欄目所發表的文章也不限于敦煌石窟,而擴展到全國各地石窟、寺院、遺址等方面的文物保護研究,在文物保護科學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可以說《敦煌研究》的出版,不僅推動了敦煌學的發展,而且對很多相關學科都起到了帶動的作用。
段文杰院長作為《敦煌研究》的主編,對編輯部的建設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首先是注重人才的引進與培養,編輯部成立后的短短幾年,編輯人員從無到有,到1986年,《敦煌研究》開始作為季刊定期發行時,編輯部已有編輯人員6人。由于編輯人員大多沒有編輯出版經驗,段文杰先生決定派人到出版社學習編輯知識和技能,在文物出版社黃文昆先生和中華書局《文史知識》編輯部柴劍虹先生的大力協助下,編輯部先后派人到文物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實習,提高了編輯人員在圖書和期刊編輯方面的實際能力。此后,編輯部雖不斷有人調離,但也不斷有新進人員,編輯隊伍穩步壯大。
編輯部的工作人員不僅要編輯《敦煌研究》期刊,還有圖書編輯的任務。自編輯部成立以來,經由編輯部編輯而出版的圖書總計65種(包括本院的學術著作、翻譯著作以及敦煌學相關的普及讀物),其中大多數是最近十年間出版。除了編輯整理本院的學術成果外,近年來,為了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編輯部還有計劃地組稿,編輯一些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讀物,把敦煌學的學術成果轉化為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文化知識,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在承擔編輯任務的同時,編輯人員還分別承擔著各種學術研究課題,學者兼編輯是本刊編輯部的特色。多年來,編輯部的工作人員不斷發表學術論文,出版學術專著,不少編輯已成為學術界較有影響的學者。對學術的深入研究,使編輯人員對來稿有較強的鑒別能力。同時,由于身為學者,也更容易與學者交流,從而加強和提高編輯出版的質量。但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也不忽視編輯專業技能的提高,近年來,根據期刊出版的需要,編輯部每年都派人參加不同形式的編輯培訓班,以提高編輯素質,并了解全國期刊發展的形勢。
三十年來,《敦煌研究》出版了正刊136期,特刊7期(截至2012年底),共發表敦煌學及相關專業論文3118篇,其中包括石窟藝術與考古研究方面的論文925篇,敦煌相關歷史文獻研究論文1167篇,石窟保護科學論文310篇,以及相關信息資料稿件716篇。涉及敦煌學的所有專業,在敦煌石窟及全國各地石窟考古和藝術研究、石窟保護科學研究等方面的論文成為本刊最具特色的學科領域。同時敦煌文獻研究方面也有許多不容忽視的成果。本刊登載的論文每年都有不少被轉載、被引用,或被翻譯成外文在國外發表。還有相當一部分論文在全國以及各地的社科成果評獎中獲獎。《敦煌研究》不僅在世界敦煌學術界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且對于相關的學科也產生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敦煌研究》自創辦以來,得到了國內外敦煌學界的廣大學者的大力支持和關懷,也得到了敦煌研究院和上級主管部門的鼎力支持和幫助,使我們的工作不斷取得成績。1994年,在甘肅省首屆社科期刊評級中《敦煌研究》被評為“甘肅省一級期刊”。1995年,《敦煌研究》榮獲國家新聞出版署評選的“全國優秀社科學術理論期刊獎”。1997年,榮獲首屆中國期刊獎。1999年被評為“甘肅省一級名牌期刊”。1999年,本刊再度榮獲“全國優秀社科期刊獎”并被評為“第二屆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刊”。2002年《敦煌研究》進入中國期刊方陣“高知名度高學術水平”的“雙高”期刊之列。2005年,榮獲“第三屆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獎”。2007年榮獲“中國北方十佳期刊獎”。2008年被評為“甘肅省品牌期刊”。2012年本刊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
三十年的歷程中,值得欣慰的是《敦煌研究》始終堅持學術質量第一的標準,這是從前任主編段文杰到現任主編樊錦詩都堅持的。即使是在敦煌研究院最艱苦的時期,也要保證辦刊的經費,保證發表文章的學者有稿酬,堅決反對向作者收取費用。也決不因為社會上的某些需求而降低標準,從而保證了刊物的學術品位。
2006年,在《敦煌研究》出版100期的紀念專號上,主編樊錦詩回顧了二十多年來《敦煌研究》發展的歷程,指出:
今后的敦煌學研究必將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朝著更深入、更細密、更全面的方向發展。多學科交叉的研究,不同專業學者間的合作研究,古代文代藝術與當今社會文化藝術發展相結的研究,文化遺產的綜合保護管理研究等等將成為學術發展的大趨勢。同時隨著國際性敦煌學研究聯絡組織的成立,國際學術交往的頻繁發展,國內外學術信息的溝通將會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何時候,敦煌學必將在世界人文科學研究領域閃耀出新的光芒。《敦煌研究》期刊也將在新的時代擔負起歷史的重任,為新時代的敦煌學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篇(2)
2014年1月21日,將值段文杰先生仙逝三周年紀念日。本刊特刊發段先生兩篇遺作及一組紀念文章,以緬懷一代敦煌學大師。
段文杰先生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綿陽。194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從杭州遷往重慶的國立藝專五年制國畫科,師從林風眠、呂鳳子、潘天壽、陳之佛、李可染、黎雄才等先生學習中國畫。由于學習勤奮努力,在繪畫基本功和文史知識方面都打下了堅實基礎。1944年,在重慶觀看了張大千先生臨摹的敦煌壁畫展覽,被敦煌藝術所吸引,同時也了解到地處邊遠荒漠的敦煌石窟藝術遺產需要有識之士去保護和研究,就下決心要擔當一名志愿者。他的想法得到林風眠、潘天壽、陳之佛等先生和同學們的支持。1945年畢業后,幾經曲折,義無反顧,于1946年到達敦煌莫高窟。在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從事敦煌藝術保護和研究工作,并擔任美術組組長和考古組代組長。1950年后,歷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組長、所長、副研究員。1957年后,遭錯誤處理。1962年,經上級組織甄別,恢復原有職務和待遇。“”期間又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農村勞動。1972年,回所工作。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長。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長。1998年以后,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段文杰先生是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曾擔任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甘肅敦煌學會會長、甘肅省對外交流協會名譽會長、甘肅省國際傳播交流協會名譽理事長、甘肅省社科聯副主席、甘肅省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等多種社會職務。1986年,被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聘為名譽教授。1993年,被日本創價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還被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授予名譽研究員。曾獲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學術獎、東京富士美術館最高榮譽獎。
篇(3)
【關鍵詞】 敦煌藝術 美學 中國美學史
一 問題與思考
1.1 重寫中國美學史
自20世紀末以來,我們處于一個社會文化的轉型時期。在此歷史的關頭,曾經的一切文明成果在給我們以啟示的同時,也或隱或顯地昭示出某種新的文化癥候,那就是——重寫!我們更加認同李學勤先生在《世紀之交與中國學術史研究》一文中的論斷,他說:
在世紀交替之際,總結過去,啟示未來,本是學術史發展的一條規律……20世紀的考古發現所引起的學術意義至少在如下三個方面值得我們去討論。第一,考古發現改變了傳統研究方法與學術觀念……第二,考古學改變了有關中華古文明狹隘認識。……第三,大量簡帛佚輯的出現,證明中國學術史必須重寫。…… 多學科相結合、從多角度入手,有利于揭示歷史的本相。
中國美學事實上也面臨這一挑戰。我們試圖引入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旨在對中國美學施以盡可能還原,將“歷史”與“歷史學”書寫區分開來,以新的實證眼光,佐以理性分析和審美感悟去重新書寫中國美學史。
首先,中國美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并非出自一種理性的自覺,它伴隨著20世紀初“文化維新”運動從東洋日本被介紹進中國,源自德人鮑姆嘉通的“感性學”被修正為“美學”,并為國人所逐漸認識而廣泛接受。嗣后,經過一個多世紀的不斷譯介和學術建設,中國美學已日漸成熟,幾度“美學熱”風靡中國大陸。我們認為,中國美學的確立不僅需要借助于外來眼光作參考,更要確立自身品格,而這無疑應當從該文化現象之所從出的發源地去找,那就是——中華文化的本土資源!已故考古學宗師蘇秉琦先生曾精要地概括了泱泱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色,“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1】。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自成系統的幾大悠久文明之一,迄今為止,這一文化體系仍然在歷史中前行,未曾出現過中斷。如果說,“美學”的定義之所以至今沒能統一下來,而不能貿然用西方的固有概念來框定中土學科的話,那么,其間至少有兩點是不言自明的:其一,中華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審美理念,這一理念滲透在中華文化的方方面面,從而與西方的美學觀形成一種雙峰并峙的獨特景觀,形成了人類審美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其二,雖然不同的審美觀導致對“美學”的理解歧義,但是,作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其間應該有一些共通的特征,譬如說:追求精神境界的創化意識與和諧的美好情感等。因此,宗教和藝術勢必成為人們交流的最佳思想武器。
其次,對于日漸走進“地球村”的當代人來說,文化的趨同性愈是明顯,人們內心深處追求“文化個性”的焦灼感便愈加強烈。文化的多元碰撞在產生新的文化“寧馨兒”的同時,文化的“返祖現象”也愈加神秘。“趨同”不是為了“同化”,“碰撞” 是為了激起新的“火花”。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人類的族性差異不會因為彼此的靠近而消失殆盡。中國美學的歷史使命正在于從本土資源出發,從而確立自身的獨特品格,而不應該惟他者馬首是瞻,在合理汲取異域文化的同時,更新并確立自己的品性。
再次,從文化淵源上看,源自遠古時期的“龍飛鳳舞”乃至“百獸率舞”的文化因子在一以貫之的文化道統中得到傳承,其典型事例莫過于“敦煌學”的興起與“敦煌藝術”的出場。中國美學將佛教藝術的典型代表——敦煌藝術——納入考察和研究的視野,無疑是中國美學重建(或“重寫”)的必然,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之雙重意義。學科更新不僅需要新的方法論,更應該具有新的學術視野、問題意識和戰略眼光。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既是理論的認知,亦是實踐的要求。“與時俱進”不是拋棄歷史,正是要融入傳統之中的“時代性”;“學術創新”不是割斷既有的文化臍帶,否則即會失血而喪失生命力。
最后,從敦煌學研究總體布局看,缺少一門重要的分支學科——敦煌美學。季羨林先生主編并于上世紀末出版的《敦煌學大辭典》是當下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謂體大思精,舉凡一個世紀的所有學術成果均一一作出事無俱細的介紹,可惟獨少了一條“敦煌美學”。這難道是一種偶然?雖然曾經有學者制訂過類似于“敦煌學研究系統”的學科總表,但自覺而成系統的研究成果與蔚成風潮的敦煌學研究相比,少得幾乎不成比例。難怪季羨林先生幾乎無法在其主編的皇皇巨著《敦煌學大辭典》中列一條目,因為可堪介紹的研究成果實在太少。
質言之,一種自覺的﹑介于敦煌學與美學、藝術學之間的分支學科——敦煌美學一直付之闕如,現在是該建立的時候了。從當下場景來講,過去沒有出現是有歷史原因的,而今天我們呼喚其出場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我們的理由建立在下述幾點基礎之上:
第一,一門學科的出現及臻成氣候需要相關學科的成熟和學術支撐,而作為敦煌美學的主干學科——敦煌學已經誕生了一個世紀【2】,“敦煌學”一詞【3】的正式確立也近八十年之久。借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先生的話來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現在敦煌學已濅假成為世界‘顯學’。” 【4】
第二,與敦煌美學緊密相關的藝術學學科不僅已經建立,且基本理順了學科關系,這就為敦煌藝術的整體研究提供了學科發展的動力和學術支撐。
第三,敦煌學的基礎性研究(如研究范圍、歷史分期、洞窟斷代定名、文獻歸類整理等)也基本完成,從而為敦煌美學的順利開展基本掃清了障礙。
第四,多學科交叉性研究不僅是當下學科建設走向縱深的標志和趨勢,而且已經在敦煌學界取得一定的實績,如考古圖像學、考古類型學、音樂與舞蹈考古學、文化人類學等引入即是明證。
第五,在此文化轉型的新時期,無論是美學還是藝術學、敦煌學研究都面臨著深化和開拓眼光,從而發現新的學科增長點諸問題。惟其如此,更需要一門敦煌美學來實施互動式發展。
第六,敦煌學中一些基本問題和重大問題的解決為敦煌美學的建立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關于敦煌藝術各方面工作也基本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礎,尤其是對于歷史上曾經令人困惑的某些難題大體具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和評價。此外,隨著對中國審美文化專題研究的推進,尤其是針對華夏藝術美學精神的深入思考,敦煌壁畫及其樂舞藝術等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范例。我們可望通過對敦煌藝術的深入研究來進一步印證此前我們所作的研究論斷【5】:
華夏藝術的文明發展使詩歌、音樂、舞蹈走向了獨立發展,但以“樂”為本體這一特性并未消散,它仍然體現在詩歌的節奏、動律和音韻上。同理,“樂”仍然出現在舞蹈的造型、旋律與騰越上。不獨詩歌、舞蹈如此,華夏文化的其他藝術類型同樣體現了“樂”的特性:韻律、節奏與飛動。……這種“樂舞精神”不僅成為華夏文明的生成基因,更在其后歷史發展途程中化為華夏藝術的血肉靈脈,從而成為我們解讀中華藝術的美學鎖鑰。
1.2 建構“敦煌美學”
敦煌美學是一門交叉學科,介于敦煌學與美學之間。從本質命義上言,它更傾向于列為敦煌學的二級學科,是一門重點研究敦煌文物與藝術之美的人文學科。鑒于其豐富而駁雜的學科特性,經過認真思考,我們認為將其置放于敦煌學中來加以研究比較妥當。一方面,我們可以大量利用現有敦煌學研究成果來拓開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并加大研究力度,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學、藝術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相關研究成果(如佛教藝術、建筑史、考古圖像學、考古類型學、音樂與舞蹈考古學、藝術人類學等)都能得到有效利用而使其更趨完善;另一方面,我們還可借助哲學眼光來研究敦煌學中的美學現象、問題與規律等,并以此為契機,豐富敦煌學研究領域和擴大美學研究的觀照視野,從而進一步探索其與中國藝術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美學史的內在聯系等。在此,我們不是簡單地利用敦煌藝術來為中國美學作例證,而是將敦煌藝術本身作為中國藝術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來研究其中的美學問題,從考古實證的角度準確地分析其美學規律,從而豐富我們的美學研究。
當然,學界對于“敦煌學”的認識目前尚缺乏定論。如《中國敦煌學史》一著的作者就認為:“中國的敦煌學、伴隨著石窟藝術研究的開始,終于成為一門嚴整的學科。” 【6】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者,則持不同意見,如有學者認為:“‘敦煌學’的確是一門不成系統的學問。” 【7】問題不在于以敦煌文物為研究對象本身,而在于可能隨著研究視野的擴大從而導致重心的轉移。我們的看法是,敦煌學研究不能自我孤立、自我設限、劃地為牢從而自我封閉、自行扼殺敦煌學的生命力,而應當利用各專業不同學科及其方法來研究敦煌學資料,用開放的眼光及平和心態去研究與敦煌學相關的材料,以期達到深化敦煌學研究的目的。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隨意擴大研究范圍,從而游離并偏離主題。具體到敦煌美學這一新興分支交叉學科而言,我們就可以為它找到一個恰當的研究范圍,并在敦煌學體系中為其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8】——它應該是與敦煌藝術學與敦煌文學等處于同一層次的二級學科。下面,我們擬從時限、空間和內涵三個方面為其劃定一個大致范圍。
第一,時限。敦煌美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從屬于敦煌文化的,因此,敦煌文化的起迄期也就是敦煌美學研究對象的大體范圍。顏廷亮先生在《敦煌文化》一著中認為:“敦煌文化的歷史開始于4世紀而終結于14世紀” 【9】。這一觀點的上限沒有多大疑問,因為這一點已經為敦煌學界普遍認同,至于下限為14世紀(元朝)就值得進一步推敲。
我們之所以不認同有些前賢們將敦煌學研究對象的下限定于元代這一觀點,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方面,敦煌文化不僅僅指敦煌石窟,還應當包括漢唐時期沿至清朝末年的諸多非物質文化內容,如音樂、舞蹈、文獻等。另一方面,如果說敦煌石窟是敦煌學的主要內容之一,且自14世紀(元朝)以后,其藝術價值幾無可稱道是歷史的事實,那么,藝術價值的不足難道就可以代替其他學術或文化上的價值研究嗎?我們難道僅僅依據其藝術價值就視而不見其他學術意義、文化意義和歷史意義嗎?難道就應該一筆抹煞14世紀以后的石窟藝術和敦煌文化嗎?這種看法無疑是人為地割斷歷史,阻斷了曾經血脈貫通的敦煌文化和敦煌石窟藝術。歷史的問題應該歷史地去看待,我們不能苛求歷史、超越歷史去想問題,以所謂“當代人”的眼光去要求當時的境況。這不是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更不是尊重歷史的科學態度。我們絕不能這樣認為:因為元代以后基本上沒有產生藝術史上的杰作,所以,整個敦煌藝術史就此終止。這是一種未免主觀化且不太負責任的舉動,不僅有悖于歷史的真實,更有悖于我們的治學原則。理由如下:
其一,清代確有一定的造窟與修繕之舉,極個別的清塑也自有其時代的特點,雖然同前代相比,其藝術價值不可同日而語,但就藝術品自身而言,具有一定的藝術水準并反映了當時那個時代的風貌和尺度,這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敦煌藝術已經呈現強弩之末的勢態,清代作為中華封建王朝的尾聲,勢屬必然。我們當然不能把歷史的賬算在敦煌藝術身上。
其二,我們認為,敦煌藝術的下限既不是元代,也不是民國時期,而應是清末。因為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敦煌學,是有特定所指的,即歷史上創造出來的敦煌文化,而民國時期更多的是維護與研究,而不是創造。我們之所以將其下限定為清末,不僅因為清代有許多維修行為,還有一定的創作,如開鑿洞窟,并有一定數量的雕塑、壁畫作品(詳后)。此外,民國時期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中華封建專制歷史階段。更有甚者,自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以來,敦煌就進入了學術層面意義上的新時期,其時雖然略有重修、重繪,更多是出于維修而非主動的創作,中間且摻糅進某些不純粹的非佛的動機因素等。這種情況很顯然與前代造窟、畫壁之舉相矛盾,已經無形中割裂了優秀的敦煌文化傳統。
其三,我們不能將敦煌學的下限截止于元代前后,并無形中受其影響。因為,敦煌遺書當時被封存以后,作為敦煌學之主體的敦煌石窟文化仍然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更有甚者,作為敦煌學分支之一的敦煌文史仍然有著強勁的生命力。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充分考量敦煌學的內容及其方法論問題,敦煌學實則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但是這三個分支在互相聯系的基礎上,彼此并不同步。也即是說,敦煌遺書僅止于“藏經洞”中的文物,敦煌石窟的歷史則從公元366年建窟伊始直至清代封建王朝的覆滅為止;而敦煌文史則應該從中國歷史上敦煌建制開始,即西漢(公元前111年)至敦煌石窟的終止鑿造期間所有歷史文化內容。因此,從時限上來說,敦煌美學的研究內容應該自公元4世紀至20世紀初這一段長達一千六百余年的巨大時段。
第二,空間。既然敦煌學應圍繞敦煌來做文章,敦煌學亦因地名學,那么,其大體空間范圍應以歷史上的大敦煌地區為主,兼及周邊交往十分密切的地域。具體而言,即是以今天的敦煌市所轄地為中心,包括肅北蒙古族自治縣、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安西縣以及嘉峪關市、玉門市和酒泉市以及新疆的吐魯番(舊稱“高昌”)等。敦煌美學的研究對象即依據上述這一大體空間范圍內所產生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中的審美問題來展開的。
第三,內涵。1992年出版的《中國敦煌學史》將敦煌學內容大體分為“敦煌史地”、“敦煌美術”、“敦煌建筑”、“敦煌樂舞”、“敦煌宗教”、“敦煌文學”、“敦煌語言文字文獻研究”、“敦煌科技文獻研究”與“敦煌版本文獻研究”九個分支學科。其中,“敦煌石窟美學”屬于第二大類(“敦煌美術”)。李正宇先生1993年發表的《敦煌學體系結構》結構龐雜,共有十一大類分支學科,主要為:“敦煌史地學、敦煌考古學、敦煌藝術學、敦煌宗教學、敦煌文學、敦煌民俗學、敦煌語文學、敦煌文獻學、敦煌科技學、敦煌文保學、敦煌學學”。 其中,“敦煌美學”位列第三大類(“敦煌藝術學”)中第九項。這一構想是李先生十余年前的研究思路,在此之后,敦煌學又有了新的進展。胡同慶先生于1994年發表的《敦煌學系統工程圖》將敦煌學總體劃分為石窟藝術、藏經洞出土文物與其他遺留文化及相關史料三大版塊,共四十五項內容。其中美學與哲學、心理學共列,與藝術學等并行,成為敦煌學系統的方法之一,以達到“解決有關學科的史或其學科的基本原理,以及借鑒創新等方面的問題”之目的【10】。我們發現,十幾年前敦煌學總體設想在逐步變成現實的同時,迄今仍沒能給敦煌美學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以至于1998年12月出版的《敦煌學大辭典》這一集大成之作竟然無形中取消了敦煌美學,連一個簡要的詞條介紹都吝于留下。
結合前述內容來看,從《中國敦煌學史》一書的作者們將敦煌美學稱之為“敦煌石窟美學”【11】,并將其放置于第二部分(“敦煌美術”,如“敦煌藝術與現實之審美關系”【12】)之舉來看,無疑說明了這樣三個問題:其一,敦煌學界已經認識到敦煌學的美學問題之存在必要性;其二,敦煌美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尚未成立,而且對其研究方法與內容等具體問題尚缺乏嚴謹思考,只粗略地以“敦煌藝術與現實之審美關系”的表述方式匆匆帶過,諸多深入而具體的美學現象、美學問題和審美規律等并沒能得到明確說明;其三,“敦煌石窟美學”一名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即是敦煌石窟中的美學問題,至于其他則被有意識地排除在外。李正宇先生的《敦煌學體系結構》有了進展,出現了“敦煌美學”一詞,遺憾的是,他卻將其放置于第三大類“敦煌藝術學”之中與部門具體藝術類型并列,削弱了“敦煌美學”作為一門分支學科的合法性問題,從而誤將原理性學科問題與方法手段等作了不恰當的倒置。應該說,作者認識到了敦煌美學主要研究敦煌藝術這一問題,只是沒弄清美學與藝術學之間的學科界限,無形中便剝奪了敦煌藝術之外的美學問題,如敦煌文學、敦煌民俗中的美學問題等等。相對而言,胡同慶比較清醒,他不僅將美學與哲學、心理學并列而將其與藝術學置于平行位置,也明確地從方法論角度來安排其位置。但作者卻疏于說明其具體研究對象為何,而且僅作為方法論而不是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去考慮,就難以真正從美學角度去展開深入研究,充其量為敦煌學研究增添一些知識信息,并不能切實解決敦煌學中的具體美學問題,從而導致美學學科地位被削弱、消解乃至被其他學科所代替的現象出現。由此,“敦煌美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也就基本明確了,它主要分為三大領域和兩個層次。
三大領域是:敦煌石窟、敦煌遺書與敦煌文史。敦煌石窟為公元366年至清末年間遺存下來的敦煌一脈文化遺室;敦煌遺書則為1900年由“藏經洞”出來的那批近五萬件文物;敦煌文史為公元前2世紀敦煌建置開始,敦煌文化產生以后至清末年間產生的各種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及其文獻記載下來的全方位內容(無分世俗與宗教)。如果說前兩類主要是與敦煌佛教文化為主所產生的歷史遺存,那么第三類敦煌文史則是文化的全部內容,是屬于敦煌社會文化全景式記錄,而并非單純指宗教藝術。如果尊重歷史,那么,我們就應該明白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在佛教進入彼時的敦煌地區之前,敦煌文化并非空白,而是以漢晉文化傳統為底蘊的世俗社會,除了佛教之外,還有其他教派等的流布。因此,帶有濃重佛教色彩的石窟藝術和敦煌遺書都是彼時敦煌文化(乃至敦煌文史)的一部分。不僅如此,即使以佛教為主體的石窟藝術或敦煌遺書,其中也不乏世俗因子,即敦煌佛教與敦煌石窟本身亦存在相關的世俗化內容,這已經為學界所認可。
兩個層次是:其一,顯層次。敦煌美學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藝術、敦煌遺書和敦煌文史中的基本美學問題。其二,隱層次。敦煌美學還要研究敦煌學中各分支學科中所有相關美學問題和帶有原理性質的元美學問題。嚴格說來,這是一種更帶有基礎性質的原發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敞開學科深層的內應性問題,而不應該僅僅著眼于表象上的具體闡釋。敦煌美學的建立正是為了通過現象的解釋和說明來揭開曾經的“遮蔽”,找出一種富有規律性的機制,進而說明敦煌藝術(或敦煌文化)的血脈;通過研究,揭示其“美”之為美的生成機制;通過敦煌文化的審美分析來找出其與中華民族精神系統的一致性,進而返觀母體自身。
二 研究與綜述
自20世紀敦煌學研究日漸成熟以來,已陸續出現一些針對敦煌藝術審美特性等研究論文。可見,敦煌美學的建立不是歷史的延誤,而是一種自然進程。總體而言,關于敦煌藝術(包括文學等)美學研究的動態大體可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2.1 發軔期(20世紀60年代以前)
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論著不多【13】 ,主要圍繞如下幾個問題來展開:第一,關于敦煌藝術研究的哲學方法;第二,關于敦煌藝術在中國藝術史上的特點、價值與地位,并與西方藝術相比較來顯出其獨特審美風韻。 論文大多自覺運用美學視野來進行觀照;二是擴大了敦煌藝術美學研究的領域【15】,如出現了“飛天審美”、“曲子詞審美”、“講唱文學語言審美”、“樂舞審美”、“服飾審美”等等選題。主要特點是出現了量的積累,理論上的成績不太突出,尤其缺乏原創性理論分析文章。
2.2 探索期(20世紀70-80年代)【14】
本階段,有關敦煌藝術審美特點的探討文章逐漸增多,同前一階段相比,論域有所擴大,某些問題觸及的深度亦略有增強,但并沒有在質的意義上超過宗白華先生的那種理論高度與學術深度,從而顯示出某種繁榮背后的寂寥之感。總體而言,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來展開:第一,關于敦煌藝術中具體形象能否勝任表達抽象思想概念的問題;第二,敦煌美學的存在形式與學科建構問題;第三、圍繞“信仰與審美”主題,分析和闡發敦煌佛教藝術審美的社會因素;第四,關于藝術與宗教的關系問題。
2.3 推進期(20世紀90年代)
本階段是敦煌藝術研究的上升時期,成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表的論文大多自覺運用美學視野來進行觀照;二是擴大了敦煌藝術美學研究的領域【15】,如出現了“飛天審美”、“曲子詞審美”、“講唱文學語言審美”、“樂舞審美”、“服飾審美”等等選題。主要特點是出現了量的積累,理論上的成績不太突出,尤其缺乏原創性理論分析文章。
2.4 深化期(21世紀初期)
進入21世紀以來,敦煌學研究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關于敦煌藝術的美學研究也出現了回顧過去、總結提高的階段。成績主要反映在,有關學者通過整理過去曾經發表的相關論文,在原來的基礎上作出一定的修訂和充實,從而顯出新的認識深度。雖然至今還為時稍短,但出現這一好的勢頭顯示出敦煌美學研究開始步入理性思考。主要論著有:修訂再版的張錫厚先生《敦煌文學源流》,以及胡同慶、胡朝陽合作的《敦煌壁畫藝術的美學特征》、《論敦煌壁畫藝術中的節奏感與韻律》(見《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2期)與《試論敦煌壁畫中的夸張變形特征》(見《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三 思路與方法
3.1 學術轉向
從學科發展角度看,當代藝術學、美學研究再也不是相對純粹的人文學科了,而是與多種其他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乃至工程技術等學科相交叉而互動共生為一門綜合性研究的系統工程,尤其是它們要與考古學聯袂登場,從而宣告自己的新生與成長。因此,當下的藝術學、美學研究就暴露出一些不足,如:傳統藝術理論的“延宕性”、西方美學闡釋的“先在性”、當代考古科學的“即時性”,以及構建人文學科的“迫切性”等。這幾點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我們目前正從事的工作的尷尬。因為,作為一門系統理解和建構人類藝術史(或美學史)的既有理論現在看起來并非那么完善,因此,我們必須找出一條新的解說路徑,以盡可能避免一些隨時充填和重寫的“滯后感”,在材料與釋讀、客觀與主觀、個別與整體、主題與時代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夾縫中走出來,去達到一個新的整合,建立一種新的釋讀方式。
我們在此嘗試引入圖像志和圖像學方式來拾回“左圖右史”的中華文化傳統,不過分依賴于曾經書寫的文字,以免使得我們對中華文明的記憶顯得殘缺不全。正如唐蘭先生所言,我們應該重視不斷發現的新的歷史文物,從而避免“我們的歷史學家將必須不斷地改寫我們的古代歷史”【16】這一尷尬的被動局面。也誠如岑家梧先生書中所言,“文獻無證,必須利用考古學的資料來補足,假使不懂得考古學就不能談古代藝術。”【17】 我們認為,潘諾夫斯基關于考古學與美學研究關系的精辟論述具有一定指導意義,他說:
直覺的審美再創造跟考古式研究互為關聯,從而又一次形成我們所謂的“有機情境”。認為藝術史家首先經過再創造的綜合形成其對象,然后著手考古式研究——就像先買火車票后上車一樣,這不符合實情。其實,這兩個過程并非魚貫而行,而是互相滲透。不僅再創造的綜合可以成為考古式研究的基礎,反過來,考古式研究也可以成為再創造過程的基礎;二者互相限定,互相修正。【18】
潘氏一席話擊中了當前學界(尤其是藝術學、美學)的軟肋。以前我們的美學研究與考古學相結合的工作做得太少,現在應該加強這方面認識,并盡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實際上,美學與考古學相結合并不是簡單的拼接,也不是以某一方為主導的依附性關系,更不是以現在的審美意識去印證歷史,而是以一種客觀求實的實證精神去復原歷史真貌,并以這種分析和看待問題的方法去研究藝術品中本然具備的不同藝術風格之美,從中發掘其科學的、歷史的和藝術的價值等。就宗教藝術而言,世界上其實再沒有任何其他一門學科是如此地具有親和力,它拉近了人們彼此之間的距離,跨越了精神與物質的鴻溝,因為藝術就是對人類生命珍重的意識載體,誠如克萊夫·貝爾所說:
雖然沒有任何宗教能逃脫教理的纏身的外衣,但是有一種宗教可以比其他任何宗教更容易和更漫不經心地把這些纏身的外衣脫掉,這種宗教即是藝術,因為藝術即宗教。它是思想的表現和表現思想的手段,它和人們能夠經歷的任何思想同樣神圣。現代的思想不僅是為了追求最直覺的感情的完美表現,而且是為了追求生活的靈感才轉向藝術的。【19】
藝術既然同屬于人類精神之場的靈物,那么,藝術與宗教之間就不會出現本質上的對立,因為藝術總是在不斷地改變其形式以適應精神的宗教。貝爾說得好:“再沒有別的表現情感的方式和引起心醉神迷的手段像藝術這樣好的為人類服務了。任何一種精神的洪流都可以在藝術中找到一條疏泄的渠道。當藝術不成功時,那是由于缺少情感,而不是由于缺少與之適應的形式。從來就沒有一種宗教能像藝術這樣有適應性和普遍性。”【20】
從宗教學角度看,自佛教輸入中土以來,舉凡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涂染上了佛學色彩。有意思的是,恰恰在敦煌這個最早濡染佛教文化因子的地方,卻顯得是那么風格獨具——它游刃有余于宗教與世俗之間,不即不離,而又若即若離,恰到好處地融出世與入世于一體,合宗教與世俗于一爐,鍛造出一種匪夷所思的藝術奇葩——敦煌藝術!
我們認為,敦煌藝術作為宗教的藝術已隨宗教的遠遁而衰落,而藝術本身作為另外一種形式的存在,卻猶如人類的終極關懷一樣長存。例如,我們將敦煌莫高窟初唐時期的第205窟佛壇上南側的坐式菩薩與盛唐時期第45窟西龕內南北側的兩尊菩薩雕像譽為“東方維納斯”、或“中國的美神”。觀音菩薩的宗教性法衣雖然仍在,但其作為佛教教義上的那個菩薩早已蕩然無存了,產生之初的宗教之場早已不復存在,而且觀音菩薩在中土早已超出了宗教信仰的閾限而走進了千家萬戶,打上了濃重的生活烙印。觀音還是那個觀音,菩薩還是那個菩薩,但早已剝離了宗教的情緒,與中華子民融會在一起了。更為深層的原因還在于,佛教雖然是外來宗教,但已經中國人改造而華化了,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仍然是一種樂生的愛美情操占據了上風,由于缺乏宗教那真正的終極依托,從而以一種替代性方式將精神追求寄托于華化的佛教文化,將內心深處對愛與美的追求在藝術化場景中去達成。而且,中國人的實踐理性與禮教決定了現實宗教的闕如,而只能求助于外置的文化形態,同時也就不期然地與“以美育代宗教”的信念合拍。既然現實中崇尚美的終極觀念,不妨將對宗教的渴望與現實的追求結合起來,于是最終誕生了中國式“美神”——觀音,從而順理成章地解決了宗教與藝術的關系問題,“以美育代宗教”既是一個合理命題,亦是對中華文化真實場景的高度提煉。從這一意義上說,“以美育代宗教”不啻為中華審美文化的準確表述,也是我們進行學術轉向的合法依據。
3.2 主題確定
敦煌美學主要以敦煌藝術為研究主要對象,其中敦煌石窟藝術是主體。此外,還有敦煌遺書中的有關內容以及歷史上的敦煌史地與民俗文化審美等。“敦煌美學”有兩個基本特性不可忽視:其一,浸于佛教文化氛圍之中的藝術造像首重其佛性因素,而藝術的審美性是潛涵因素;其二,敦煌地處多種文化之要津,因此其不同文化雜糅的綜合性質遠大于審美特性。
對敦煌藝術的深入研究可以解決一個困擾美術史多年的重大理論問題。例如,中國美術史研究歷年存在著四種傾向,即以漢族為中心,忽視了其他55個民族;以中原為中心,忽視了周圍的邊遠地區;以文人為中心,忽視了民間美術和宗教藝術;以繪畫為中心,忽視了其他美術。這四種傾向積弊太深,從某種意義上已經扭曲了我們藝術史的整體風貌,用張道一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其結果造成了肢體不全,不能形成大美術事業的良性循環。即使有所成就,也只能是某方面的,局部的、個體的。如果整體而論,便缺少全面的思考和完整的結構。”【21】當我們選擇敦煌藝術作為美學研究的重點時,恰好能夠彌補這一缺憾。因為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正是遠居邊陲的敦煌地區,由一批批不知名的畫家和民間畫工、塑工、打窟匠人創造出來的燦爛作品;這些作品的主題是宗教,并為宗教目的服務的;而敦煌地區本就是處于古“絲綢之路”上的前哨和中轉站,西域古道上各種文化系統在此匯流,數十國的人們曾在此友好往來、生息繁衍等。
總之,敦煌藝術作為一種宗教藝術、綜合藝術、多民族藝術和民間藝術,為我們提供了“大美術研究”的理想范本,從而能夠給我們以新的啟示,同時也為中國美學史的整體研究提供了實例。
3.3 研究方法
我們在遵循理論與實踐、歷史與邏輯和美學與歷史相統一等原則基礎上,力圖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由藝術學上升到文化學、美學和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從藝術文化-審美文化-中國文化等展開一種雙向展望,并充分考慮到中國藝術的母系統與敦煌藝術子系統之間的內在聯系,以期把握敦煌藝術之美的內在理路。其策略與宗旨是實現:
第一,實證考察與文獻遺書之間的互證;
第二,文獻考辨與圖像資料之間的互動;
第三,歷史梳理與邏輯分析之間的結合;
第四,問題意識與原則方法之間的統一;
第五,部門學科與總體線索之間的聯系;
第六,傳統盲區與現實需求之間的張力;
第七,國學積淀與西學眼光之間的互補;
第八,人文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互通。
我們深信,走出傳統美學的固有程式將是中國美學史獲得重建的必由之路。
注釋:
[1]《中國文明起源新探》(蘇秉琦著,三聯書店1999年6月第1版,第176頁。)
注釋:
[2] 一般以為,敦煌學的成立以正式展開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物的研究開端為標志。更有人以為,“敦煌學作為一門定型學科在中國誕生于40年代前期”(見《中國敦煌學史· 緒論》林家平、寧強、羅華慶著,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3] 《論“敦煌學”一詞的詞源》(王冀青,《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2期,第110頁。)
《從“敦煌學”的詞源談起》(方廣錩,《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2期,第91頁。)
[4] 見《敦煌學大辭典·序》。
[5] 見拙著:《樂神舞韻:華夏藝術美學精神研究》之“理論篇”(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06、357頁。)
[6] 見《中國敦煌學史·緒論》(林家平、寧強、羅華慶著,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頁。)
[7] 見《敦煌學十八講·緒論》(榮新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頁。)
[8] 參見拙編《敦煌學體系結構》。
[9] 《敦煌文化·導論》(顏廷亮著,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頁。)
[10] 《敦煌學研究胡同慶論文集》(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頁。)
[11]《中國敦煌學史·緒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頁。)
[12] 見前揭,第5頁。
[13] 本階段相關論著主要有:
a.《敦煌藝術論略》(傅振倫,《民主與科學》第1卷第4期,1945年)
b.《略談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宗白華,《觀察》周刊第5卷第4期,1948年)
c.《敦煌藝術概論》(向達,《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第2卷第4期)
d.《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常書鴻,同上)
e.《我對于敦煌藝術之看法》(徐悲鴻,同上)
f.《敦煌在中國考古藝術史上的重要性》(陳夢家,同上)
g.《談敦煌藝術》(吳作人,同上)
h.《豐富的想像卓越的創造:論敦煌莫高窟壁畫的成就》(金維諾,《美術》1955年11期)
i.《按照美的規律塑造:談莫高窟的彩塑》(金維諾,《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2卷2期)
[14] 本階段相關論著主要有:
a. 《敦煌藝術》(郭宗紓,中華書局1973年第2版、1982年第3版)
b. 《敦煌莫高窟藝術》(常書鴻,《文物》1978年第12期)
c. 《神的世間風貌》(李澤厚,《文物》1978年第12期)
d. 《形象的歷史》(段文杰,《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0年第2期)
e. 《美的歷程》(李澤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3月新1版)
f. 《敦煌佛教藝術之淵源及其在中國藝術史上的地位》(向達,《敦煌學輯刊》1981年第2期)
g. 《試論敦煌壁畫的傳神藝術》(段文杰,《敦煌研究試刊》第1期,1982年第6期)
h. 《早期敦煌壁畫的美學性格》(郎紹君,《文藝研究》1983年第1期)
i. 《敦煌美學談》(1-3)(陳驍,《陽關》1983第2、4、5期,1984年第5期)
j. 《莫高窟藝術之美》(楊學芹,《西部美術》1985年第3期)
k.《信仰與審美——石窟藝術研究隨筆之一》(史葦湘,《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l. 《產生敦煌佛教藝術審美的社會因素》(史葦湘,《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m.《再論產生敦煌佛教藝術審美的社會因素》(史葦湘,《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n.《從晚唐石窟論敦煌佛教藝術的審美特征》(史葦湘,《敦煌研究》1987年10期)
o.《意象激蕩的浪花——試論敦煌美學》(孫宜生,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p.《敦煌石窟藝術中有待探討的美學藝術學的幾個問題》(洪毅然,《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q.《儒家思想及其美學觀點對敦煌藝術的作用》(李浴,《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15] 本階段相關論著主要有:
a.《敦煌壁畫飛天及其審美意識之歷史變遷》(陳允吉,《復旦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
b.《敦煌藝術美學巡禮》(謝成水,《美術研究》1991年第2期)
c.《試論敦煌曲子詞的審美特征》(張仲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d.《敦煌講唱文學語言審美追求》(汪泛舟,《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e.《初探敦煌壁畫中美的規定性》(胡同慶,《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f.《敦煌樂舞中的對稱美學思想》(高德祥,1994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提要)
g.《敦煌舞譜的當代審美意識》(陳曰國,1994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
h.《封建專制下的人性精神——敦煌說唱文學的美學意義初探》(傅小凡,1994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
i.《宗白華與敦煌藝術研究——兼談敦煌藝術研究的哲學方法》(穆紀光,《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j.《“藝術、藝術哲學、敦煌藝術哲學”散論》(穆紀光,《甘肅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
k.《敦煌壁畫服飾審美文化透視》(喬志軍,《益陽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
l.《敦煌石窟藝術的美學特征》(方健榮,《絲綢之路》1997年第6期)
m.《試探敦煌俗賦的體制和審美價值》(伏俊璉,《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n.《試論敦煌壁畫音樂藝術的美學觀》(莊壯,《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o.《以敦煌飛天為基準的美的設計方法》([日]高梨隆雄,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提要)
[16]《陜西、江蘇、熱河、安徽、山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唐蘭,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1版。)
篇(4)
Keywords: Ikeda On; Education summary; Dunhuang Studies; Catalogue of work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池田溫教授是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世界級敦煌學家。他1931年12月出生于靜岡市,2011年4月,在池田溫先生八十壽辰前夕,日本數位敦煌學與魏晉南北朝唐史學者(金子修一、土肥義和、坂上康俊、小口彥太、窪添慶文、大津透及池田先生本人,還包括韓國學者任大熙)聚會在東京的東方學會會議室,就其學問與人生進行了座談{1}。在此,我們對先生的敦煌學研究略作介紹,以紀念池田先生八十壽辰。
一
池田溫先生23歲畢業于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1956年獲東京大學碩士學位,1961年在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完成了博士課程{2}。此后,他在北海道大學、東京大學、東洋文庫任職,于1976年4月晉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同年10月兼任東洋文庫研究員。1990年出任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兩年后正式從東大退休,出任東大名譽教授。1992年4月,擔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自1993年10月起,在創價大學任職,其間于2002年4月任該校文學部特任教授,2007年3月以名譽教授身份退職。在四十余年的教學研究生涯中,池田先生還獲得了兩項重要榮譽:1983年以《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榮膺第73回日本學士院獎;2003年被授予日本國勛三等旭日中綬章,該榮譽是日本國授予“對國家公共有功勞者中,有引人矚目的顯著功績內容”之人,這正與池田先生在學術領域的輝煌成就相匹配。此外,他還承擔了一些重要的學術兼職,如曾任日本東方學會、唐代史研究會的會長,現在則是東方學會、史學會的顧問。這些學會在日本學界聲望甚高。他還出任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中國敦煌研究院兼職研究員及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干事。
少年時代的池田先生接受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初步訓練,1952年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學習后,在西嶋定生的講座中學習了杜佑的《通典》,同時研讀了西嶋先生的《中國農學史》、《中國經濟史概說》等講義,自此有志研究中國古代史。
正在此時,在海外訪學的山本達郎先生回到了日本,他將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調查到的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中的戶籍類文書作為講座教材,分發給學生認真釋讀,這種一字一字地釋讀可以說對池田先生以后從事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獻的研究有很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將池田先生引入了敦煌學領域。1954年大學畢業后繼續在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讀研究生,師從著名的中國經濟史專家西嶋定生先生,在西嶋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論文《有關唐代均田制的研究——以其實施的實情為考察中心》[1]。
在大學和研究生學習期間,池田先生親炙于山本達郎、榎一雄、西嶋定生、倉石武四郎、仁井田陞諸先生,為其學術航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此,日本現任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關尾史郎教授在介紹西嶋先生的學術業績時,認為作為西嶋先生的學生,池田先生是日本“吐魯番學和敦煌學第一人”[2],以示其學養淵源。而從20世紀50年代通過山本達郎先生接觸西魏大統計帳,并在東洋文庫觀摩、整理斯坦因所劫敦煌文獻的膠卷開始[1]260-261,池田先生已在敦煌學園地耕耘了半個世紀,成就巨大,影響廣泛,正如榮新江先生所言:“在敦煌學的世界里,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大概是沒有人不知道池田溫先生的了。”[3]
二
為池田教授帶來莫大聲譽的首推《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和《中國古發表本識語集錄》兩部論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的概觀部分由序章和三章組成。序章主要是研究史的回顧與總結;第一章通過對戰國到漢代簿籍的演變研究,著力探討古代籍帳制度的形成;第二章通過對魏晉十六國籍帳的考察,主要研究了籍帳制度的變質;第三章是本書重點,即利用敦煌、吐魯番籍帳文書研究古代籍帳制度的完成與崩潰。一是由武周、開元初年籍帳的松弛而深入研究了開元敦煌籍中出現的檢括痕跡,如開元十年籍草稿中所見到的檢括和征兵、見于開元四年籍抄錄中的檢括及宇文融括戶政策的一面;二是指出天寶敦煌籍中所出現的偽濫傾向,如每戶口數的增大、男女數的不均衡,并分析了偽籍的原因;三是在差科簿研究的基礎上,從文書原形與年代、差科簿的登錄對象、破除與見在、差科簿的編制手續、年齡分布與老小登簿、差科簿中出現的鄉間的差異、差科的特質、大歷差科簿的形骸化諸方面,全面討論了敦煌差科簿的變遷;四是以大歷四年敦煌手實為線索,通過對本件手實的外形、登載戶口的激減、田土登錄的名目化與全國統計的關聯,揭示了安史之亂后籍帳的荒廢傾向。并且,以比較的手法放眼東亞古代社會,初步展開了日唐戶籍法令、日唐籍帳樣式與內容異同的對比研究。他認為唐代籍帳制度是古代東亞各國的模范,而敦煌吐魯番籍帳文書是極為寶貴、可供參考的資料,并對這種比較研究寄予期待[4]。由于他的研究能夠十分貼近文書的客觀內容,所以其探討方式和所得結論都帶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另外,《中國古代籍帳研究》的錄文部分載有敦煌籍帳(戶籍類文書)15件,天寶年代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3件,其他與敦煌人口、土地、物品相關的籍帳上百件。著者將敦煌籍帳文書放到漢唐籍帳制度演變的長河中,這種長時段的考察視角使敦煌籍帳的價值凸顯,同時看到了古代中國籍帳的演進之路。池田先生的錄文工作是漢語古文書學的典范,切實做到了盡可能地研讀敦煌文書原件,從原件出發以詳作注記。在本書中,池田先生完善了錄文的規范,記明年代、原題或擬題、正文各行番號。錄文凡例中又以各種記號表明異體字、俗字、通用字、殘存字記號,前后缺記號,例補記號,異于本文筆跡文字、朱字、朱點、朱勾、朱印、抹消文字、印鑒、原紙縫、原來不連接斷簡等等。嚴格的注記規范主要體現在錄文末尾的注記(原本收藏藏家、登錄號、尺幅、縫背注記、目錄著錄、圖版刊行、別家錄文)、紙背及連貼型制、插圖,而對構成寫本的物質要素如用紙、墨料、裝潢等外觀也加以注記。為了照顧字體、書寫風格、書寫格式、印簽等外貌而專門設計了插頁,以上圖版下錄文的直觀方式,便于使用者參照。這些細節都體現了著者的良苦用心。池田先生對古文書學的卓越追求,為發展中國古文書學的規范提供了榜樣[5]。
本書出版后,得到了中日學界的一致肯定,高明士先生認為:“以敦煌吐魯番的文獻而言,半個世紀以來內外學者專家對籍帳制度的檢討,到池田氏書出,可謂集其大成。本書作為‘敦煌學’有關籍帳類的錄文而言,可說是最完備的書。”“實際上作者多年來殫精竭慮的成果均已融會在本書里。”[6]并且,本書還被認為是“對戰后均田制研究帶來巨大推動并構成其發展階段的代表性成果”[7]。
不過,《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之“古代”,主要是指從商周到隋唐,“這種時代區分,正是以東京大學為中心的學者們的說法。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學者們卻將隋唐作為‘中世’的結束。日本史學界對隋唐一段的時代區分法差異很大,這是我們參考日人著作時應格外留意的地方。”[6]216可見本書烙上了東大史學傳統的痕跡。
篇(5)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and New York, 1998.
這就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季先生著《新疆博物館藏甲種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的英文本,由季羨林先生轉寫、翻譯和注釋,得到德、法兩國吐火羅語學者W.Wenter和J.-J.Pinault的協助,由總部分別設在柏林和紐約的跨國出版公司Mouton de Gruyter于1998年出版,列入Wenter教授主編的《語言學的趨向叢書》(Trends in Linguistics),作為其中《與專著》 (Studies and Monographs)系列的第113種出版。
現藏新疆博物館的這批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殘卷,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個星(錫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個灰坑內發現的,共44葉,雙面書寫婆羅謎文。八十年代初,新疆博物館把這批寫本的照片送給季先生,請季先生解讀。季先生很快辨認出這是用甲種吐火羅語(Tocharian A)所寫的《彌勒會見記》劇本。從此,季先生開始解讀這部“天書”。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一點也不過分。熟悉語言學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新疆發現幾種滅絕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尤以吐火羅語最難解讀,因為吐火羅語屬于印歐語系的西支,而發現的地點卻在印歐語系各種語言分布區域的最東端,其中不少詞匯早已變形或消失,給解讀帶來極大困難。而熟悉新疆出土各種民族語言資料情況的人知道,相對于同時出土的死語言----于闐語和粟特語的材料來說,吐火羅語的資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數是從新疆各地的寺廟和洞窟廢墟中挖掘出來的,往往殘缺不全,不像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一些于闐語和粟特語寫卷,長逾千行,而且完整無缺。季先生解讀的這部“天書”,也同樣是殘缺的,每葉的左邊都有約三分之一的部分被火燒毀,給解讀造成更多的困難。
說這部吐火羅語的著作為“天書”的另一層意思,是因為它的價值連城,極富研究旨趣。首先,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因為過去發現的吐火羅語材料較少,雖然經過近百年的研究,還有許多沒有解決,通過這部殘卷的解讀,可以增加辨識的吐火羅語詞匯,可以積累吐火羅語的語法形式,可以弄清一些吐火羅語名詞和動詞的變化形式,進而可以討論和檢驗前人關于印歐語系諸語言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還牽扯到新疆發現的吐火羅語材料引發的一個更大的學術爭論問題,即印歐人的起源問題。其次,從的角度來看,我們過去對操吐火羅語的龜茲文化的認識,主要是通過漢文史料和僧人傳記,而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卻提供了比較完整的龜茲古代佛教著作的典范,使我們可以透過它來了解龜茲佛教的淵源、小乘佛教在龜茲的流行、龜茲譯經的水平等問題。最后,因為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是一部劇本,而新疆吐魯番和哈密出土過從吐火羅語譯出的回鶻文本《彌勒會見記》,這就給我們認識西域戲劇的形式、和傳播途徑,提供了絕好的材料。
季先生當然十分清楚這部吐火羅語的價值,所以,在接到這批資料時,雖然已經年逾古稀,卻毅然決定利用早年在德國的吐火羅語知識,來解讀這部“天書”。
八十年代,季先生曾經在北大主持過一個“西域文化讀書班”[1],我也曾忝陪末席,受益良多。由此,與季先生往來較多,所以在季先生解讀這個殘卷的文字和研究相關內容時,時而讓我查找一些西域語言文字資料,特別是于闐語資料。季先生的關于這部吐火羅語文獻的研究成果,對于我們理解西域文化很有幫助;他對古代西域彌勒信仰的考察,以及他翻譯的與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內容相關的于闐語文獻,對于我研究于闐的歷史與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因此,我一直關注和收集季先生有關這個殘卷的研究成果。
在這本英文書出版前后,我所知道的季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發表在以下書刊中,現依出版年代順序列之于后[2]:
《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6-19頁。
《文物》1983年第1期,42-44頁。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43-70頁。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7頁。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I, Reykjavik 1987, pp.70-76。
Studia Indogermanica et Slavica. Festgabe fur Werner Thomas zum 65.Geburistag,
Munchen 1988, pp.141-151。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23-39頁。
《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3-14期,1989年,250-259頁。
《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年,36-43頁。
《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4-15頁。
《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71-74頁。
《知の邂逅:佛教と——冢本啟祥教授還歷記念論文集》,東京佼成出版社,1993年,93-99頁。
《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4頁。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3-8頁。
《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8年,212-216頁。
《中亞學刊》第5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4-8頁。
季先生前期發表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成果,主要是用中文寫成。后來考慮到吐火羅語研究這門學科的國際性,加上Wenter教授的鼓動,最終決定用國際學術界最通行的語言----來發表全部轉寫、翻譯和注釋,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英文新書。
這本書主要由四部分組成。
一、《導言》,介紹殘卷的發現經過、外觀,提示E.Sieg與W.Siegling在《吐火羅語殘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中發表過的《彌勒會見記》殘卷、回鶻文殘卷和翻譯,以及漢、藏、于闐、粟特、巴利、梵文中的內容相近的文本,概述第一、二、三、五幕的內容,最后是一些技術性的說明。
二、《殘卷的轉寫、翻譯和注釋》,這是對44葉,88面殘卷文字的全面整理,由于編者的精心安排,書中的轉寫和翻譯都是頁面相對排印的,十分便于讀者對照,而注釋則附在每一面翻譯的后面。
三、《索引》,包括焉耆殘卷中出現的所有詞形和它們出現的葉、行數索引,根據詞根分類列出的所有動詞詞形及含義索引,其他所有非動詞詞匯的釋義索引。
四、《圖版》,用銅板紙印制的殘卷全部88面圖版。
可見,這是國際學術界典型的古文書整理考釋之作。《導言》提示基本情況和前人研究成果,以及殘卷內容;轉寫、翻譯、注釋構成全書的主體;詞匯索引是古代語言研究的著作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像吐火羅語這種沒有真正的詞典的研究領域,更是如此;圖版可供其他學者核對本書的轉寫。
現在,這部英文大著已經收入江西出版社出版的《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題作《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書前有漢文部分,只有《導言》,沒有轉寫、翻譯和注釋,但《導言》中關于本書性質說明,對Maitreyasamiti與Maitreyavadanavyakarana兩者區別的辨析,敘述巴利、梵、于闐、粟特、回鶻文中的彌勒資料,以及討論彌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和在新疆的傳播,都比英文本要詳細得多,如討論于闐文資料時,根據R.E.Emmerick教授的英文譯本,把于闐文《贊巴斯塔書》( Book of Zambasta)第二十二章,即于闐文本《彌勒授記經》全部翻譯成漢語,還加了一些Emmerick原書所沒有的注釋,對中文讀者十分方便。我想,如果季先生把全部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都譯成漢文,集中出版,對于國內研究西域歷史、語言、宗教、戲劇的學者,都是十分有益處的。
讀完季先生的這部大著,掩卷沉思,不由得浮想聯翩。
自從1983年開始,季先生就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一職,除了在組織上和指導思想上推動敦煌學的健康之外,季先生還身體力行,以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研究,開拓了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
篇(6)
2010年11月的一天,甘肅省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收到一封來自美國西雅圖的信。信中,一位叫(Mimi)的女士表達了她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熱愛,尤其是對敦煌藝術情有獨鐘,希望能夠現場觀賞敦煌藝術。樊錦詩被她的熱情打動了,經過研究院討論同意,她給回信,歡迎其隨時造訪敦煌。
2011年2月,衣著簡樸的女士如約而至,在樊錦詩的陪同下參觀了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洞窟735個,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2415座,被譽為“人類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藝術的寶庫”、“東方盧浮宮”……女士對此驚嘆不已,表示愿意贈送一套兒子設計的文物管理軟件系統給敦煌研究院,樊錦詩被她的心意感動了。
閑聊之中,女士提到他兒子的軟件公司叫微軟,樊錦詩驚訝地道“您是比爾?蓋茨的母親?”女士笑笑說“準確地說,我是他的繼母。”
樊錦詩真沒想到比爾?蓋茨的繼母如此平易近人且作風嚴謹,完全不似養尊處優的老太太。更令她意外的是,女士還是中國通,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淵源。
女士畢業于斯坦福大學亞洲史學系,后在愛荷華大學攻讀東方與中國研究碩士,并取得了耶魯大學藝術史博士學位,是美國首屈一指的亞洲藝術專家。早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博物館工作的時候,她經常與中國文物打交道,對中國文化著迷不已。
1985年,她到北京大學學習中文,所接觸的中國人都非常友好,這讓她對中國的印象更好了。學習期間,一位教授給她起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中文名字一一倪密。教授說“倪”是中國人的姓,含義為“邊際”,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即使遠在天邊,也同樣與中國文化保持親密關系”。她非常喜歡這個名字,每次聽到中國人這么叫她就開心。
畢業于北大考古學專業的樊錦詩知道了女士的中國情結后,也親切地稱呼她為“倪密”。
她曾將三星堆文物精華請到美國展覽
倪密告訴樊錦詩,20多年來,她一直致力于亞洲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的研究。她在北大留學期間研究的課題就是中國古陶瓷,并以此著述通過了論文答辯,后來,她的研究成果被結集成書出版,在美國相當暢銷。
她第一次來敦煌是1998年夏天。當時,她住在敦煌研究院的招待所里,半天看洞窟,半天在圖書館翻閱資料。下班以后,游人散去,她又站在洞窟前靜思懷古,沉浸于歷史的長河中。一周時間,她深深地被敦煌藝術所打動,同時也為這些壁畫和彩塑受到風化、游客增多等因素的破壞而感到痛心。
之后的一天,當她再次回味敦煌藝術的璀璨時,猛然意識到再不盡快采取保護措施,人類將會永遠失去這個無價的歷史瑰寶。于是,她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對敦煌藝術的研究中,為此傾注了大量的感情和心血。此次敦煌之行,就是為了尋求與敦煌研究院進行合作。
樊錦詩感嘆:“難得你對中國文物、敦煌藝術有著這樣一片摯愛之心”
她告訴倪密,敦煌壁畫、彩塑等文物因為建成年代久遠,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空鼓、起甲、疤疹、酥堿、霉變等現象,她對此也感到非常揪心,也在殫精竭慮地想辦法保護。
倪密說她決定去歐美籌措資金,為保護敦煌文物盡一份微薄的力量。樊錦詩向她表示感謝,她說:“為保護敦煌文物,我愿意竭盡全力也許你不相信,我曾經為了成功借展中國文物,不惜花費幾年心血來爭取”
這話絕非空穴來風。1995年,倪密擔任西雅圖博物館館長期間,收到一位中國朋友寄來的生日禮物一一三星堆文物明信片,她就此對三星堆產生了興趣。實地欣賞了三星堆文物后,她萌生了將其借展到西雅圖的想法,但四川省文物局擔心文物在運輸過程中出現閃失,婉言謝絕了她的請求。她并沒有就此放棄,之后又請基辛格、美國副總統戈爾和當時任得克薩斯州州長的小布什時任華盛頓州州長的駱家輝等人說情,加上四川省文物局實地考察后認可了西雅圖博物館的借展實力,雙方終于于2000年12月簽訂了借展合同。
然而好事多磨,兩個月后西雅圖經歷了50年來最嚴重的地震。為了打消四川省文物局的顧慮,倪密想盡一切辦法獲得了美國最權威的地震研究機構一一華盛頓大學地震研究所提供的相關資料,資料分析表明三星堆文物借展西雅圖博物館期間,華盛頓州內及其鄰近地區絕對不會發生地震(西雅圖位于華盛頓州),這才保證了文物展如期進行。
2001年5月2日,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圖開展。此次展出了來自中國四川的各種文物共175件,其中包括大青銅立人像、大青銅縱目面具等6件國寶級文物,是西雅圖博物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文物特展。展覽在西雅圖引起轟動,當地媒體評價說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最引人注目的文物精品展覽”,是“中美兩國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
正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倪密愿意為保護中國文物竭盡全力。
受繼母影響,比爾?蓋茨也愛上中國藝術
在對三星堆文物和中國古陶瓷進行研究的同時,倪密從不間斷對敦煌文物的研究。2010年10月,她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美國敦煌基金會并擔任主席,為敦煌藝術的研究與保護四處籌措資金。2011年2月,她在樊錦詩的陪同下考察了敦煌后,又于5月再次進行考察,從中收集了大量歷史資料和研究資料。
7月2日下午,她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進行了一堂以“千古遺珍――敦煌佛窟”為主題的演講。在兩個多小時的演講中,她以大量詳實的多媒體材料,向聽眾講解敦煌的歷史、壁畫創作的精妙以及這些文化遺產的保存和維護情況。
她告訴聽眾,統計數據表明,僅莫高窟每年就要接待游客50多萬人,遠遠超出洞窟的接待能力。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敦煌研究院準備修建“游客中心”,中心可以把莫高窟內的壁畫影像設計成3D的形式,讓游客觀看洞窟影像時有身臨其境之感……
她同時展示了河南籍畫家劉劍霞所畫的第248窟敦煌壁畫作品。劉劍霞掌握了把真正的墻面壁畫復制到畫布上的特殊技藝,站在她的作品前,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千年敦煌壁畫,感受經千年歲月沉淀后成熟而美麗的色彩。
演講結束后,倪密回答了聽眾的提問,并提供了敦煌管理機構一一中國敦煌研究院的官方網站、美國敦煌基金會、英國敦煌國際項目組織等機構的網址以及所保存的網上資料,聽眾對敦煌文化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這次講座促進了美國人民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敦煌文化的了解。倪密表示,她今后還將舉辦更多的活動,促進世界了解敦煌藝術、保護敦煌藝術。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她的影響和熏陶,比爾?蓋茨父子也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談到妻子時,老蓋茨最為自豪的就是妻子是一位中國藝術研究專家,他總是對妻子曾經出版過中國古瓷研究方面的書籍而津津樂道。每當妻子到中國欣賞文物或參加學術活動時,他都如影隨行,從中也了解了不少中國文化。
篇(7)
關鍵詞:西北方言;下位變體;藏文對音;回鶻字音;西夏材料
中圖分類號:H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3)02-0100-03
一
在中世紀時期的中國,西北方言被視為組成漢語的一種重要語族。這種方言在西北地區廣泛使用,作為中國和中亞之間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手段,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敦煌、吐魯番及其他中亞等地發現的吐蕃語、粟特語、于闐語、回鶻語等古代中亞語言文獻中出現了大量的漢語詞匯,從中可以看到那些文獻一般都表現了西北方言的特點。不過,考慮到說西北方言的地域廣大,就可以想象其中一定產生了相當多的變體。遺憾的是,這種變體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對此不夠重視的原因是,這種方言的語音系統缺乏可靠的音韻材料,除了以下少數幸運的之外:
(1)10世紀河西方言(敦煌): 由于吐蕃文和于闐文中使用了漢語文獻,當地人為漢字作了注音,可以據此為這個語音系統溯源[1]。
(2)漢字的回鶻語發音:這廣泛使用于9到14世紀的回鶻汗國中。這種回鶻語發音是基于各種西北方言的,但又與河西方言的發音略有不同[2-5]。
(3)12世紀西夏王國里所操的漢語方言:學者們已經嘗試用西夏—漢雙語字表《蕃漢合時掌中珠》重構這種方言的語音系統[6-9]。
除了上述材料以外,還包括下面的材料:
(4)這種方言反映在823年漢蕃條約碑(即《唐蕃會盟碑》)的轉寫中。這種轉寫顯示的是長安標準語的語音系統,可以認為長安方言是西北方言的一種。
在本文中,筆者旨在指出古代西北方言中存在系統的、重要的變體。
二
那么,古代西北方言的主要語音特點是什么呢?我們可以考慮把以下兩個作為其中最顯著的特點:(1)鼻輔音聲母的非鼻音化,m-、n-、η->mb-、nd-、ηg-;(2)鼻韻尾的消失或弱化,-m、-n、-η。像濁音聲母的清化、塞音韻尾(如入聲韻尾)的消失、一系列音節韻母的合并等變化,和其他的因太細微而沒有被認識到的差異,都不能當作是西北方言的特點。因為在其他方言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特點。然而,濁音聲母的清化值得我們注意。一般來說,所有的北方官話濁音聲母的清化模式應該遵循同樣的規則。平聲的濁音聲母系列變為送氣清塞音,而其他聲調(上、去、入聲)則變為不送氣清塞音。基本規則概括如下:
三
考慮到現代方言的材料,我們認為上面提到的普遍化的濁音清化模式似乎是有根據的。這種模式同樣也適用于古代西北方言嗎?在試著重構10世紀河西方言的語音系統時,筆者偶然發現有兩個獨立的材料,他們的模式相互矛盾。第一個是藏文書寫的漢語佛教文獻《大乘中宗見解》(T),另一個是用于闐文寫的漢語佛經《金剛經》(Kbr)。這兩個材料都可追溯到10世紀;而且,如果不考慮聲調的差異,可以認為他們用不送氣清音來表示所有的濁音系列。如前所述,其他所有材料都表現出了正常的清化模式。然而,根據大多數材料中顯現的系統來重構河西語音系統似乎是準確無誤的。不過,面對這兩種文獻中發現的反常模式,我們不可避免會對假設在10世紀河西地區存在一種不合規范的方言而猶豫不決。眾所周知,客家話是與這一描述擬合的方言之一。據袁家驊的研究,江蘇省的一些方言,如南通、如皋、泰州等地的方言中也顯示了相似的模式[10]。我們能在山西省聞喜方言的白話層里發現相同的模式[1]73, 這在今天的西北方言中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然而,這種相似僅限于聲母*b-這一例。值得注意的是12世紀的語音系統。龔煌城、李范文成功地用西夏——漢雙語字表《掌中珠》重構了西夏王國所說的漢語方言,表現出與上述完全相同的清化模式。盡管在重構的方言系統方面,龔氏和李氏的研究還存在著差異,但是,就我們正在研究的問題而言,他們已經達成了共識。12世紀西夏王國所操的這種方言,時間和空間上最接近上文提及的兩種材料。雖然我們還不能認為那些材料反映了存在于西夏王國漢語方言的前身,但是我們研究結果的證據,卻支持在10世紀河西地區可能存在某一方言。這種方言中四個聲調的古代濁塞音和塞擦音全部變成了不送氣清音。
四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古代濁音聲母因四個聲調的不同而分為兩部分,這是一個與現代漢語北方話共有的重要特點。然而,這與古代西北方言情況并不相同。古代的方言似乎已經產生了許多變體。而且,以存在像我們見到的那樣一個重要變體為理由,我們甚至可以懷疑是否存在統一的古代西北方言。“古代西北方言”這個概念,可能是一個受現代漢語方言分類影響的錯誤觀念。上古和中古時期西北地區漢語方言的歷史發展也許比我們所想象的更為復雜。基于回鶻語發音的漢語方言的語音系統與10世紀河西方言十分相似,但是二者的確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存在著分歧。因此,漢語方言可能存在另一種變體,生活在吐魯番盆地的中國居民們持續不停地使用著這種變體。深入研究該問題所能使用的材料極其有限,這使得我們離全面研究古代西北地區所有方言的距離還很遙遠。考慮到這些因素,目前我們所能做的是通過相關材料的研究和可靠證據的積累來探討語言變體。
譯者注:本文英文原題為“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刊于波波娃(Irina Popova)、劉屹主編《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Dunhuang Studies: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rch)》,圣彼得堡,2012年,第249-250頁。
參考文獻:
[1]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M].東京:創文社(東洋學叢書),1988:33.
[2]高田時雄.ウイグル字音考[J].東方學,70,1985:134-150.
[3]高田時雄.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J].東方學報,62,1990:329-343.
[4]吉田豐.ソグド文字てされた漢字音[J].東方學報,66,1994:271-380.
[5]莊垣內正弘.ウイグル文字音寫された漢語佛典斷片について—ウイグル漢字音の研究[J].言語學研究,14,1995:65-153.
[6]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問題)[C]//龔煌城著.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北: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2002:243-28.
[7]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C]//漢藏語研究論文集.2002:282-330.
[8]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母系統的構擬[C]//漢藏語研究論文集.2002:331-377.